
我关注到目连戏,是因为研究《西游记》的关系,目连变文中的有些内容和现今发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有相像之处。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剧作品之一,“目连救母”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要比玄奘取经的历史故事传播更为广泛。鲁迅先生也多次写到绍兴目连戏,如《无常》(“目连戏的热闹,张岱在《陶庵梦忆》上也曾夸张过,说是要连演两三天。在我幼小时候可已经不然了,也如大戏一样,始于黄昏,到次日的天明便完结。这都是敬神禳灾的演剧”)、 《且介亭杂文》(“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连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连救母记》是完全不同的”)。现今台湾地区民间丧礼法事,仍偶有目连戏演出。孝子目连、孝女白琴,更多民间丧葬与孝文化的表达,也是中元普渡时的例常祭礼。故而目连戏并不算是演来娱乐的,更有仪式剧的作用。有些仪式中会出现三藏取经、过火焰山等等表演,历史悠久。
三十年前,朱建明曾写作一篇有趣的文章《目连戏在上海》,指出上海流行目连戏已有三百五十年的历史。早在明末清初,上海人姚廷遴在《历年记》中记载,“崇祯十七年……周浦做目连戏。”清末民初,目连戏开始真正盛行上海。其时流行的目连戏有四种——徽剧、绍兴武班、昆剧、京剧。前一阵我在上海昆剧院看《目连救母》,想到一些有趣的问题。目连戏,又称《救母记》。目连虽为唐人,也西行见佛,但不像唐僧为了普度众生。目连不忍见到母亲在地狱中受苦,甚至愿意为了救母放弃修行,解除神力,贬为凡人。“目连救母”的故事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实际上还是来自故事本身悲剧的力量。郑之珍《目连救母》的“三殿寻母”,刘青提唱“三大苦”,非常直接地表述了妇女生产之疼痛、养育孩童之艰辛。细致到讲述母亲在抚养孩童时的各种提心吊胆的心情,从一怕到十怕(怕冷着、饿着、摔着、病着……),身为人母,永生永世牵肠挂肚,一直到死,化成鬼魂,还在思念儿子。在地狱里登上望乡台,还想要看见儿子。对于佛门来说,刘青提破戒背叛,是个罪人。但同时,这位宗教上的罪人又是个人间慈母。这种人物处境的刻画方式,十分具有感染力。目连明明知道母亲有罪,却愿意为母亲的罪承担责任。他承担的方式,是不惜牺牲自己的前程,来为母亲忍受苦难,非常动人。这种母子之间的依恋焦虑,在戏曲舞台上被一再放大、强化,深入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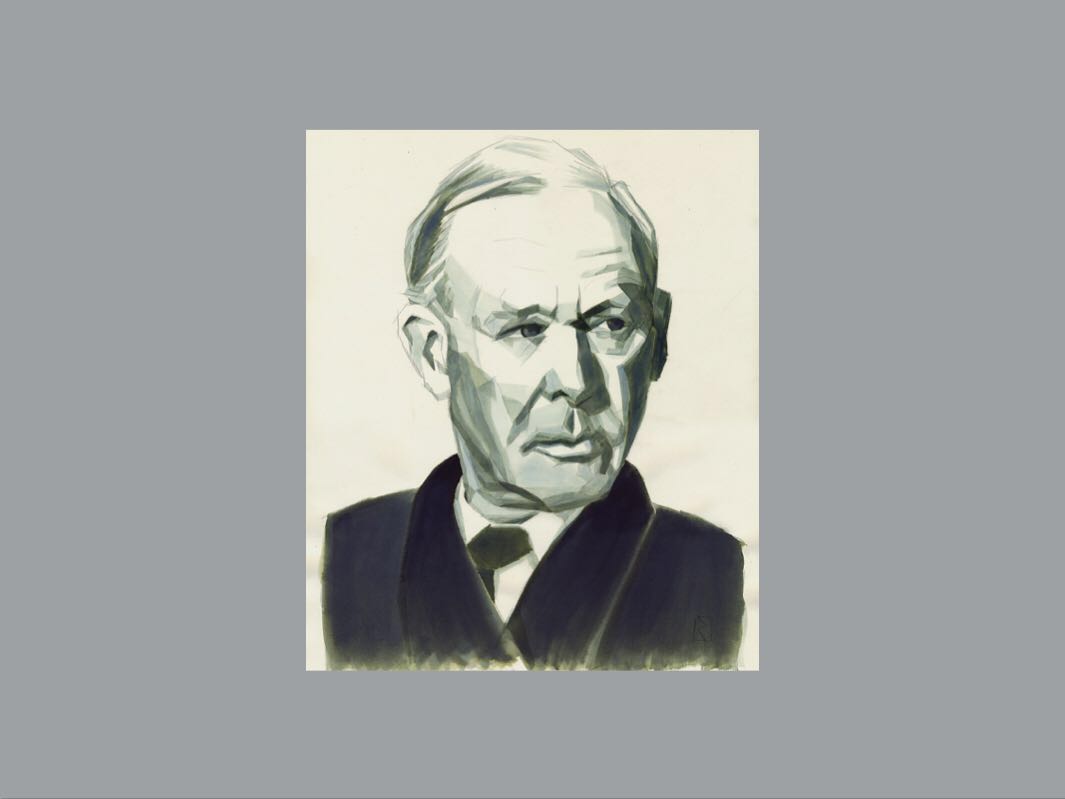
▲英国发展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
北京大学的易春丽在为英国发展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的著作《安全基地:依恋关系的起源》作序时提到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即“我们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中几乎看不到男人去救妻子,我们看到的是儿子救母亲的故事,比如《宝莲灯》《白蛇传》。女性期待拯救自己的是她们的儿子。这是中国女性的集体无意识。母子共生是我们的文化所鼓励的”。但她同时强调,“在精神分析中,无法分离是一种病”。
目连为了救母亲,既辞婚、又辞官、不愿成佛、百折不回,哪怕母亲有错,哪怕母亲变成了一条狗,这种拯救力量是悲剧性的、震撼人心的,同时也可能是可怕的。 “目连救母”之“救”,不仅仅是“救援”之“救”。它恰恰指向孩童内心的“不愿分离”。

安徒生的名作《海的女儿》,虽然是篇给小孩子读的童话,在“分离”问题上,却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探索。小人鱼不顾一切投入爱情,非常自信地觉得王子一定会爱上她,她没有想到,当她用自己的声音和舌头换得人腿之后,她发现王子虽然很喜欢她,但并没有要娶她。在迷惘之际,小人鱼才懂得自己和巫婆交易的真正代价,她再也回不到自己的家庭中去了。她没有忘记她的亲人,她的亲人也没有忘记她。失恋的痛苦放大了她内心的孤独,每天晚上,小人鱼都看到自己的姐姐们浮上海面遥遥地望着她。有一天晚上,小人鱼甚至看见了多年不曾浮出海面的老祖母和戴着王冠的海王。他们对她伸出手来,但他们不像她的那些姐姐,没有敢游近地面。这种隔着海洋的互相遥望,是爱情与亲情的撕裂。小人鱼的姐姐们用头发换得了一次挽回的机会。小人鱼如果愿意用巫婆的刀刺向王子的心脏,让王子的血流到自己的腿上,那么她就能重回大海,变回原来的样子。当小人鱼远远地看到姐姐们失去了漂亮的头发,她的内心该是多么痛苦啊。那是亲人无言的爱,也是牺牲与牺牲之间的互相照亮。众所周知的是,小人鱼最后化成了泡沫。善良的她接受了分离,也由此获得了一种成人式的升华。这种升华,同样也是悲壮的。
过分沉溺于“分离焦虑”的母亲,也会受到追求独立自由的年轻人的批评。但《目连救母》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依然没有解答。母亲有错怎么办?曾忍受生产痛苦的母亲、保护过孩子的母亲,如果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身为子女的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们在文学里读到、听到过这样的矛盾,是这种矛盾把我们引领到人类本性的最深处。
作者:张怡微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舒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