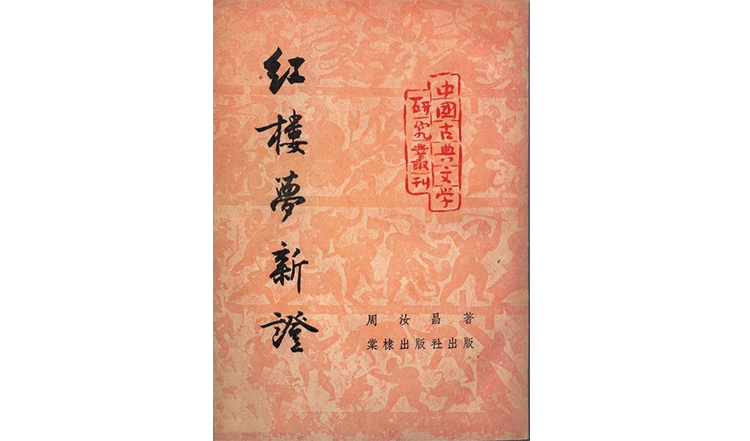
1953年秋,拙著《红楼梦新证》刚一出版,即奉一册与老师求正。从先生的来函看,知道先生开头是不敢打开《新证》就看起来,所以拆封之后,仅仅欣赏了一下封面,并不预备读下去,而是恐怕我的白话文让先生大失所望。又知道他开始看的是下半部,是对脂砚斋批语的研究。这表面看起来是一种偶然现象,但在我个人的感受中却觉得里面包含着很多方面的内容和原因。我曾仔细玩味先生信函中的每一句话,作出我自己的感受和有关的揣度,例如:先生为何不从开头第一页看起而一下子翻到了后面论脂批的这一部分?一般人可能对此不作深思,我却不然。我的想法是先生不是没有从头打开,而是打开先看了目录,看到前一大部分,比如人物的考证、地点的讨论、书中日期的讨论、对于清代历史的研究等等,没有立刻引起最大的兴趣,而一见脂砚斋与史湘云的这一部分,先生便立刻细看起来,而且兴致如此浓厚,评赞如此逾常。这,正好说明先生在1947年秋冬来函嘱我“不佞欲玉言将来成为文人,而不必成为学者耳”的那番深意。因为《红楼梦新证》的前半部分正是那种学者味较浓的考证文字,而一入脂批的这一部分,立即显出了我自己擅长的貌似考证而兼有诗情境界、感悟成分的这种文字。换言之,那种学院派处处要有“学术规范”的文字是没有多少生气的死文字,而能把考证写成活泼而意趣盎然的新鲜体格是不易多见的活文章。先生喜欢后者而加以赞赏,虽有溢美之词,也就绝非偶然的事了。
说到这里,还让我提醒一句,就是1943年底,我刚一接到《苏辛词说》时,看那讲稼轩词的第一篇《金缕曲·咏琵琶》,整个儿的讲说就是为了指点写作文学首要的在于一个“活”字。
读一读先生对于《新证》的那样高度的评价,有人会说:一位名师对他的学生弟子的著作会给以如此这般的赞许文辞,这未免太过分了吧?这是真正的客观评价吗?内中恐怕含有不少的感情成分。
我答:所谓感情的成分我自然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自从1942年起始到1953年出书,已历十一年之久,先生对我特加青眼,关切、爱护、指点、教示,种种深情厚意,信函用语,虽然亲切,但总是非常委婉谦慎,并无丝毫过分的宠爱之词。那么为何十一年之后一见《新证》,忽发如此令人大有“石破天惊”之感情爆发?若认为这仅仅是由于一些师生感情的作用而如此下笔措辞,那对先生的为人、立论未免太欠理解和尊重了吧!
我见先生对《新证》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自然是喜出望外。我不想假谦虚,对先生的赞语只一味不敢承当,那样不但自己不诚,也就等于说先生的赞语也都出于不诚了?那我如何对得起先生的一片热情和激情呢?
先生对我的赞许和奖励,有两次是用了“三长兼于一体”的分析综合法。第一次先生说的是:“风格之骏逸、文笔之犀利”,后面又作“文笔之工、考据之精、论断之确”;第二次则是说《新证》“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这两次的评语先生赐予了我,不但是我个人的光荣,也是先生论文谈艺的重要标志,所以我在此试行讲自己的体会,述说一下,可供后来的学子作为一种学习的借鉴。
先说说什么叫“俊逸”(先生用的是“骏逸”)。当然,学文的皆知唐代诗圣杜少陵有好几首怀念李白的五言律,其中一篇写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我每读此篇,便被杜老的那种好句和深情所感动。由于这篇诗的腹联两句,便留下了“暮云春树”这个四字的典故,意思是说我在渭北,你在江东,我在此地所见是春天之树,而你在江东我只能望见一片远方的暮云——然而这一联上面的“清新”“俊逸”,在文艺、诗歌理论和审美上的重要意义却未见有令我倾心满意的解读说者。“清新”二字较为好懂,“清”是气清而不浊,“新”是鲜亮而不陈旧,能得此二字之评语已非容易——恰好,在1942年4月7日(农历二月廿二)先生给我写信的开头已然说过“大作清新有余而沉着稍差”。说老实话,上世纪四十年代,我的诗词并不十分成熟,但有时却真能写出几句不浑浊、不陈腐的佳句来。但是至于“俊逸”二字,先生从来未见许过。可见这二字的境界就比清新要高深得多了。
如今要想懂得“俊逸”的真义,却先要懂得什么是风格。这些中华文化上的独具特色的词语要认真细讲起来,就非三言五语所能说清的。我此刻为了简而又简,节省读者的精力,就采取一个最为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借用刘勰大师的《文心雕龙》里的一个审美标准,叫做“风骨”。《文心雕龙·风骨》篇说:“……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这段话,重要无比。原来,文学上所谓骨力的劲健,那是文辞上的事;而风力的骏爽,则是文气上的事。这个分别,并不总是被弄得清楚的。所以“清新”、“俊逸”,不是别的,就是气质,就是风骨。
我不但要借《文心雕龙》来助解,而且还要引一下《红楼梦》一起来讲说这个重要的问题。请你打开《红楼梦》第一回,就出现了一僧一道两位仙师。曹雪芹是怎样形容他们的呢?道是:“气骨不凡,丰神迥异。”好了,这八个字,一面是气骨,一面是丰神,这不恰好就是风骨风格的最好释义吗!所谓“不凡”,就是不一般,不平庸,不低下,在大众之中独是出人头地,高出一等。这个就叫“俊”。你看,俊是“单人旁”,所以是形容人之不凡,如果换了“山”字的偏旁,成了“峻”字,岂不就是形容山的高出众峰了吗?俊字的本义讲明白了,然后再看那个“逸”又怎么讲?巧极了,我也可以引一下《红楼梦》来再作为助讲者。有一次,贾宝玉受他父亲的召唤来到正房,侍立一旁,他父亲举目一看,只见他是“神采飘逸,秀色夺人”——请看这个“逸”字,恰好就又出现在形容一个人的风采气度时而令人特别感受的出现了。逸者何?也姑且简而言之,就是不顿、不滞、不低、不笨,有飘飘超越一般人间境界的感觉。——好了,我这么一讲,岂不成了我自己把自己夸奖得令人发笑了吗?
当然,我的本意是若不用此法来讲清“风格之俊逸”,那就不是本书体例篇幅所能容纳的了。所以不必怀疑,借此为一个方便的手法来说明先生之所谓“风格之俊逸”者,就是说作文首先要有一种超脱平凡、不落尘俗的气味和境界,这就是“俊逸”的基本意义。它是形容文章风骨的特用词语,也就是中华文化上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审美标准。(本文为周汝昌先生遗作《苦水词人念我师》中的一节,由其女周伦玲整理提供,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周汝昌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