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骆一禾
这远方的太阳:深渊的火
精神寒爽,独自灿烂
不使我们被庸人和时代所赦免
——骆一禾《世界的血·第二章·第二歌》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禾是我的良师,80年以来我受益于他,以至在他病逝之后我竟觉得恐怕在我将来的岁月里,再也不会遇到一个象他这样近乎接近完美的人,以至我竟觉得真实的他此刻依然上升,而我们这些留在大地上的人不过是一些幽暗的身影,出没于街头巷尾,纸张书籍之中。
海子自杀后,一禾曾对我说,现在,他只有十个朋友了。我有幸属于这十人之列。然而这样一位高尚的诗人,直到他去世,我才发现自己对他知之甚少。他身前更多地是去帮助别人,了解别人,谈论别人;我们在一起时他则更多的谈论海子。只有一次,一禾几乎谈到了他自己。那是在1989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在我家里,我给他看一本法国人奥斯卡·德韦尔所著的有关占星术的书。一禾的星座是宝瓶星座,主宰行星是天王星。我给他读了书中与他有关的章节:“宝瓶座的人是新思想的开拓者,如果给他以完全的行动自由,让他随心所欲地去思考和决定,那么他会表现出卓越的工作才能。他是一个创新者,层出不穷的念头和突如其来的直觉,使他能预感到未来。”“(他的)才能几乎全部集中在智力或精神生活方面。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有敏锐的直觉,并富有幽默感。……他对于一切开拓性的事业、发明创造、前沿科学、改革创新和神秘学都有浓厚的兴趣。”
……一禾始终微笑着听我读书,待我读完,他说,书上说的基本正确。那天晚上他临走时借走了这本书。去世前他写有一首题为《壮烈风景》的短诗,诗中写道:“星座闪闪发光/棋局和长空在苍天底下放慢/只见心脏,只见青花/稻麦,这是使我们消失的事物。”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说道:“让他的目光脱离自己周围卑微的事物吧。”“我们不再攀登高位而攀登永恒。”如果说思想是人类的使命,人类最高的义务,那么诗人骆一禾恰好具备真正宜于思想的头脑,并且在他平和的面貌和随便的衣着之下,有着他对于诗歌艺术的严谨态度,对于苦难人生的关注,以及对于宇宙大真理和万物之美的迫切向往。现在,由于一禾的死,我们有了谈论和倾听他的机会——骆一禾,1961年2月6日生于北京,祖籍浙江临安,少时曾从父母在河南省农村劳动。1979年秋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出版社《十月》杂志编辑部工作。1989年5月14日凌晨因长期用脑过度和先天性脑血管畸形而出现大面积脑出血。在北京天坛医院昏迷18天之后,于5月31日13点31分去世,时年28岁。
一禾之死看似偶然,而其实却与他所从事的事业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一个以诗歌为装饰或游戏的人,不可能象他那样切实体味到“诗歌的深渊”。在那巨大的深渊里,这个勇敢的人搏击,翱翔,尽管有时恐惧,有时感到孤独,但最终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形而上的上帝的秘密,表现出人的正直。
海子生前在同我谈到一禾的诗歌时,曾说一禾的诗是从一株青草生长起来的大树,因此带有本质的单一性,与其同旋的思维方式形成对照,在我看来,一禾的诗歌以爱为根,结成幻想的果实;只是这幻想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形象为出发点的幻想不同,一禾的幻想与其哲学性的宽广的沉思有关。究竟其宽广的沉思以什么作疆界,我无法说清,但沉思对于一禾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沉思中听到了血涌,并起立歌唱。相信凡是读过一禾早期诗歌的人,都会同意,一禾早期的诗歌大多是温暖的,注重细节和场景的,且以亮色为主,在语言上表现为平易,在内容上表现为青春。在一禾行将自北大毕业时,他曾抄录了一册他自己的诗歌送我,我对那些诗歌的印象大致如次。1985、1986两年,是一禾深入思考诗歌的两年,其间几乎搁笔,后来他开始了雄心勃勃的诗歌创作,写下了分别长达三千行和五千行的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
《大海》我不曾读过,《世界的血》我也只是大略通读过一遍,不能说有深刻的理解。《世界的血》分六章:第一章“飞行”(合唱),第二章“以手扶额”(祭歌),第三章“世界之一:绿色生命”(孤独动力),第四章“曙光女神”(颂歌),第五章“世界之二:本生生命”(恐惧动力),第六章“屋宇——给人的儿子和女儿”,我们仅凭长诗各章的标题便可想而知,这部长诗是谨严构思的产物,排除了一时一地的思想火花,放弃了仅仅依靠灵感的写作方式。这部长诗以血为核心,以人的孤独与恐惧为两翼,展开生命的主题。面对苦难,死亡和黑暗;“黑暗是永恒的,而光明/必须运行。”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看,《世界的血》属于荀子那一路创作。主题是肯定的,人在天地宇宙间有其积极的作用。心灵的眼睛既看到了万物严酷的一面,又看到了万物壮丽的一面,心灵把真正的死亡称作“牺牲”。从这部长诗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具体的场景和细节,有的只是紧张的幻象,仿佛诗人自身已经高高升起,无所不在,与此相适应的诗歌语言陡峭而绚丽。
与其说一禾在其晚期诗作中所着意描述的是天堂,不如说是充满了噩梦的地狱。但在这地狱中没有堕落,只有搏斗。
海子曾称一禾的诗歌以大海为背景。他说这话的根据大概是一禾的另一部长诗《大海》,对此我没有发言权,但是请相信海子的话,他的看法不会有误。
一禾曾有一个宏大的构想,那就是海子、我和他自己,一起写一部伪经,包括天堂、炼狱和地狱,这部伪经现在是无法完成了。
一禾还曾跟我谈到过他的另一部长诗的构思。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写出一座城市,在大海之下——其规模大约与十六世纪意大利多米尼克派僧侣奥凡。康帕内拉所描述的“太阳城”有某些相似之处——只有穿过大海的人才能抵达这座城市。但这部长诗他同样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了,我宁愿把这座城市看作已经完成的一禾本人。
或许有人会认为一禾的创作应该属于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文学观念虽然高级,但是经过本世纪初欧洲现代派文学及我们时代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冲击,这类观念已经显得陈旧。然而,对于文学的潮流,一禾有他自己的看法,简而言之,即登上顶峰的文学就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学。诗歌自精神始自精神终,其灵光不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减弱,亦不因种族、地域的差异而变质。这正是里尔克在本世纪初所表达的观点相同:艺术作品应当具有“共时性”,它们都是人类各种“向往”和“恐惧”的“物化”,古典艺术、中世纪艺术和现代艺术之间存在着不间断的延续性。
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学,一禾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以为这类聪明作品的产生,说穿了是作家心力的底下。他曾经兴冲冲地给我读《世界文学》1987年第4期是刊登的美国批评家本。德莫特所写的《六十年代是否损害了小说》一文:“这些作家这一些最能引起兴趣的人,有时候活象暗中勾结在一起,在通力合讲一篇故事,而且只有一篇故事,主题一成不变,就是人间的无情。”他们要向我们指出——简直无休无止,不遗余力——人们在相互观察,期待着病态的反应。“在一禾看来,这种情况已经渗入中国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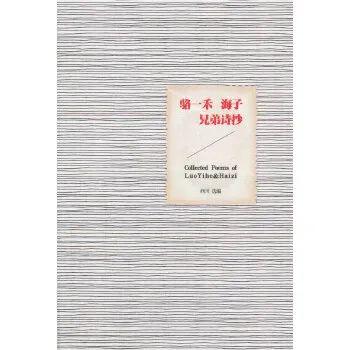
西川 选编《骆一禾 海子 兄弟诗抄》
所以我把一禾的死看作中国健康文学的一大损失。有他存在,就有一种尺度存在 。我在这里回忆的,不过是一禾全部思想的万分之一,而且不能说是他最重要的思想,它们有些已随一禾而去。一禾去世以后,曾有一位朋友来信,说海子选择了死,所以他干干净净地去了,而一禾未曾选择死,所以他至今依然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生活在我们中间。这当然是一种美丽的说法,不过对我来讲,一禾的确已经不在了,虽然有时我还在夜晚梦见他,但1989年6月10日在北京八宝山,是我和别人一起拉着他的灵床来到火化室门口,事实总是这么残酷,哀莫大焉。
1990年2月20日

诗人西川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