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切和发声,东欧哲学家齐泽克在3月18日提醒政府和民众除了医疗危机、经济危机,还有容易被忽略的心理健康危机,同时也应警惕类似“适者生存”这样违背生命平等的声音。以色列历史学家、《人类简史》三部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3月24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则呼吁全球应团结合作,特别是重视“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和知识”。

新冠肺炎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态势,也让不少学者重新思考东西方文明在面对危机来临时的不同思维模式。比如,中国在疫情趋缓之后,积极驰援全球其他国家,其背后的思维模式有着深厚的传统因素,正如下文所提到的,传统文化里推崇的学人永远是站在利己主义者的对面,“一个人只有在某一天能超越自己,放下小我,走向大我,也就是超越个人的利益得失,而思考天下问题的时候,他才可能走向真正的学问之路。这就是知行合一。”
同样被纳入考量的还有“科学”一词,缩小到疫情相关的问题则是中西医效用之争,事实表明,中医在此次防控疫情方面广泛介入,和西医结合形成了很好的疗效,医生张文宏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特别提到了“上海的治疗是中西医结合的,而且合作非常愉快”,这也能理解为何中国对欧洲部分国家的医疗援助之中有中医的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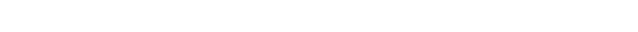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评论家徐兆寿特别对此展开了探讨,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医被怀疑乃至否定,都是因为衡量的尺度是“西方科学世界观的检验,说透了就是微观世界的检验”。进而提出了沟通的前提,“为什么我们不拿中国文化去重新衡量西方文化呢?只有彼此否定不了的东西,可能才是我们沟通的桥梁。”
(本文首发于文学报3月26日)
疫情面前,我们该如何思考和行动?
——写给高校青年学子的话
文 / 徐兆寿
农历二十九日我去甘肃武威,大年初一赶回。回来以后就开始在家里观察疫情,想做些什么,写过几篇文章和毛笔字抗疫,但感到无力,便想到张载的故事,于是开始研究,并写作《传统四书》。现在写了二十多万字,也在有意识地回答中国文化怎么办,包括中医怎么办的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特性是什么,在传统性格上与西方文化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如何将西方文化的优长中国化,也就是鲁迅的拿来主义怎么拿来和运用的问题。
我将中国传统文化最后归纳为十六个字,便于记忆:道法自然、中庸之道、礼教之道、君子之道。
如果套用今天的词汇来讲,它是中国古人的核心价值观,从大到小,有世界观,有方法论,有准则,最后有结果,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这是我讲了十五年中国传统文化后的一个小总结。
这也是下面谈论疫情话题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基础。
历史上一次瘟疫毁了一个国家的情况太多了。这时候,我们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即知识分子、读书人如何选择命运。新时期以来的几次选择我都是经历者,记忆最深的是1993年左右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持续了好几年。知识分子非常地焦虑,很多作家和学者都参与了。从那以后,大规模的讨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很多人说,这才是正常的。其实,我深信每一次国家的选择都是知识分子新的选择之时。这次疫情虽然看起来不是什么大时代的转折时期,但它的灾难之大仍然迫使我们思考,在国家危难时读书人该怎么做,在各种文化喧哗之时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些难题。这样一想,它也就变成了大时代的问题。每当这时候,我们都会回望历史,看看历史上那些先贤们是如何做的。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张载。
范仲淹做不到的,张载做到了
二十岁出头的张载觉得书生无用,便投笔从戎,奔赴前线,欲为国家效力,这是超越了自己。跟鲁迅先生一样,要去学医救人,是士,是仁者。他去找范仲淹。范仲淹是了不起的文人,他说,你一个书生,又不懂兵法,能有多大的本事杀敌立功?你也不是医生,不能救治伤员,你能做什么?
张载一时语塞。范仲淹说,你要认真想想,你在这个世上能做什么,什么才是你真正要做的事,现在国家有难,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问题,还有整个国家的精神问题,如果精神不立,再多的人也无法抗敌,而立精神的事就是你要做的事。
张载一听,顿有醍醐灌顶之感,也像鲁迅弃医从文一样,立刻返回家里,钻研圣人之学问,所以后来就有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命,就是要在危难时分为百姓代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人民说话。为天地立心,就是要参透天地的大道,再研究人的事情,即究天人之际,再把历史搞清楚,即通古今之变,但这些都离不开圣人的绝学,反过来说,不参透圣人的绝学,也就没有前两者的立命立心,把这些都做好了,最后就可以为万世开太平了。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就是周公、孔子等圣人,要在精神上把人立起来。所以,张载的选择便是读书人最高的选择了。这一点,范仲淹想到了,但无力去做,要让张载去做。

在这个时候,读书人就分了工,范仲淹前线抗敌做英雄,并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呢,在后方读书写作,重立圣人之学,也有横渠四句。其他人也是分做各的事,各有各的建树。有些人要在战时用,有些人则要在战后用。
我借此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每个人做自己能做且能做好的那个事,尤其是善事。医生如李文亮、专家如钟南山和其他专业人士做了他们的分内事,都是他们擅长的事,既有良知,还有担当。还有许多医生、护士、记者、军人,都在做他们分内的事。甚至快递小哥做得也很好。当然,还有很多公益人,就更是了不起。前线的人可以做英雄,后方的人处理好后方的事也很重要。我很惭愧,觉得不能为这件事做什么,感到无力。虽然前后写过三四篇文章,给省上也有三份文化方面的建议,还在微信、微博上为中医辩护,但都感到这些发声太无力,最后想到张载的事后也是有些恍然大悟,放下小说写作,潜心研究,希望有所发现,对社会有所助益。
学子们如何思考与行动
作为学生,第一使命就是求学,把分内的事做好。我也曾要求我的本科学生们要有家国情怀,要积极地去做些什么,不要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疫情到来,有些同学走上街头,做了志愿者,有些同学积极做公益活动,但大多数同学在家关注疫情。我最终觉得让他们读书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了,在家里一边关注疫情,一边静静地读几本中外经典名著,尤其读几本中国古代的名著。
其次,就是能发声的时候,尽量的去发声,维护社会的正义,维护社会的公平,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读书不为公义,读书就是一件可耻的事。我记得小时候村里若有一个读书人不讲理,村里人就会骂,读书读到驴肚子里去了。因为读书只为个人利益,也不读圣贤书,没有道义,没有德行,还怎么敢称读书人?我觉得最近教育部出台意见破除“SCI至上”就是一件好事情。它就是让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的人明白,科学研究是要研究一些真问题,解决社会的难题,是要完善自己的道德,也是要在国家和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能挺身而出。这才是国家的栋梁。
最后是进一步思考疫情之后中国人和人类怎么办的事,包括我们自己如何过好后面的人生。一生中,我们遭逢了这样的大疫大难,能看到社会百态,定然也会被社会的各种情状所触动。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没能触动你的意志和情绪超越自己,那么,我们要么就是无用之才,要么就是利己主义者,要么就是时机不合适,那就有待以后的命运开示你了。一个人只有在某一天能超越自己,放下小我,走向大我,也就是超越个人的利益得失,而思考天下问题的时候,他才可能走向真正的学问之路。这就是知行合一。在中国文化中,学术不是知识的凌空蹈虚,而是既要面向个人的道德完善,又要面向社会的实践,能够知行合一,这样的学术才是真的学术。
从加缪开始,重新讨论一些深沉的文化命题
在整个人类的文化中,只有中国与古希腊文化是以人文理性精神为主的文化,其他地区的文化基本上是宗教文化。人文精神主要是人在起作用,即使有神存在,人的精神也是起主导作用的,也就是说,人类用自己的精神能够去表达神的意志。古希腊三哲如此,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墨子等都如此。但是,两种文化处理世界和人生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结合与疫情相关的作品来谈,我们可以以加缪为切口。
加缪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之一。他与萨特原来关系很好,后来破裂。他们都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加缪得奖的时候很年轻。我喜欢他的《局外人》,更喜欢他的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的神话》,这部作品对我影响至深。萨特也是,他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是至高的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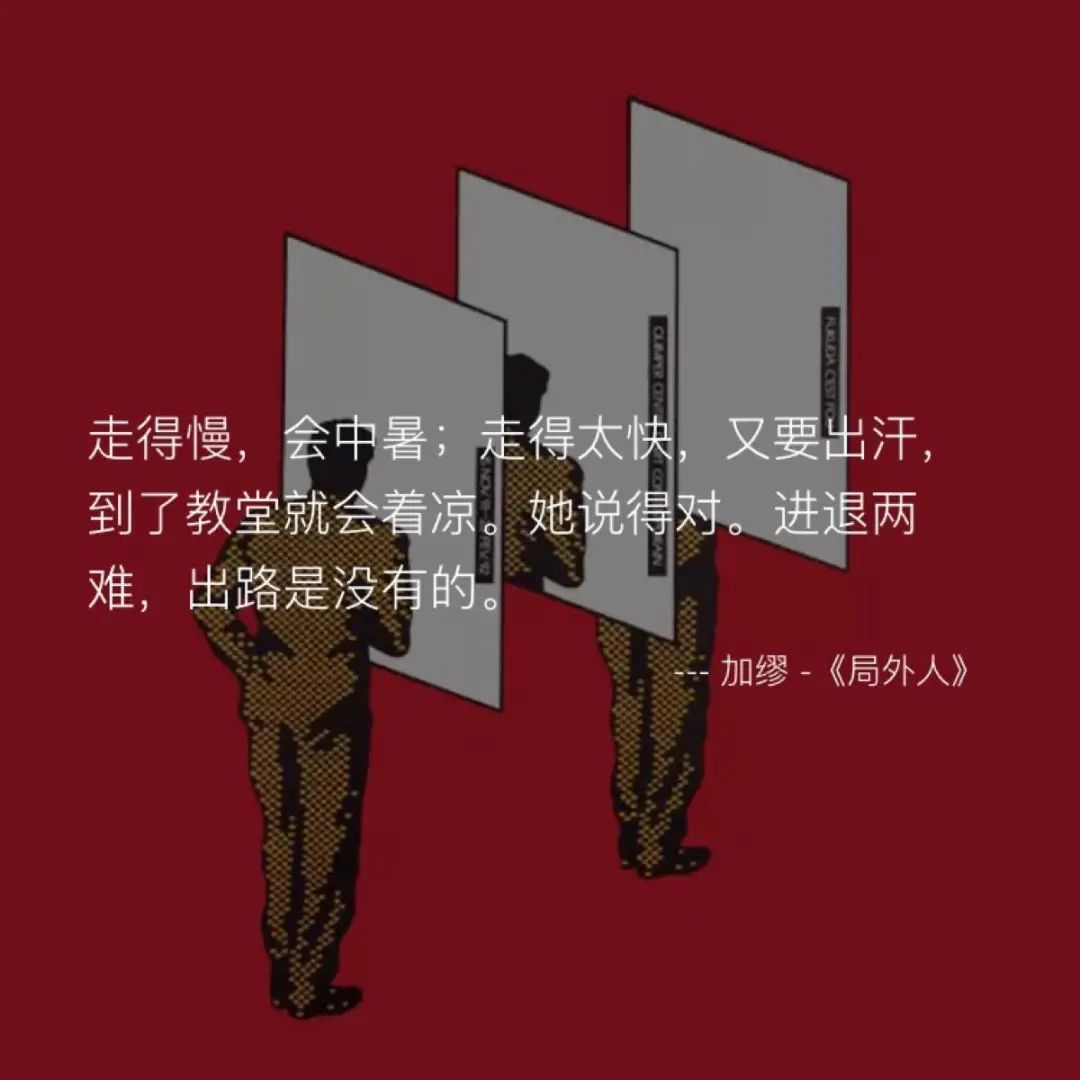
从大的方面说,西方文化是“两希文化”融和的结果,一个是原有的古希腊文化,它的中心在欧洲不断地发生位移;一个是古希伯莱文化,后来其实是基督教文化。两千多年以来,它们也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罗马时代是它们逐渐合起来的时期,文艺复兴是它们第一次分离的时候,迫使基督教进行改革,近代以来,在科学主导的工业革命开始,又是它们分离的时候,从哲学上来讲,大概是从黑格尔以后吧,我们现在能想到的那些哲学家、文学家几乎都是。尼采站出来宣布了上帝的死亡,然后便歌颂古希腊的诸神,回到希腊文化中,甚至都不是三圣哲学时代,而是直接回到了荷马时代。但加缪又否定了希腊诸神,要西西弗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蔑视诸神的伦理规矩。萨特基本上不再讨论神的问题,是在加缪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人如何在日常中建立完整的命运观和人道主义精神。海德格尔、索绪尔等则回到了人类的原初语言中去寻找人类原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试图重新为人类寻找新的文明尺规。马克思与尼采一样,是彻底否定基督教的哲学家。所以,总体来讲,他们是返回到古希腊精神中去了。他们在不断地返回到传统中去创新自己的文化和精神,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科学”一词
中西医问题,是目前大家在网上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我是持中西医结合的态度,但有时不免要为中医说几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中医有误解。不仅如此,搞中医传播的人把中医又进一步神秘化,甚至妖魔化。这对中医实际上是不好的,所以我也批评这种现象。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中医。目前我们对中医的认识并不是站在中医的角度去判断中医,而是站在西医的角度去丈量中医。也就是当我们要说A和B的优劣点时,我们没有拿一个中间尺度,或者说,如果没有中间尺度,我们至少可以站在各自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我们直接拿A的尺度去说B好不好,科学不科学,这本身是不公平的。
西医来到中国时就是跟着科学进来的,而那时的科学就是与宗教与传统文化相背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的科学是一种经验化基础之上的理性工具,是实验室系统,是物质的微观化,即使我们拿望远镜去观察太空,也是通过机器的角度去观测,它放大了我们的眼晴,但是,它也同时让我们开始否定我们的经验,否定我们的眼睛,最后是否定机器没有观察的所有一切。这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但它正在发生,且在控制着世界。

拉斐尔《雅典学院》(1510-1511)
梵蒂冈博物馆
但是,我们别忘了,如果往古代上溯,我们会找到古希腊的哲学家那里。我们会说,那时候希腊的哲学家是科学方法,他们中有人发现世界是由水构织的,因为他们看见大海,看见尼罗河的潮水在决定着世界的秩序;他们中有人认为世界是火构成的,因为他们崇拜太阳神,看到太阳对万物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中有人认为世界是由土组织的,还有人认为世界是由气化而成的。瞧!这与中国人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很相似吧?可是,今天仍有人认为五行学说是迷信,而古希腊人的那种探索是科学。可见,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一种新的迷信。这使我们不能站在中立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的传统。
还有一个人是极有意味的存在。他叫德谟克利特。他把上述这些思想都进行了考察,并到当时的希腊半岛、中东地区甚至印度去学习过,还跟巫师学习过天文学,那时叫星相学,最终他说,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而物质是由最小的原子组织的,所以我们欣喜地认为,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总之,世界是物质的。
但是,我们忘了他还说了另一句话,那就是在原子与原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虚空,而这个虚空是不为人知的。就是因为不听后面这句话,我们的认识便缺了一半。这就是科学所无力达到的。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就是只有阳,没有阴。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就是只说身体的细胞,而不管细胞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虚空。那就是人的呼吸。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细胞还在,可是人死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死了呢?我们也许有人会说,是细胞间的呼吸停止了。可是它们不是物质啊,我们在说科学的时候,在用放大镜、显微镜透视的时候并没有在乎过那些虚空的存在。
所以,我们引进的现代科学只是认识世界的一部分而已,但我们将它当成唯一的尺规。当我们再也看不见那些虚空的存在时,我们只知道人是需要吃的、住的、穿的、行走的,可在虚位上存在的道德伦理呢?难道不需要它吗?显然是需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需要,但我们如何在实验室里建设人类的道德伦理大厦呢?
中国古人说得好,这世界上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叫知,另一类叫未知,合起来才是知识的全部。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过去我们解释得片面,他的本意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意思,把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全部加起来,就叫真正的知,也可以说是智慧。知道的和看得到的东西称为阳,看不到的和说不清的称为阴。这才叫科学。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拿西方“科学”一词而把我们的一部分文化否定。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科学”一词。
中医就是被这样怀疑和否定的,因为它不科学。这里的不科学不是中国的科学定义,而是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定义。为什么我们不拿中国文化去重新衡量西方文化呢?只有彼此否定不了的东西,可能才是我们沟通的桥梁。是我们自己把天平放斜了,这怪不得人家。比如,中医是靠阴阳五行思想发展而来的,后来还和《周易》、天干地支结合起来发展了经络学,也就是针灸学。它有什么大的问题吗?西医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没有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它就简单地否定了这些运行了几千年的理论。但中医呢?很委曲,它面临着西方科学世界观的一次检验,说透了就是微观世界的一次检验。
我认为这个检验也非常有必要,它在检验中可能是对的,但我想,有一些很可能就是错的,因为中医是不固定的,与人的天赋和经验有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如果我们根据西医的人体解剖学把这一学问纠偏和进一步完善,岂不是更好,岂不是可以造福全人类。所以我想,这对中医也是好事情。
我不赞成简单地信仰西方文化和西医的科学观念,也不赞成简单地否定中国文化和中医理论。以我十五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研究和十二年对西方文化的教学思考,深觉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真正可取的态度是中庸之道,取长补短。
这是疫情带给我们的副产品,其实是更为深沉的问题,它反映了我们人类精神文化中的病理现象。它已经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但首先要我们中国人来解决。从某种角度来讲,能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一种幸事。
作者:徐兆寿
编辑:郑周明
责任编辑:陆梅
*文学报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