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全国各地已陆续复工,许多网友在怀念着何时能去武大看樱花,但疫情依然在继续,人们坚守着,保持期待。从春节以来记录着疫情下生活与思考的“此刻·我们”栏目也会继续分享给大家。
漫溢的情绪,首选诗歌去承载。这些天,来自武汉方舱医院一名护士的组诗感动了许多读者,看了太多第三方的描述之后,来自现场的真实感受让诗句呈现了质朴的震撼力。
疫情之下,有人期待诗人们尽快写出鼓舞人心的诗歌传之四海,也有人认为,此番情境如何还有心情读诗?相信这是许多人的疑惑,而这种疑惑,来自于诗歌长期被赋予了实用的功能,但是,不妨发问,这种两难如何而来?
今天分享的思考来自诗人、翻译家汪剑钊,他为诗歌的功能与发生机制提供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也将近期引起争议的那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放回到原文语境中给予了解释。归根结底,我们要尊重每个个体的选择,每个人的写作习惯,以及内心的诚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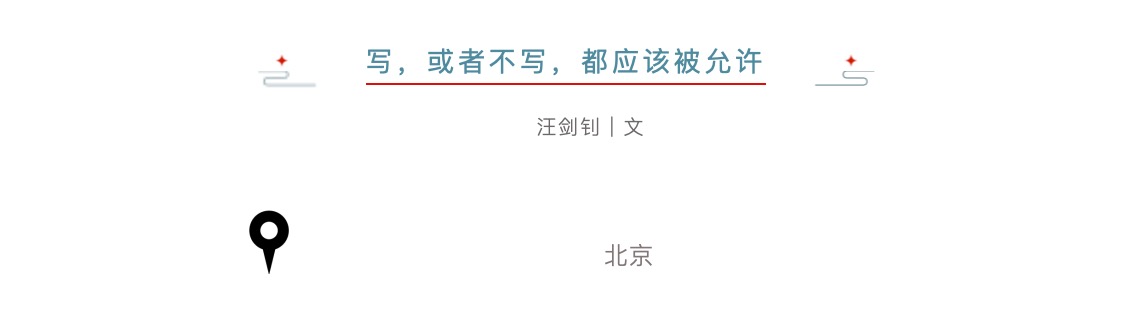
最近,有友人发来微信,向我提出了如下的问题:“疫情发生后,怎么还有心情读诗,听诗,又如何写得出诗?你如何看待诗在生命中的意义,尤其是灾难,变故,困境之中的意义?”我想,这些个疑问不仅存在于这位朋友的心中,而且也是相当一部分人面对诗歌与现实时可能产生的一个普遍性迷惑。它们值得每一个诗歌写作者认真的思考。
我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明确诗歌的功能和它的发生学。诗人受某个人、某件事或某一场景的刺激和引发,开始于“非说不可”、“不吐不快”,随后,他(她)的脑海里便出现了词与词之间的互相运动,它们交接、碰撞、摩擦、和解、融合、重组与亲密……于是,最初那些模糊的碎片逐渐向一个清晰的目标靠拢,由一个点伸展为一条线,再由线的生长扩展到面的溢生,最终定格于一首诗的完成,中间有普遍的规律,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从社会学意义上说,诗面对的是整个世界,表达的是丰富、复杂的人性,它要体现人对善、真、美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在求索过程中所暴露的软弱、缺陷和不足,包括内心的各种活动和外界的多重刺激,自然与社会的对立统一,时间和空间的纠缠与变幻,等等。概而言之,诗是语言的艺术,是人类对具体的万物进行抽象的结果,但又指向一个新的具象,一个由词语和声音重新打造的新空间。

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在他的著作《文化批判与社会》中说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断言,也常常被某些人用来指责诗人对一些天灾人祸或者突发性事件所作出的诗性反应。这里,我想说一下个人的理解,首先,阿多尔诺在说这句话时有一个背景,那就是纳粹分子曾在集中营举办音乐会和希特勒本身还是一个小有才气的画家这样的事实,这些所谓的“艺术”实际就是对人性的一种无耻践踏。其次,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存在的同时,一部分艺术家、诗人无视劫难的存在,继续进行反现实的创作,一味地吟风弄月,营造歌舞升平的假象,他们在客观上起了一种帮凶作用。其实,阿多尔诺在那篇文章中还有一个思考经常为人所忽略,那就是“今日写诗何以可能”。他本人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想,他应该有自己的立场,那就是倡导一种否定的艺术,对技术时代戕害人性的做法予以抨击,重塑美好的人性。这就是说,阿多尔诺并非完全否定诗的存在,他拒斥的是那种虚假的、粉饰的诗,而呼唤一种有生命热度、有力量的诗,给人以思维上的警醒和精神上的提升。
中国有一个“诗言志”的传统说法。关于这个“志”,较常见的有两种看法,其一,指的就是诗人的志向、抱负和理想;其二,指的是记忆,诗人的任务就是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对这两个释义,我觉得都是合理的,也都能够接受,它们也是诗的意义所在。因此,我也认同“言为心声”的观点,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人,他要维护人的生存权,关注个体的自由、尊严和个性;同时也必须承担社会性的责任,利用自己的文字能力在公共领域发声,为人类的正义、幸福尽自己的力量。正是有着这样的预设,诗也相应发挥着与其他艺术门类、其他媒介、其他文体相同或不同的作用,它抚慰人们的心灵,表达个人的喜怒哀乐,全人类对真理的探索、对美的憧憬和善的呼唤,对假恶丑的揭露与抨击。我认为,诗人是时代最敏锐的感应器,所谓“愤怒出诗人”也恰恰是感应的最好例子。诚然,诗因其特殊的生成和传播,有着一定的非实用性或“无用性”,有时甚至还显得柔弱、无力。殊不知,力量有时就蕴藏在这份看似柔弱的坚韧中,就像温柔的水滴一样,具有穿石的潜力。因此,大疫当前,读诗、听诗和写诗,都有它的合理性,加之诗歌本身还具有柔能克刚、摧刚为柔的转换能力,更是为前述行为保持其连续性上提供了超越文学之外的依恃。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诗人在写作中的感应显然不同于普通人的感应,它需要显示其职业性的特征,也就是说,他的愤怒应该是诗人的愤怒,书写的文字必须符合诗的要求,充溢于笔底的良知必须是诗性的挥发,在情感表达、想象力的激发和词语的组合上,显示出一定的创造性。涉及到灾难诗或当前的疫情诗写作,那就是它们必须是货真价实的诗,而不是简单的口号,不是粗制滥造的散文之分行,不是词语的堆砌,更不是假大空的献媚和点赞。我觉得,判断一首诗的好坏,情感的真挚与否当然是第一位的考量,与之相关的就是审视其表达方式是否具备美学意义上的个性,遣词造句是否达到了陌生化的组合,辨识诗中的词语哪些是真正来自作者的内心,哪些属于从其他地方“租赁”和“窃取”来的,其中尤其要警惕那些通用性的大词、圣词。说实话,当一个诗人不断使用从别处借来的陈词滥调时,他所抒发的东西又能有多少“真挚”与个性?顺便说一下,目前有一部分“抗疫诗”跟当年汶川地震时铺天盖地的那些“抗震诗”有得一拼,尽管打着正义、良知、仁善的旗号,但都不过是一种肤浅的文字喧嚣,作为作者自身的个人宣泄,大概有一定的作用,倘若因此就将它们看作是诗,则无疑降低了诗的美学品格。至于一部分“冠状君”式的“作品”,实际还传播着语言的病毒,对现代汉语进行了严重的污染。

特殊事件或灾难来临之际,我们无须对所有人的行为作千篇一律的要求。面对疫情马上有感而发,写出真正反映疫情的诗歌,或鼓劲或针砭时弊,自然是大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诗人尚未产生深切的感受,不作即兴式的发声,也必须得到尊重,毕竟每个人的写作习惯不一样么。诗歌不是新闻,它也不可能以报道式的面目出现。况且,根据文学史的考察,如果与当时的人与事拉开一定的距离,反而更有可能出现杰出的作品,因为本质大多藏在现象的深处,需要时间来穿透。另外,我觉得,在特殊的时期,也应该允许诗人从事表面上与严酷现实无关的工作。例如,世所周知的是,俄国诗人普希金在1830年曾在乡下遭遇一场瘟疫。在交通被阻隔的情况下,他创作了数十首抒情诗,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几个片段,以“别尔金小说”为总题的五个中篇小说,还有几个小剧本。这一令人惊叹的创作成就在文学史上被称作“波尔金诺的秋天”。但耐人寻味的是,其中的大部分作品并没有涉及当时的那场瘟疫,不过,它们依然不失为俄罗斯文学的瑰宝。也就是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我们应该有一种宽容,允许每个人在无害他人的条件下作出自己的选择。诗歌有自己的伦理,它服从至高之美的律令,写或者不写,都应该诚实地服从自己的内心,写什么或不写什么,也应该由写作者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夺。
作者:汪剑钊
编辑:郑周明
责任编辑:陆梅
*文学报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