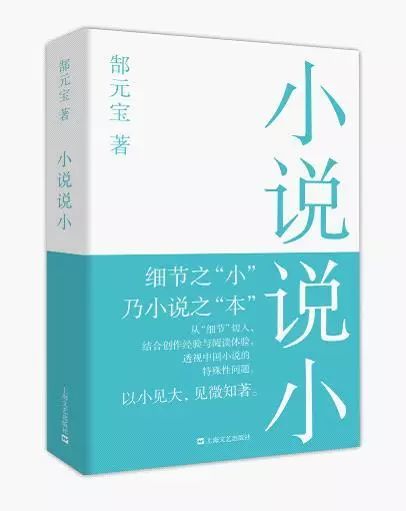
《小说说小》封面书影,上海文艺出版社
评论家郜元宝新书《小说说小》,近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力避架空议论,始终由衣食住行、人物场面、语言逻辑、视角结构、身体身份等细节切入,透视小说的写与读无法绕开的文化背景、历史脉络、意匠经营与人情世故。细节之“小”乃小说之“本”。例证涵盖中外古今,主体却是我们活在其中的“现当代”。博雅君子,将有小取焉?

郜元宝
我们读文学作品,遇到书中人物的服饰,无论繁简,恐怕都会一眼溜过去。其实在许多优秀作家那里,给人物穿什么衣服,为何让他(她)们这么穿,而非那么穿,都有讲究。
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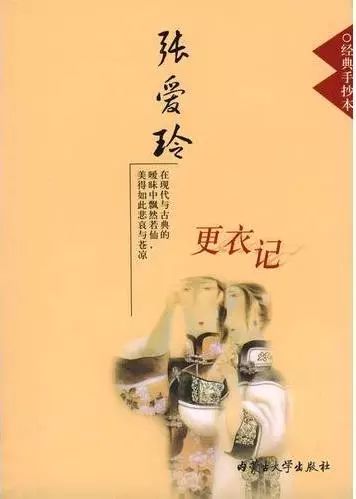
我们读文学作品,遇到书中人物的服饰,无论繁简,恐怕都会一眼溜过去。其实在许多优秀作家那里,给人物穿什么衣服,为何让他(她)们这么穿,而非那么穿,都有讲究。
小说故事性强,描写细腻,涉及衣物服饰更多。小说之外,作家们也会通过戏剧、散文、杂文等文学形式来描绘或探讨衣着打扮这一常见的生活现象。
张爱玲的散文《更衣记》就很别致。它当然不是写某人某次更换衣服的行为,更不是取“更衣”的委婉义之一“如厕”,而是概括地记录了作者所了解的一部分中国人从清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服饰变迁的历史,即什么时候流行什么衣服。这篇文章提到许多服装款式,光皮衣就有所谓“小毛”“中毛”“大毛”,棉袄的滚边则分“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诸如此类,今天的读者若非专门研究,会觉得很隔膜。好在我这里并不打算专门谈论张爱玲的这篇散文,只是借她这个题目,梳理一下现当代中国文学中有关人物服装的描写。至于衣服上过于琐碎的佩饰,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更衣记》告诉我们,张爱玲对衣着打扮很有研究。她18岁时写的散文《天才梦》结尾那句名言就和衣服有关:“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更衣记》里也不乏这样的“隽语”,比如说,“在政治混乱时期,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中国的服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男子生活虽然比女子更自由,但“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据说张爱玲还跟她的闺蜜炎樱合资办过时装店,自任设计师和广告文案的作者。日常生活中她的许多衣服都自己设计。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不怕惊世骇俗。她也喜欢借服装设计来探讨文学理论问题。比如她认为写小说要有“参差对照”,最好是“青绿配桃红”。
现在张爱玲的传记出了好多种,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她究竟如何设计服装,如何像同时代另一位有名的上海女作家苏青所说,喜欢“衣着出位”。
“月白背心”“长衫”“破毡帽”“寿衣”及其他
再看鲁迅。《故乡》写豆腐西施出场,“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除了“没有系裙”这四个字,豆腐西施穿了什么,全无交代。有读者就纳闷:那可是严冬啊,豆腐西施“没有系裙”,却可能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你能看出“圆规”来吗?这或许就是鲁迅描写女性衣着过于简单而惹出的麻烦吧。
再比如《祝福》写祥林嫂:“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完全是神态描写,不涉及衣着。
鲁迅说过,“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鲁迅这里指的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鲁迅不写祥林嫂衣着,只注重其神情,尤其是“那眼珠间或一轮”,和顾恺之说的是一个道理。

《祝福》舞台剧祥林嫂形象
《祝福》写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做佣人,“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这就凸显了衣着与身体两方面的特征,说明祥林嫂是干干净净守寡的女人。她虽然营养不良,但大体健康,甚至还有某种容易被忽略的青春朝气,而她的衣着也与这种身心状态基本保持一致。
隔了两年,祥林嫂第二个丈夫去世、孩子被狼叼走,不得已再次上鲁四老爷家帮佣,作者也再一次写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强调服饰依旧,说明祥林嫂生活贫寒,几年没添新衣,同时也反衬出她虽然服饰依旧,身心两面却都已判若两人。这就像《故乡》写少年闰土头戴“一顶小毡帽”,中年闰土则是头上“一顶破毡帽”。毡帽相同,闰土却不再是原来的闰土了。
说起毡帽,不能不说说阿Q的打扮。毡帽也是阿Q的“标配”。鲁迅对阿Q的破毡帽念念不忘,十几年之后,有人要把阿Q搬上舞台,鲁迅还特别提醒改编者“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他生怕改编者不知毡帽是什么,特地寄去一个画家朋友所画的头戴破毡帽的几张阿Q的画像。

电影《阿Q正传》剧照
鲁迅写阿Q,在服装上所作的文章,当然不止一顶破毡帽。比如阿Q和王胡之间的那一场打斗,就起因于他和王胡比赛在“破夹袄”上捉虱子。套用张爱玲的话说,生命对于阿Q王胡可不是什么“华美的袍”。他们只有“破夹袄”,而“爬满了蚤子”则没什么两样。阿Q因吴妈事件被赶出赵府,他给赵府舂米舂热了脱下来的那件“破布衫”也就拿不回来,“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片,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经过这一次“恋爱的悲剧”,阿Q被赵家和赵家所指使的地保盘剥得一贫如洗,“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万不可脱;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在“颇有些夏意”的季节,阿Q就穿着仅存的那件“破夹袄”和“万万不可脱”的裤子,仓皇离开未庄。
如果说鲁迅只对眼睛感兴趣,完全不写人物的服饰,肯定不对。“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寥寥数字,不就写活了孔乙己吗?再如《孤独者》写魏连殳登场,“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这固然是只写神态,不写衣装。但小说又写到魏连殳死后,只穿“一套皱的短衫裤”,这就暗示他做了官,花钱如流水,却依旧颓废,依旧不修边幅,依旧不为自己打算。
但《孤独者》最后,作者详细描写了怎样给魏连殳穿“寿衣”,“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嵌着很宽的红条,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金闪闪的肩章”。魏连殳就这样“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透过一套“寿衣”来刻画魏连殳一生的颓废,以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真是入木三分。
“摹本缎”·“二马裾”·“西狐肷的斗篷”
都说汪曾祺是“美食家”,善于写“吃”,其实他写“衣”也有许多精彩之笔。
汪曾祺小说多取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故乡高邮,那里面的服装当然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的烙印。上文提到汪曾祺1996年短篇小说《小孃孃》,写“来蜨园”的谢普天与谢淑媛“姑侄乱伦”,其中就有张爱玲《金锁记》里出现过的当时流行的面料“摹本缎”。汪曾祺不太谈张爱玲,不知道他写《小孃孃》这一节,是否想到过《金锁记》。
张爱玲倒是知道汪曾祺。1990年2月,隐居美国洛杉矶的张爱玲看到汪曾祺小说《八千岁》,专门写过一篇散文《草炉饼》。《八千岁》写“衣取蔽体、食止果腹”的米店老板“八千岁”专门吃一种极便宜的“草炉饼”,这勾起了张爱玲对于往昔的无限眷恋,她在上海也听到过“草炉饼”的叫卖声,却一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这回算是解开了将近五十年的一个谜。
张爱玲应该也注意到汪曾祺对“八千岁”父子特殊衣着的描写,虽然她那篇不点名地回应汪曾祺的散文,并未提到汪曾祺笔下“八千岁”的特殊服装。

汪曾祺
汪曾祺写“八千岁”节俭,表现在食物上是专门吃极其廉价而粗糙的“草炉饼”,表现在衣服上,则是一年四季雷打不动,只穿一种老蓝布做的长过膝盖但距离脚面尚有一尺的款式奇怪的“二马裾”。这“二马裾”和“草炉饼”是“八千岁”的“标配”。
可悲的是,省吃俭用的“八千岁”突然被小军阀“八舅太爷”以“资敌”(暗通日本人)的罪名绑架,硬是勒索去九百块大洋,才肯放人。“八舅太爷”用一百块办了一桌满汉全席,让“八千岁”看得心痛。但小说没写“八千岁”是否知道,那出手豪阔的“八舅太爷”竟然还用另外八百块,给妓女虞小兰买了件“西狐肷的斗篷,好让她冬天穿了在宜园梅岭赏雪”!
分析“八千岁”这个人物,不仅要注意作者对他的吃物“草炉饼”的描写,还须懂得何为“二马裾”,以及“八舅太爷”用“八千岁”的八百块钱给那位风尘女子购置的“西狐肷的斗篷”。
两种方式,各有千秋
古人谈论文学描写人物的方法,经常借用绘画理论的术语,比如说作家既可以“遗形写神”,就是不关心人物外貌而直指本心,但也鼓励“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这个“形”,自然也包括穿着。
上述几个现当代文学中与服装有关的例子,对这两种传统都有所继承。优秀作家既可以不写或少写人物的衣着,也可以大写特写。两种方式各有千秋,都可以见出作家们的苦心孤诣与匠心独运。
作者:郜元宝
编辑:傅小平
责任编辑:陆梅
*文学报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