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热衷于将自己隐在文字之中,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就曾指出:“库切小说中一个基本的主题就是根源于南非种族隔离体制的价值观,在他的小说中,其个人的情绪到处可见。”他自己也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坦陈:“所有的自传都在讲故事,而所有创作都是一种自传。”
由此,想要真正了解库切,最好的,似乎也是唯一的途径便是阅读他的作品。也正因为此,前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J.M.库切传》的作者、南非传记作家J.C.坎尼米耶在该书前言中不由感慨道,对于像库切这样的作家,研究他生平是否有意义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事实的情况是,库切的生平确乎很值得研究。这不仅在于如该书中文译者,库切研究专家王敬慧所透露,库切是一个特别注重自己私人空间的作家,他生活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喜欢谈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也很少接受采访,有记者开玩笑说,大概只有动物保护机构才能得到采访这位素食主义者的机会。据说库切刚得诺奖的那几天,南非媒体都苦恼于如何想方设法采访库切而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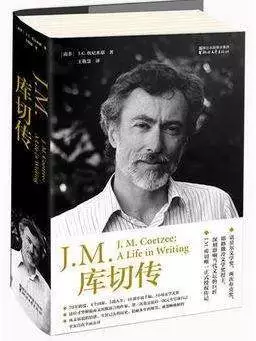
有据可查的是,有导演曾想把他的《内陆深处》改编成电影,并于十几年前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与他一起写剧本,但其间他说过的话还不到一牛车。导演说,你若问他一个问题,回答往往要等半个小时后。如果你问,你觉得这样写好不好?库切总是不语,但千万不要以为无声就是默许,因为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后,他会回头来说:“不,这样不好。”另据开普敦社交界的女主人们说:若是请库切出席晚宴,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
实际上,对库切的此等怪癖,实在不用惊诧。对于多少作家趋之若鹜的布克奖,他都不愿意出席颁奖典礼,他两次获该奖,却未亲赴伦敦领奖。人们曾一度猜测他可能也会拒绝出席当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很多年来,中国的出版社多次邀请库切来华未果,直到他终于答应参加2013年4月于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有人预测他发言不会超过五句话,没想到他竟做了将近15分钟的演讲,这诚然可以视为他对中国读者的礼遇,让人不禁联想到年轻时,他曾怀有一个中国情结:上世纪80年代时,他从IBM离职,确曾给中国大使馆写信说想到中国教英语,只是被阴差阳错地拒绝了。

库切获颁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无怪乎王敬慧感慨,这一次,库切坦然地把他的人生交给了他所信任的传记作家坎尼米耶,我们面对的将不仅是一部传记,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少见的出版事件。而以库切多部作品的中文译者文敏看,真正的库切和表达出来的库切、叙述出来的库切,究竟有着怎样的真实关系是一个哲学问题。她认为从《J.M.库切传》的出版来看,库切是希望将自己的作品和真实的自我做一个切割。当然,从了解库切生平的角度,要说该书还有什么意义,或许不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而在于如王敬慧所说,我们终于明白库切为什么不愿谈论自己。
“耶稣三部曲”里的大卫可以说是库切创造的一个充满寓言色彩的自我。第一部《耶稣的童年》故事始于一场神秘而模糊的移民。大卫和老西蒙在通往新世界的船上偶遇,他们都被抹去了从前的记忆和身份,要在诺维拉开始新生活。西蒙靠直觉认定了大卫的母亲伊内斯,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偶合家庭”。男孩不肯上学,声称早已懂得了真实的语言和数字,他最愿意阅读的,是一本儿童版《堂吉诃德》。上了年纪的西蒙所知道的一切,不停经受着男孩刁钻的提问和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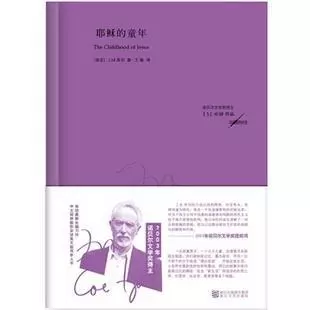
《耶稣的童年》封面书影,浙江文艺出版社
让人心生疑惑的是,书名虽为《耶稣的童年》,其中的叙事却与耶稣无关。我们唯一可以猜想的是,库切笔下的大卫是否代表了耶稣?虽然大卫的很多特质,确乎与耶稣很像。大卫和耶稣一样,对周围每一个人都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如此看来,把他当成尚且懵懂,没有“神化”的耶稣,也未尝不可。但很显然大卫并不能代表耶稣,库切在书名里写到“耶稣”,与其说他指向这个宗教人物,倒不如说指向《圣经》。他希望三部曲在叙述上能达到《圣经》式的简单,如有评论所说,《圣经》式思维没有理论推导过程,省却了各种逻辑关联,库切想要获得类似的叙述效果。《圣经》使用的是最基本的语言和句式,库切同样热衷于此。与此同时,唯简单方可多义,唯基本方可接近本质,库切也显然希望三部曲达到《圣经》式的复杂多义。《耶稣的童年》开篇就抽去了完整的时间链条。大卫和他的“父亲”西蒙只是在一个偶然的空间里相遇。库切实际上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深邃的哲学命题:我们的记忆,究竟可靠不可靠?
作为《耶稣的童年》的续篇,《耶稣的学生时代》更是像《圣经》一般包揽了诸多思考,涉及宗教、道德、社会、哲学、艺术等多个方面。男孩大卫和西蒙、伊内斯为逃离诺维拉的教育制度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作为“逃犯”的他们在这里必须隐姓埋名。大卫需要上一所新学校,于是进入了埃斯特雷拉的舞蹈专校,这里的教学方法颇为匪夷所思——校长夫人,也就是舞蹈老师,指导学生们通过跳舞把数字从星星上召唤下来。毫无预兆地,一桩谋杀事件降临在校长夫人身上,而谋杀背后的故事比学校的教学方式更为耐人寻味……
如此,一个虚构的移民国度、一个神秘的天才儿童、一所匪夷所思的学校、一桩离奇的杀人案件,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以该书译者杨向荣的说法,库切似乎只是写了一个简单的事件,但我们却能从中探寻到孩子蒙昧心灵中对死亡、杀人、善良这些概念界限的模糊认识和可以自由穿越的幽暗真实。小说里,看门人杀死了自己最喜欢的女老师,男孩没有建立起对杀人者的厌恶、憎恨和害怕,居然还继续与之偷偷往来甚至搭救他走出监禁的医院。而这也恰恰体现了库切的无情可怖之处。相比而言,西蒙却在道德判断和道德勇气上表现得斩钉截铁。他是激情、怜悯与理性、克制兼具的道德家。他的道德意识清晰,绝无模糊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道德感淡漠,甚至道德体系有被侵蚀和出现分崩离析趋势的当代社会,西蒙具有定海神针的象征意义。
倘使把“耶稣三部曲”的这两部小说和“自传三部曲”里的《青春》和《男孩》做一对比,我们会发现,如作家李洱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耶稣的学生时代》分享会”上所说,这两个系列之间有同构性、互文性。李洱表示,两相对比,库切小说基本的叙事元素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库切写南非风云复杂巨变的现实,线索看上去是简单的,但他的思考如此深入,他的文本后面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如此的辽阔,而他所处理的主题看似集中,却相当深入地击中我们目前的文化现实。可以说是我们所有人都被卷进去,这是库切作为知性作家,他的手术刀般的、庖丁解牛般的能力,确实让人非常惊叹。”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库切擅长处理宏大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自身特殊的经验。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库切在小说里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却也不能因此认为他写的就是他自己。相反,他和他塑造的人物之间,总有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以科斯特洛为例,别说她和库切年龄性别不同,按文敏的看法,库切具有巴赫金所说的“外在立场”,对世界的观察也远比她透彻。“库切的策略是让科斯特洛去替他嚷嚷,让她去面对驳诘、冷落和各种尴尬场面,借着女作家那份偏执劲儿,库切毫无忌顾地将自己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引向较为极端的方向。”
或因如此,无论在自传体小说,还是别的小说里,库切惯于选择第三人称叙述。他之所以这样做,以这本传记所示,是因为他需要距离,距离带来安全和放松的感觉,以及审视自我的可能。诚如云也退所言,库切那个被始终压抑的“我”,也只能藉由另一个人之笔以“他”来表达,而且这个人必须跟他一样,有着“书写一个人物来让他不朽”的热切需要。比库切大一岁的坎尼米耶,恰好契合了他的这一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在结束全书时,坎尼米耶不由感慨“理解库切就是理解自己”,而坎尼米耶还没看到书的英文版出版便于2011年底去世了。
可以想见,库切或许如云也退所说,在坎尼米耶身上看到了一些令自己戚戚然的地方:他们各有各的写作人生,而这段人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也同时遇到了老龄和疾病的终极考验。库切回望自己的前尘岁月,也必然会感受到时间带来的复杂况味,他先后经历了多次沉重打击。第一任妻子菲丽帕·朱贝死于癌症,儿子尼古拉斯意外坠楼身亡,爱女吉塞拉在1989年罹患癫痫。种种不幸的遭遇,都让他苦行僧似的写作,带上了类似自我救赎,乃至自我疗伤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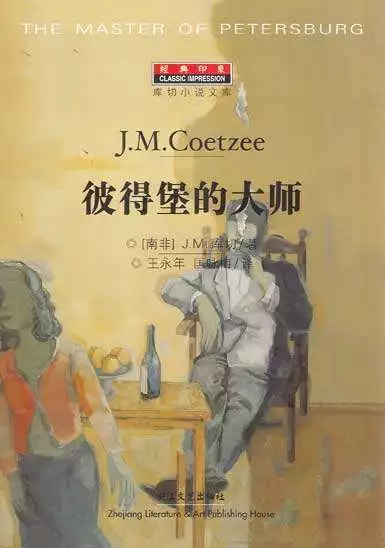
《彼得堡的大师》,浙江文艺出版社
这般自我救赎的意味,体现在《彼得堡的大师》里,库切将尼古拉斯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夭的孩子巴维尔,他想象这位文学大师如何搜寻巴维尔生命最后几个小时里的行踪,以克服自己的悲伤。也因有评论说,这部小说是澄澈的,这种澄澈或许来自库切对文字有力的节制和叙述上的冷静,但它也是动情的。也许这种动情来自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深深的敬意。库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父子关系的书写,寄寓了他内心的情感。“这种父与子的二元对话关系不仅是血缘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充满现实和隐喻的色彩。”
库切风格各异的作品,富有现实针对性的同时,都有着很强的隐喻性。就像他最具代表性的小说《耻》,藉由南非白人教授戴维·卢里因的遭遇,库切意欲探讨越界是否可能。无可疑义,任何事物之间都各有其界限,强行越界,必然会付出一些代价,但交流和沟通本身就预示着越界的可能,问题只在于我们得怎样遵守界限,又该怎样逾越界限?库切对此并没有给出解答。而他那些更具寓言性的小说,无论是《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还是近年的《耶稣的童年》《耶稣的学生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他多元思想的呈现。
要阐明库切的思想无疑是困难的,相对可行的方法无过于把他从思想的云端拉回到地面,从而引发公众对库切的兴趣。前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围绕《J.M.库切传》一书在上海和杭州两地的宣传,分别以《J.M.库切:当然,我不吃肉》和《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自我修养与成长》为题,未尝不是包含了这样的用意。评论家李庆西说,读《J.M.库切传》最深刻的感受,在于能读到库切无论从自身人格,到哲学认识等方面都有着极高的修养。“从这部传记,还有库切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非常聪明,不仅聪明,还特别刻苦,有了这两项,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库切。”他所说的这个库切,当然不只是作家库切,还有作为思想者的库切。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一章里,科斯特洛参加颁奖活动时,有记者请她谈谈自己“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她上来就跟记者兜圈子,“我的思想?我有义务带来思想吗?”在文敏看来,这也许正是库切的自我警示。“库切给读者带来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存在方式。”
译作选读

他一直以为埃斯特雷拉要更大些。在地图上,它跟诺维拉显示为同样大小的圆点。但诺维拉是座城市,埃斯特雷拉却顶多算个位于某个充满山丘、田野、果园的乡下的外省小镇,它杂乱无章地朝四面八方延伸,一条无精打采的河从镇子中间蜿蜒穿过。
在埃斯特雷拉开始新生活可能吗?在诺维拉,他还能依靠重新安置办公室安置住所。他和伊内斯还有这个男孩在这里能找到家吗?重新安置办公室是慈善性质的,是没有个人感情色彩之别的慈善的具体化身,可它的仁慈会延及一个逍遥法外的逃亡者吗?
搭便车的胡安在去埃斯特雷拉的路上跟他们走到一起,他建议大家可以在某个农场找份工作。农场主总是需要帮手,他说。更大的农场甚至还有给工人住的季节性宿舍。不是橘子季就是苹果季,不是苹果季就是葡萄季。埃斯特雷拉以及周边地区是个名副其实的丰饶角。如果他们愿意,胡安说他可以带大家去自己的朋友们曾经打过工的一家农场。
他和伊内斯交换了下眼神。他们该听胡安的劝告吗?钱不用考虑,他兜里有的是钱,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待在一家旅馆里。可是,如果诺维拉的当局真的在追寻他们,那么或许隐藏在无名无姓的临时过客中可能会更安全些。
“好吧,”伊内斯说,“我们就去这家农场。我们圈在车里也太长了。玻利瓦尔需要跑一跑。”
“我也是这么想,”他,西蒙说,“不过,农场可不是度假村。伊内斯,你准备好了整天在烈日下摘水果吗?”
“我会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伊内斯说,“既不多也不少。”
“我也可以摘水果吗?”男孩问。
“很遗憾,不行,你不能摘,”胡安说,“那会犯法。那就是当童工了。”
“我不介意当童工。”男孩说。
“我敢肯定农场主会让你摘水果,”他,西蒙说,“但不会太多。不会多到让摘水果变成劳动。”
他们顺着主大街开车穿过埃斯特雷拉。胡安给大家指了市场、行政大楼、朴素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他们穿过一座桥,把小镇抛在了身后,沿着那条河道方向行驶,最后来到半山腰上,看见了一幢宏伟气派的房屋。“这就是我说的那家农场,”胡安说,“我的朋友们找过工作的地方就在后面。它看上去挺沉闷,其实非常舒服。”
这个避难所是由两个长长的镀锌的铁皮棚屋构成,用一条带篷顶的走廊连接,一边是个洗浴房。他把车停住。除了一条双腿站立的灰狗在锁链限制的范围里朝他们露出黄黄的长牙嚎叫外,没有一个人出来招呼他们。
玻利瓦尔舒展开身子,从小车里溜出来。他在一定距离之外审视了一番这条异乡的狗,决定不理它。
男孩冲进棚屋,然后又跑出来。“都是上下铺床!”他大声喊叫道,“我能睡上铺吗?求你们了!”
这时一个在一件宽松的连衣裙外系了条红色围裙的胖女人从农场住宅的后面走出来,一摇一摆地沿小路朝他们走来。“你们好啊,你们好!”她大声说。她仔细看了看装得满满当当的小车。“你们是走远路过来的吧?”
“是啊,很远的路。我们想你们这里是不是需要额外的帮手。”
“帮手多了我们事儿就好办多了。人手越多干活儿越轻松。——书上不是这么说吗?”
“可能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妻子和我。我们的朋友在这儿有自己要办的事。这是我们的男孩,他叫大卫。这位是玻利瓦尔。可以给玻利瓦尔安排个地方吗?他也算这个家的成员。我们去哪儿都带着它。”
“玻利瓦尔是它的真名,”男孩说,“它是条阿尔萨斯狗。”
“玻利瓦尔。这个名字不错,”这女人说,“很特别,我相信会有它待的地方,只要它自己举止规规矩矩,能心满意足地吃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不要打架斗殴或者追赶鸡就行。这会儿工人们都出去上果园了,不过我来带你们去看看睡觉的地方吧。男士在左侧,女士在右侧。我想,恐怕没有家庭房。”
“我要去男士那边,”男孩说,“西蒙说我可以睡个上铺。西蒙不是我爸爸。”
(《耶稣的学生时代》[南非]J.M.库切/著,杨向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
作者:傅小平
编辑:李凌俊
责任编辑:陆梅
*文学报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