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局部》中,陈丹青曾不无遗憾地谈到印象派画家巴齐耶之死,“这么好的一个青年,倒在战场的泥浆里。”这位天才画家死于1870年普法战争,年仅29岁。
今天要介绍的法国作家阿兰-傅赫涅和巴齐耶有着几乎相同的命运。他1886年出生于法国,1913年完成了《大茂那》的写作,这也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大茂那》先在安德烈·纪德主编的知名杂志《新法兰西》上连载,几周后由埃米尔·保罗出版社出版。当年,这部小说参与角逐龚古尔奖,虽然惜败,但历经两次大战和一百多年岁月的淘洗,最终成为经典。
小说出版后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阿兰-傅赫涅参军走上前线,但仅隔一个月就在圣-雷米遭遇德军伏击阵亡,年仅28岁。他与另外二十几位战殁者的墓地,直到1991年才在马恩省被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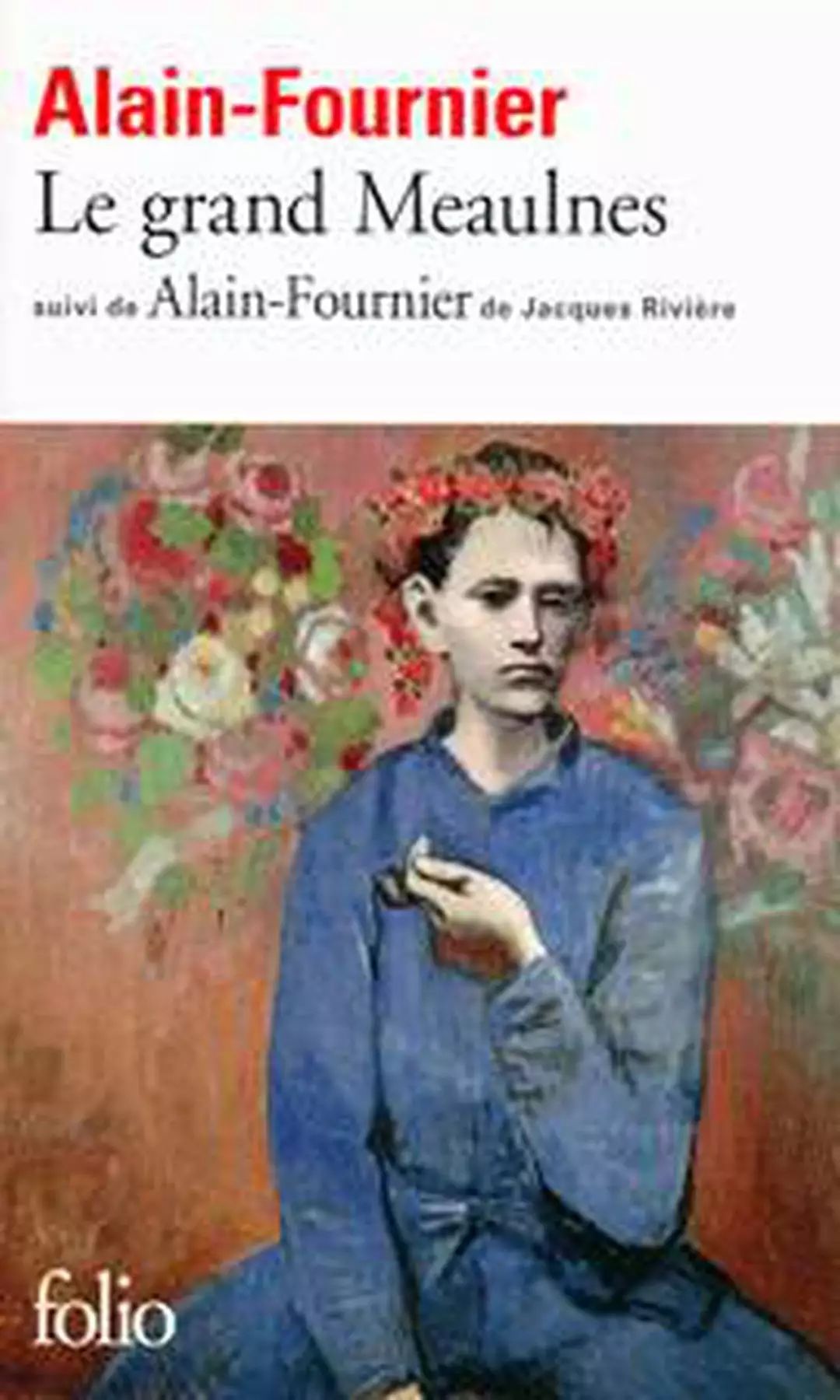
Folio Society出版的《大茂那》用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做封面
《大茂那》的叙事有狄更斯成长小说和史蒂文森历险小说的缘起,但阿兰-傅赫涅并不严格遵循时空顺序,人物、场景和故事像色彩缤纷的花雨,有着亦真亦幻的神秘色彩,这使它成为20世纪初法国文学传承和转向的标志。《大茂那》的故事并不复杂:奥古斯丹·茂那是个特立独行的男孩,他比一般同学来得高大,天生有领袖气质,常有出其不意的想法并热爱冒险。某一天,他驾着马车想到车站接客人,却因迷路而误入一座庄园,受邀参加了一场狂欢婚礼,邂逅他梦寐以求的恋人,两人有了约定。待他回到学校后,却如何也找不到回庄园的路。茂那难以忘怀这趟奇幻之旅,遇到有关失落庄园及恋人的消息绝不放弃,甚至离开学校追踪至巴黎。执着的追逐换来情感和意志的考验,不晓得何时幸福才会到来……
据考证,《大茂那》取材自阿兰-傅赫涅真实的情感经历——18岁那年,他在一次画展上偶遇伊冯娜·德·盖芙库尔,一见钟情。无奈她已订婚,并于第二年完婚。她就是小说女主人公伊冯娜·德·卡莱的原型。从索洛涅乡村到大都市巴黎,阿兰-傅赫涅把童年感受和青春恋情都写进了这部小说,他短暂的一生可以说是为这本书而经历的。

阿兰-傅赫涅故居已经成为读者探险寻幽的圣地
跨越一个世纪,《大茂那》在法国多次再版,在欧美地区家喻户晓,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有评论家把它和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相提并论,称其为“经典成长小说”。音乐家拉威尔从中找到写作芭蕾舞短剧的灵感。《大茂那》影响了于连·格拉克、西蒙娜·德·波伏瓦、罗贝尔·弗朗西斯等法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约翰·福尔斯等英美作家。有人认为,这部作品对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有着显著影响。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不受罪的文学课》一文中谈到,有三部作品“二十多年来一直位居前列:托马斯·曼的《魔山》、阿克塞尔·芒思的《圣米歇尔的历史》和阿兰-傅赫涅的《大茂那》”,他希望“这些作品能在年轻人中再度流行起来”。·凯鲁亚克说:“对阿兰-傅赫涅的《大茂那》,我有一种奇怪的投契之感。”莫迪亚诺表示:“我想写一本综合了《大茂那》的东西。”朱利安·巴恩斯说:“我以为我读它的时候已经太老了,但更可能的是,我读它的时候还是太年轻了。”

《大茂那》多次被改编成戏剧和影视剧,图为2006年电影版,让-丹尼尔·维哈吉导演
翻译家许志强曾在评论中写道:“其融合悲喜剧的魔幻叙述的原创性则是无可比拟的,是这个魔幻家族无可置疑的先驱。它是让人眷恋的青春叙事诗,也是具有魔术吸引力的作品。它在我们这个寻常世界里悄悄投下一束光,照见跳舞的年轻人,他们正迈入神秘而喜庆的晚宴……或者说,它从一个好奇而依恋的视角,从戏剧帷幕的缝隙,从非现实的平面,——自忘川之河的黑暗波涛升起的神秘的立足点,朝画面反复聚拢光束,向人呈现乡村婚礼的年轻人聚会。”
作品节选
1
我一直把那里叫“我们家”,即使那处房子不再属于我们了。差不多十五年前我们离开了那个村子,我们也肯定不会回去了。
我们住在圣阿加特公学的房子里。我父亲——像别的学生一样,我叫他索海尔先生。他在这里教中级班和高级班,高级班的课是为获得小学初级班教师资格证书做准备的。我母亲教初级班的课程。
一幢长长的有五扇门窗的红房子坐落在镇子边,外墙布满了爬山虎;一个带洗衣房和有屋顶长廊的大操场朝村子敞开大门;房子的北面,穿过操场上的一扇小栅栏门,一条大路通向三公里外的火车站。房子的正面朝北。后面,有庄稼、花园,还有镇边的牧场……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的简要地图。在那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珍贵也最纠结的日子。在那些年里,这个地方是我们少年历险旅程的起点,也是旅程每每中断时的归宿。
我们的历险像汹涌的波涛拍击着海岬。
那是好久以前一个偶然的变迁。督学还是省长的一个决定,让一辆乡下马车,在假期末尾时,把我和我母亲带到了那扇生锈的小栅栏门前(我们的居家用具要在这辆马车后运到)。那些正在花园里偷桃子的男孩子们,悄悄地从篱笆的缝隙里溜走了。

巴齐耶《粉色连衣裙》1864年
我母亲——我们都叫她米莉。她是我见过的最有条理的家庭主妇。
当她一走进那些尘土飞扬、被稻草填满的房间,马上失望地觉察到:就像我们一次一次搬家时遇到的那样,这些布局别扭的房间放不下我们的家具。她一边讲话,一边用手绢擦着我在旅行中抹黑了的孩子的脸,诉说她的忧虑。然后,她回到房子里,数清了墙上所有窟窿,为的是把它们堵上,让这里变成能住的地方……而我,戴着一顶系着丝带的大草帽,一直被留在一片陌生操场的沙地上。我等待着,在水井和棚子周围东张西望。
至少我能想起的刚到这里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一旦重拾那些遥远的记忆,想起第一天傍晚我们在圣阿加特院子里的等待,另一个等待的记忆也会浮现……
我好像看到我双手把着栅栏门,正翘首等待的那个人沿着大路走来。如果我尝试着回忆到圣阿加特院子的第一个夜晚,我不得不爬到二层阁楼进入我的房间的情形,那么另一些夜晚的情形也会联想忆起:我不再是一个人在房间里,一个不安的、似曾相识的大影子漂移在墙壁上。所有那些宁静的风景……学校,老马赫丹有三棵核桃树的庄稼地,每天一到下午四点就会挤满女客人的花园……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中,它们被那位朋友的出现惊扰,永远地改变着。他的出现让我们整个青春躁动不安,他的消失也没能让我们得到安宁。
2
不过,当茂那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已经住了十年了。
我那时15岁。这是11月里一个寒冷的星期日——晚秋让我们感到了冬天迹象的第一天。整整一天,米莉都在等一辆从火车站过来的马车,它会给她捎来一顶为这个坏季节准备的帽子。早上,她错过了弥撒。而直到布道,和唱诗班的孩子们坐在一起的我一直焦虑地看着一侧墙上的挂钟,希望看到她戴着新帽子走进来。
中午过后,我只好独自去作晚祷。
“另外,”为了安慰我,她抚摸了我一下,对我说:“即便它到了——我是说那顶帽子,我也肯定不得不花上一整个礼拜天把它改造一遍。”
冬季的星期日我们经常就是这样度过的:我父亲一大早就会出远门,在覆盖着一层薄雾的某个池塘边的一条小船上吊狗鱼。我母亲则躲在她幽暗的房间里直到夜晚,简简单单地缝补那些日常穿的衣物。她如此闭门不出,是怕会无意中碰见她的女伴中的一位女士——和她一样没有钱但同样很自尊。而我总是在晚祷结束后一边在那间有些冷的饭厅里读书,一边等着母亲打开房门进来,向我展示她的缝补成果。

巴齐耶《乡村街道》1865年
这个星期日,晚祷之后,喧闹声把我拉了出来。教堂前,门廊下举行的一个洗礼仪式把男孩子们聚集在了一起。广场上,镇上的一群男人穿着消防员制服,三枝枪一架,站在那里跺着脚,冻得直发抖。他们听着队长布佳东的口令,执行得一团糟……
响亮悦耳的礼拜钟声突然停了下来,像是一个要传出节日喜庆声音的人意识到搞错了日子和地点。布佳东和那群男人们,斜挎着抢,带着水泵快步小跑起来。我看着他们消失在第一个转弯处,四个男孩悄悄地跟随着他们。他们的厚底鞋碾着冰冻路面上的小树枝咯吱咯吱作响——跑在这样的路面上?我没敢跟着他们。
3
这时镇里最活跃的地方就只有达尼埃尔咖啡馆了。我能听到喝咖啡的人在热烈地交谈着。吵嚷声闷闷地升起而后又恢复平静。大操场的矮墙把我们的家和镇子隔开了。紧贴着矮墙,我来到小栅栏门处,由于我的晚归,我有一点不安。
栅栏门半掩着。我马上看到了某些异常。
实际上,在饭厅门外——面向操场的五个门窗中最靠近栅栏门的那扇——一位灰头发女士歪着头透过窗帘向里张望着。她个子不高,戴了一顶有系带的老式黑天鹅绒女帽。她有一张消瘦的显得精明的脸,但被焦急搞得有些憔悴。不知道她为什么而焦虑,看到她这个样子,在栅栏门前第一层台阶上,我止了步。
“他跑到哪儿去了?我的上帝!”她小声地说着。
“他刚才还和我在一起。他已经绕着房子转了一圈。他可能逃跑了……”
在每句话之间,她都轻敲三下窗玻璃,很难让人觉察。

巴齐耶《靠近海滨的风景》1870年
没有人出来为这位陌生的来访者开门。米莉可能收到了火车站送来的帽子。她正在床前忙着拆拆缝缝,改制她那顶普普通通的帽子。床上撒满了老丝带和被弄直的羽毛。在红房子的紧里头她什么也听不到。
果然,当我进入饭厅的时候,那位来访者马上跟在我后面。我母亲两手扶着头上的帽子出现了。铜丝线、丝带和羽毛乱糟糟地盘在她头上……她朝我微笑着,蓝眼睛里充满了在日落时做针线活的疲惫神情。她嚷道:“看哪!我正等着给你展示呢!”
可是,当米莉瞥见坐在饭厅深处大扶手椅上的那位灰发女士时,她尴尬地停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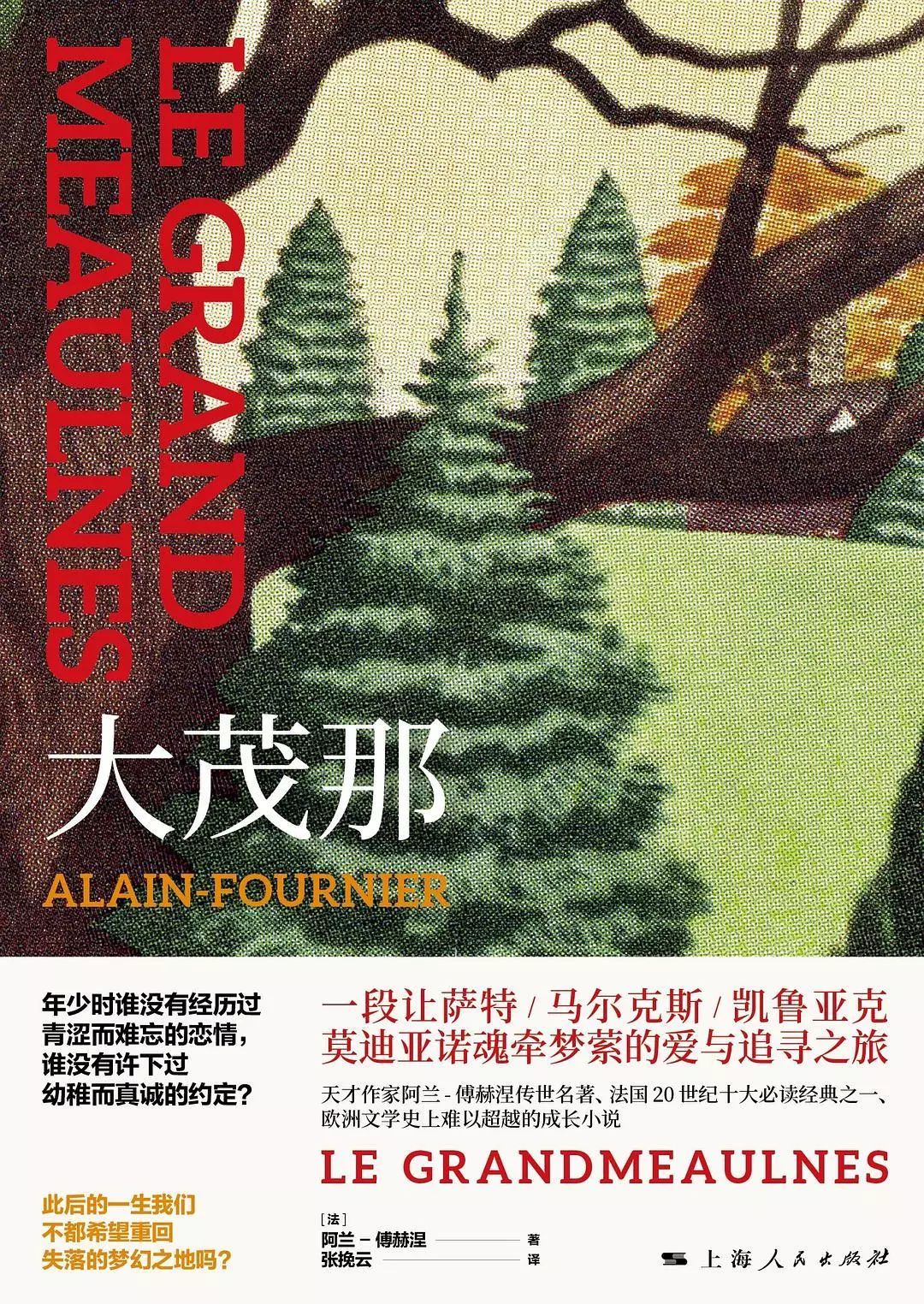
《大茂那》[法]阿兰-傅赫涅/著,张挽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版
编辑:李凌俊
责任编辑:陆梅
*文学报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