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理科生打量世界的方式”,这是作家马小淘为青年作家谈衍良所写的书评中的一句话,被印在谈衍良首本短篇小说集《乌鸦妖怪与随机数侦探》的封底,同样印在封底的推介语还有作家小白写的“试图用少量生活推导出一整个观念大厦”以及评论家黄德海所说的“一个满怀好奇的家伙,用望远镜和显微镜交替观察着人心的某些奇特角落”。
这些评语无一不指向谈衍良作为一个理科生写小说时体现的个性与特点,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充满理科思维的。此前在一篇创作谈的末尾,谈衍良说自己开始像个科学家了,但现在他认为“实验员”的说法其实更适合他,用精密的仪器来观察生活这个复杂的样本,然后做很多实验,收集足够多的数据,挑出有代表性的,但数据背后的科学道理,他不妄图去解读。在他看来,像托尔斯泰般伟大的作家,同时扮演了实验员和科学家的角色,但对他来说,只是把故事讲好、把实验做好,就已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数学方程式、液态氮、北回归线、飞行原理、随机数等理科用词在谈衍良的小说中如一个个材料,结合衍生出其他意义,进而成为生成故事的重要元素。他把数学小说化,这也是阅读他的小说会形生陌生感的来源。作为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硕士,谈衍良平时做的最多的事是研究金属腐蚀,在等待反应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去写小说。他写作时会将理科生的经验放进去,以致于“理科思维”似乎成为读者们的某种辨识符号。
对此,谈衍良表示不会为了维护“理科生”的符号而去在每篇文章里加很多数字或题目,同样地,如果在写的文章和这本书的风格不一样,这也不是为了褪去身上的符号。比如《疼痛课》的主角是一个整天坐在烧结车间电熔炉旁的控温员,但他也可以是其他身份的人,也许是一个公交司机。“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去想‘这个角色应该是什么类型的’,或者说‘这个角色太单一了,我要让他复杂一点儿’。”“我自己也是我的角色之一。如果我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符号化的人,那说明我就是只展现出了我单一的一面,这当然也没有错。”

在他眼中,“被阅读”是一件浪漫的事,被读出复杂性也是一种荣耀,但毕竟任何人的存在都不是专门用来“被阅读”的。评论家张定浩在某场对谈中提及的话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他会慢慢变成那种可以欢快地说出不愉快真理的小说家,“理科生是他的一个符号,每个写作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一个符号,别人愿意通过一个符号去辨识。如果写的越来越丰富,这个符号就会褪去,通过去掉符号的方式,作者的符号才会变得很多样。”
在《乌鸦妖怪与随机数侦探》中,有两篇在作者本人眼中都很不“理科”:《爱猫者》和《库生》。《库生》是他第一次尝试书写生活着的这座城市——上海,更贴地,他以后想要更多地关注生活在社区里的人群。而《爱猫者》是谈衍良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围绕两个虐猫角色展开,启发他写这篇小说的是王安忆的《众声喧哗》,“一个市井故事,你很难去概括每一个角色分别展现了人性的哪方面,但你读完之后就会觉得‘人就是这样的呀’。”他觉得这就是小说展现人性的方式,在经验的层面,而不是理论层面。他认为人性是贯彻在一切有人存在的地方的,所以他要的是既有真实感也有陌生感。陌生感负责挖掘那些人性还没有被完全了解的角落,真实感负责让人觉得这的确是人性,而不是空想。
“我本身是一个生活经验非常淡薄的人,所以很少会去试图区分‘正常’和‘异常’。这在写小说的层面上可能不是一件坏事,在我写那些奇怪的人的时候,我打心眼儿里觉得他们是很正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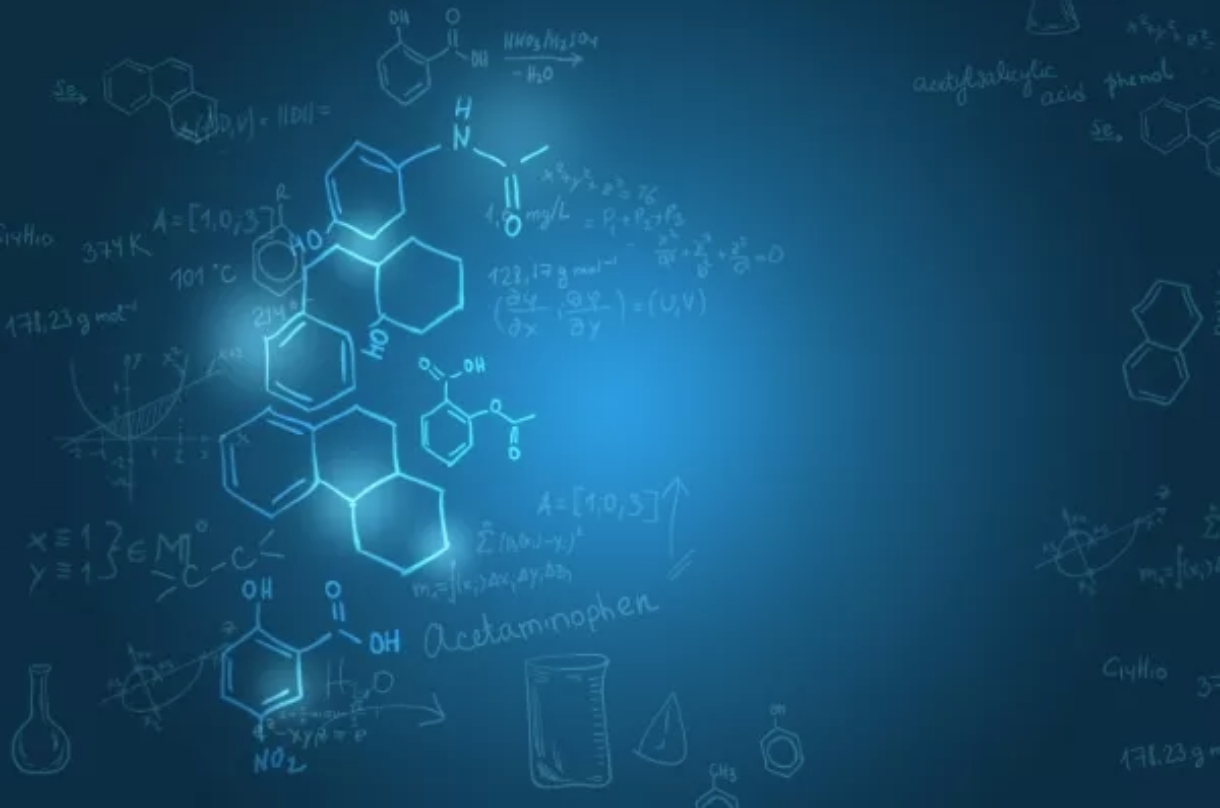
谈衍良谈及自己小说中那些奇怪又有点执拗的主人公时,如此说道。《疼痛课》里的肖伟峰特别关心“疼痛”这件事,他怕痛,所以整天就想着怎么让自己的儿子不再怕痛,甚至要故意用小针去扎他儿子一下。《百分之七十八的纯净空气》的主角林清晖,他特别关心的是空气,他觉得他所在的化工厂空气污染很严重,所以从头到尾就是想闻一下百分百的纯净空气。接着,谈衍良又举了《出题人》里的主角衍正为例,整个故事里就一直在想怎么出数学题目。但这也仅限于故事内的几个小时,他可能在故事结束之后就发现了出数学题原来不过如此,于是再次成为一个毫无特点的人。谈衍良想要极力说明的是就像他看很多社会热点新闻时不会觉得惊讶,这些主角在他眼中都很平凡。他觉得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如果默认它是一桩“奇闻异事”,就很难从中找到人性,找到真实感。“我一直相信‘一切异常都是你不熟悉的日常’,所以,把这些异常用日常的方式写下来也可以算是我写作的一种本质。”
谈衍良以一种老练的方式书写着与自己相关的经验世界,但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自娱自乐的写作者,他的写作姿态更像是一个冲动的、好奇的、具有张力的年轻人极力想要去描摹日常,却又保持了自己的思辨。他比喻自己是个丢骰子的人,扔出去一个3D20(三个二十面骰),出现的结果将替他决定好将要选择的说辞。至于为什么写小说?谈衍良用随机数回答了这个提问:一篇小说不是一个传奇的故事,而是一个平凡的故事,它只是描写了一种可能性,或者说这种可能性也是一种偶然性。“这些偶然性可能是由我的想法和经验拼凑而成的,但是由于它的排列组合是我自己没有预料到的随机的过程,那么它就可能超出了我的预期,这也就是我所认为写小说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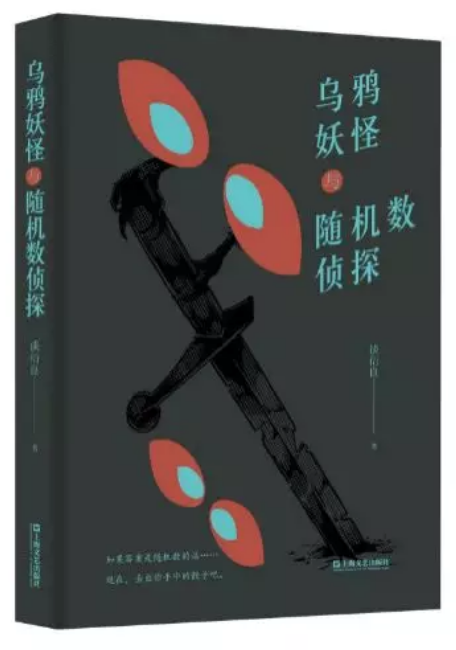
《乌鸦妖怪与随机数侦探》
谈衍良/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版
丢骰子的人(后记节选)
谈衍良 | 文
当我写完《乌鸦妖怪与随机数侦探》的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想起一句人尽皆知的名言,它叫做“上帝不掷骰子”。
……
如果要问小说在通往绝对真理的道路上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我预备了很多个不完备的答案。我也因此丢了一个3D20(三个二十面骰),它会替我决定我将要选择的说辞。
答案是二十七: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告诉我:“人性是复杂的。”
那时候我正在网上玩三国杀,并且因为队友的攻击而阵亡。我没有领会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每一个活在人类社会中的人都应当知道“人性是复杂的”,它是一个基本而普遍的现象,就像万物终将从天空坠向地面,绿豆和黄豆不会自动分成两堆。它的背后也许蕴藏着一个像是万有引力或是熵增定律一样绝对的规则,当然,没有人发现了这个规则。
那之后,我的爷爷说,他这一生遇到了许多不讲道理的人,他们大都不占着理却热衷于吵嘴,或者是以捉弄人为乐。他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他眼中人性最大的复杂之处:讲道理是正确的,与人为善是正确的,而某一些人类却亲手造就错误。为什么会有人追求错误?
对秩序的信仰与对自由的信仰,破戒的欲望与禁欲的欲望,为个体、为血脉而存在,为种族、为世界而存在,不可理解的善意、不可理喻的恶意,情感冲动、抗拒情感冲动。我们从进化论、从基因、从内分泌解释这些错误或者正确,又或者是归纳为社会学、心理学规律。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人性是复杂的”。
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选择逃避问题。
方法很简单:“人性是复杂的”这个命题,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正常的”。而又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正常的”,任何现象与事件都不会超出我们的预期。没有人会觉得一件意料之内的事情复杂,它们发生过,发生过就够了。人性是简单的,人性就是万事皆可。
在我开始每一篇小说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这不是一个传奇,而是一个平凡的故事”,它们一点儿也不复杂,只是描绘了一种可能性,或者一种偶然性。通常来说,这些可能性是由我的经验拼凑而成的,但在排列组合的方式上则完全超越了我的经验。借由阅读过程中另一份个人经验的加入,故事就将化身成为一个新的独立个体。
一个关于人类的思想实验。它包含了一些差错、一些未知、一些平凡的意料外,它因此而重新变得复杂,变得重要,成为未知规律的一个拐点、一个论证。
现在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科学家了。我想起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的奶奶问我,我的文章写出来是做什么用的。那时候我正在吃一个鸡蛋布丁,并且吃到了焦糖味最浓郁的一口。
成为科学家是一个很棒的答案,但我当时只告诉她:小说是不需要有什么用的。
它只是存在着。就好像这世界上也许的确存在着一个数学舅公;存在着一个杀猫的保安;存在着一个仲凯一村,与现世隔绝的老人在那儿消亡,向日渐远去的年轻人们挥手告别。这是一种可能性。
作者:袁欢
编辑:李凌俊
责任编辑:陆梅
*文学报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