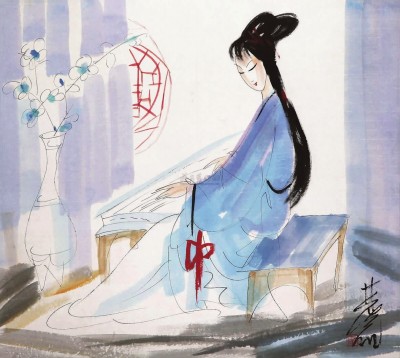
萧牧之
中国古代贵族社会中有教养的女子,所受的规训是内外有别。她们的活动空间,常常局限在“家”的范围。先秦到西汉,是高台建筑的流行期,宫殿与贵人居处,大多建立在高大的夯土台上,造型宏伟,一眼可知与庶人的区隔。在西汉的大赋里,常常可以见到对高台、宫殿的夸饰描写。居住在这些高建筑里的女子,毫无疑问,是有身份的女子。
汉乐府里的 《相逢行》,又叫 《长安有狭斜行》,常见两个传世版本。其中有一节用来描述某人家三个儿媳妇的表现,分别是:
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大妇织绮纻,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琴上高堂。
和参与劳作的妯娌不同,最小的这个儿媳妇,琴歌自娱,仿佛后世才女的雏形。她的举动,就是带着乐器“上高堂”。琴瑟都是有历史的、“雅”的乐器。当时的人甚至愿意相信,这两种乐器起源于上古神话中的伏羲、神农等帝王。演奏乐器愉悦他人,那是乐工的职业;演奏乐器愉悦自己,则是自古以来圣人君子乐此不疲的修养。身处比一般高处看起来敞亮些的“高堂”,独自弹奏着琴或瑟,人物藉由空间呈现出的,大抵是个有文化传承的、“幽娴贞正”的形象。她文化、才情方面优势特别突出,乃至不用参与劳作,就可获得家中地位。而勤劳灵巧的儿媳妇、有才情的儿媳妇,都是这个家庭可以对外夸耀的资本。
随着建筑形式逐步变化,高台也渐渐演变成了高楼。一些女子的才情更为突出,于是在高建筑下聆听她们的,便不仅仅是家里的人。譬如东汉时期,《汉书》 大部分内容刚定稿未久的时候,小部分内容还正由作者班固的妹妹班昭续写,很多人读不明白《汉书》,于是后来的经学大师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班昭负责完成的是《汉书》八表,通贯西汉基本文献,曲折反映重大史实,需要很好的学问。这样一个很可能底蕴不亚于其兄的女学者,授课的时候,需要男弟子“伏于阁下”,而不能对面讲授,或垂帘讲授。在那个年代的男性看来,这高高供奉起来,是对有文化、有才情的女子,对学问高过他们的女子,一种极致的礼重。高阁上从容落下的话音,毫无疑问,对他们是训导。这类心灵可能“高于男性”的女子,一定要在空间上也“高于男性”,才能够让当时的男学者们感到自在。班昭和马融无论在当时学者中,还是当时贵族中,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于是更强化了这一观念模式。
东汉后期五言诗兴起以后,带来中下层士人眼中另一位略显不同的高楼女子。
在《古诗十九首》 里,《西北有高楼》 是极具阐释空间的名作。起句“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看似不经意间,就为读者勾勒一幅高出寻常人间的场景:高楼之高昭显身份不凡,连所居方位 (西北为乾位) 都隐藏着尊贵。这样的氛围,是即将出场的抚琴女子“地位远高于”叙述者的暗示。“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她居处富丽,好似宫殿一般。这是人间,还是幻象? 叙述者的似梦非梦中,真正的主角登场,先声夺人。“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她的弦歌似乎不仅仅是自娱,而有了言志的意味。然而在叙述者听来,她的歌声并不快乐,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悲凉。在感叹身世,还是感叹君子道穷? 于是引发叙述者进一步的联想:“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的妻子,和她身份相当,教养相当,是阵亡将军的妻子。她冷静拒绝国君对丈夫失礼的吊唁,也留下哭倒齐长城的故事,成为孟姜女的原型。这一句是说这曲子大约是杞梁妻作的? 还是说能弹奏这样琴歌的,一定是杞梁妻那样的人? 两种理解似乎都可行。诗句所指模糊,便为后人带来多重解读的可能。她弹奏的是清商曲。“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被人认为容易“短歌微吟不能长”的曲子,因为“一弹再三叹”,反而具有了顿挫激扬的美感。于是叙述者又有了新的联想。“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是歌者不惜自己心中之苦,唱出来呼唤知音?还是听者顾不上怜惜安抚歌者心中之苦,却感于歌者若无知音,终究还是寂寞的? 他自信能知音,但不确定歌者还能不能得到其他知音,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反复冲撞内心堤防,最后喷涌而出的,竟然是“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你应该有更广阔的天地,应该有更多知音。你应该自由自在地飞翔,和我一样。我愿意帮助你……飞去哪里,对不起,暂时还没想好。
这位叙述者是个勇敢的侠客,有热血,有抱负,容易冲动。在他眼中,高楼上抚琴的女子是高高在上、令他情不自禁追随的形象,单单弦歌已足够引起无限联想。他情感喷薄,像是来不及细细分辨乐器。他的全部联想,又似乎将司马相如“琴挑”的故事,倒过来重新演绎了一番。然而,夜奔剧情真实上演之前,一切又戛然而止。后来怎样? 原作并没有给答案。
曹魏诗歌当中,“高楼/高台上的思妇”成了新热门,思妇常常叹息,却不抚琴,抚琴的思妇,也未必出现在高楼。在高楼/高台上抚琴的,除了乐工,常见的是士人。当一个真正类似高建筑中抚琴女子的完整形象再次出现在五言诗中,是陆机 《拟西北有高楼》。但不再是空灵、高高在上的形态,她面目真实,带着人类的体温:
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玉容谁能顾,倾城在一弹。
叙述者的描绘,除了乐器,更具体到女子的手、熏香、容貌。女子的才情,论动人更胜过她的容颜。她只作“哀响”,却又不一定是“杞梁妻”那样慷慨的哀响了。这次看起来,叙述者终于成功地登上了楼。固然“高楼一何峻”,不过“迢迢峻而安”;固然“绮窗出尘冥,飞陛蹑云端”,宛如宫殿一般,但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女子的琴声和歌声中,叙述者久久伫立,远眺渐渐西下的夕阳。这一次,“再三叹”的,不再是歌者,而成了听者。和《西北有高楼》的叙述者一样,他也担心歌者过于寂寞,于是日影西斜他依然久久相陪,甚至希望带着歌者随归雁远飞。“伫立望日昃”比原作多出了流逝的时间;“归鸿”,比起“鸿鹄”,多了方向。这首拟作,就像是对原作的回答,关闭了原作开放的多重可能,又打开了 自身独有的阐释空间。两个叙述者一旦互为歌者,画面会是一个慷慨陈词替另一个抱不平,而另一个却担心他气坏而不知道怎么办,就安静关切地听着么? 两作对读,真是能引人遐思了。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