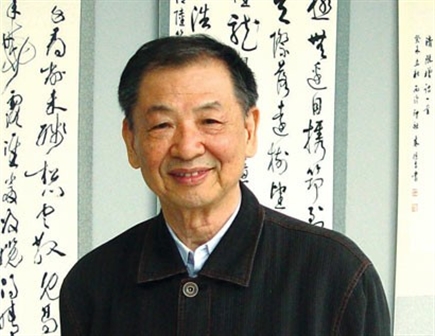
2007年陈应时在李叔同纪念馆留影。 陈应时提供
近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陈应时获得了第26届小泉文夫民族音乐学奖,该奖项是日本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东京艺术大学教授小泉文夫遗孀为纪念丈夫一生对民族音乐学的贡献而设立的,在世界民族音乐界极具分量。在陈应时之前,中国共有两人曾获此殊荣,分别是1995年第7届获奖者黄翔鹏以及2010年第22届获奖者沈洽。陈应时的获奖,不仅是对他在中国乐律学研究、敦煌琵琶谱解读研究方面贡献的表彰,同时也代表着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对世界民族音乐学的贡献,更让人自豪的是,中国的敦煌琵琶谱解读经历一番波折终于站上世界之巅。
拜访陈应时教授那天,天空晴朗,还有些冬末春初的微凉。穿着整洁熨帖的中式西装的陈教授从书房里翻出视若珍宝的泛黄期刊,娓娓道出他60余年潜心民乐“考古”的情缘。
首篇论文一鸣惊人,20年后才获发表
陈应时学术生涯中的一大成就,是论证了公元六世纪的梁朝在七弦琴(今称古琴)上应用了纯律,首次发现在唐宋时期已经形成了具中国特色的纯律理论,并提出了中国古琴的纯律调弦法就是纯律的生律法的新观点和“律种”这一新概念。这项成就,陈应时回忆起来却是源于当年老师的一个提问。
陈应时在上海音乐学院读附中的时候,大学部民族音乐系理论专业招不到学生,就破格让还在读高中的陈应时跳了一个年级提前毕业,免试直升本科。后在读到三年级的时候,归在时任系主任的沈知白教授麾下。沈知白先生开出全英文的书名《音乐声学》让陈应时去图书馆借来当教材读。当只上了两年英语课的陈应时表示为难时,沈先生说:“看不懂的地方问英语老师,专业方面尽管来问我。”就这样,陈应时硬着头皮一面靠沈知白先生的指导,一面靠查字典和英语教师吴熊先生的帮助下,啃起了他人生第一本原版音乐技术的英语著作。
在研读专著的过程中,沈知白向陈应时提了个问题:“古琴音律有人说是纯律,也有人说是三分损益律,究竟是什么律?”谁想这一问,就决定了陈应时日后几十年的研究课题。“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就开始翻阅很多书研究了起来”,陈应时说。
隔了一段时间,陈应时经过考查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去回答沈先生:“他们都对,又都不对”。理由是古琴早期使用的是纯律,后来明末清初时期起才改用三分损益律。当时纯律的代表作是梁朝丘明所传的琴曲《碣石调·幽兰》,三分损益律的代表是明末清初的《大还阁琴谱》。
陈应时在翻阅史料的时候发现,在我国的七弦琴上,因为古人发现了琴弦上的泛音后,才产生了明确泛音位置的十三个徽位。最早记载琴徽的文献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魏国嵇康的《琴赋》,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对七弦琴上的泛音做了科学的理论说明。让陈应时欣喜的是,古琴记谱法相比其他乐器都要先进、精确,甚至左手哪个指按哪个徽位;右手哪个指弹第几弦都有详细记载,“律学是需要计算的,古琴的泛音可以作为研究琴律的切入口”。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中国古代的纯律理论是围绕着七弦琴建立起来的,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自豪地说,古代中国人不仅早于西方发明了十二平均律,而且也早于西方人发明了纯律。陈应时把这一观点讲给沈知白听,沈知白很高兴。“老师说:‘太好了,你赶快写文章,我给你介绍出去发表’”。陈应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嘴角是止不住的笑意。于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陈应时写就了《关于我国古琴的音律问题》这篇文章,投稿至《人民音乐》的副刊《音乐论丛》。
但是,文章寄出后却杳无音信。在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展演期间,陈应时突然接到院办的通知,说北京来了两位领导,在锦江饭店等他去。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应时又惊又怕,连忙动身就走。那时候没有“打的”的概念,从学院到锦江饭店近两公里的路,二十分钟走出一头汗。到了饭店一看,琴学泰斗查阜西和时任中国乐协主席的吕骥就在眼前,“你就是写这篇文章的学生吗”,对方开口问道。原来,《音乐论丛》编辑部看不懂陈应时寄过去的论文,这才转到了琴学专家们手里。查阜西当场表扬陈应时写得很好,并允诺再改得精炼些就能发表。之后,由于种种原因《音乐论丛》被停刊,发表一事就被搁置。机缘巧合的是,陈应时因人介绍得以把文章拿给中国古代音乐史权威杨荫浏看,几天后,杨先生回复说“这文章很好”。先后得到了沈知白、查阜西、吕骥、杨荫浏等一众权威的肯定,让陈应时信心大增。
但好景不长,“文革”来临,一切暂停。过了十年,“文革”结束,学术研究又重新开始。终于,在1983年,陈应时的那篇退稿文章,经修改补充,篇名改为《论证中国古代的纯律理论》,由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宋光介绍,时隔20年后得以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发表。
后来这篇论文分别获得了198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和1995年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艺术学二等奖。
“灵感突发,半夜从床上跳起来”
陈应时在中国传统音乐领域另一大成就,是获得2007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颁发的金钟奖一等奖的研究成果——《敦煌乐谱解译辨证》,在敦煌乐谱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掣拍说”,解决了日本学者林谦三等前人没有解决的“拍”的问题。
敦煌乐谱是唐代世俗歌舞音乐的琵琶谱,原件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其中共有25首乐曲,分别为:《品弄》《倾杯乐》《急曲子》《长沙女引》《撒金砂》《伊州》《水鼓子》等。记谱使用的符号形似日文的假名。其实是一个个数字:一至二十的缩写字。从上世纪30年代起,最早致力于敦煌古谱解读研究的,是日本人林谦三,接着中国学者也开始着手研究——任二北、饶宗颐等都先后发表过相关著作。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叶栋公开发表了《敦煌曲谱研究》一文,并将25首乐曲根据自己研究所得,全部解译付诸演奏录音,“一千多年前的曲谱破译成功”的消息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当时,陈应时正在着手比对林谦三等人的译谱,他发现,“这些译谱无疑都各具价值,但仍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还有必要在解译上下功夫。敦煌乐谱中的 “口”和“、”两个符号究竟代表什么一直存在争议。先后有林谦三提出的“拍子说”;复旦大学权威词学家任二北所倡的“眼拍说”和赵晓生提出的“长顿小顿说”。叶栋在他的文章里引用任二北的“板眼说”,在陈应时看来,任二北是词学家而非音乐家,究竟懂不懂音乐很难说。国学大师饶宗颐得知了陈应时的观点后,请他去香港讲学,并关照:“你应该把文章整理一下拿出根据,看能不能推翻前人?”获得肯定和鼓励的陈应时决定要继续“深挖”下去。
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和南宋张炎《词源》中得到启发,陈应时于1988年发表了论文《敦煌乐谱新解》和25首译谱,在论文中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掣拍说”。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说:“乐中有敦、掣、住三声。一敦一住,各当一字。一大字住当二字。一掣减一字。如此迟速方应节,琴瑟亦然。”这“一掣减一字”,让陈应时有了灵感——沈括时代的记谱法,是以一个谱字作为基本的时值单位来看待的,从今人的节拍节奏观念来说,若以一个谱字为四分音符,则“一大字住当二字”就成了二分音符;在两个谱字相连而后一字带“掣声”时,就变成“减一字”的一个谱字时值,亦即变为两个八分音符。至此,“口”和“、”算是找到了功用。
解决了“拍”的问题还不算,陈应时还一并解决了林谦三1938年提出的遗留问题——两组《倾杯乐》旋律重合——这一跨世纪的学术难题。25个谱子里,曲中乐句重复度很高,按照基本乐理,重复乐句的旋律应该是合得上的。林谦三用自己的定弦方法让两首《水鼓子》重合了,却始终无法重合两首《倾杯乐》。后陈应时发现第12曲《倾杯乐》是C宫调,第3曲《倾杯乐》是B角调,若要求它们的旋律重合,必须将他们置于同调高、同调式。“差点就擦肩而过了!半夜里我脑中突然闪过‘会不会是转调的关系’?当时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陈应时用“变宫为角”和“清角为宫”两种转调方法作了验证,发现不论转成都是B角调或转成都是C宫调,两首同名曲五个乐句的同调高、同调式的旋律都达到了四个乐句的重合,“一变调果然就合上了”,说起这一偶得,陈应时眼里闪着孩子般兴奋的光芒。
一辈子专注律、调、谱、器
自20世纪上半叶起,国际上敦煌谱研究成就的最高话语权一直为日本学者垄断,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逐渐有了中国学者的发声。陈应时就是凭借在敦煌乐谱上的一次次突破,终于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学者的后来居上。从1987年第一次跨出国门赴澳大利亚讲演起,陈应时1989年应邀任英国女皇大学访问学者;1990年1月应聘任英国剑桥大学基兹学院访问教授。所到之处更把流散到海外的敦煌文献原件都找来细细研究。1994年9月,又应邀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国立音乐大学、大阪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武藏野音乐大学、日本音乐学会和东洋音乐学联席例会巡回讲学,所到之处,闻者披靡。
走过世界多个国家,经历过多个潮流的起起落落。陈应时走得越远、越久,感兴趣的面和点却越来越“钻”。他的世界里只有“律”、“调”、“谱”、“器”,而一旦看到有新的学术观点,他就会思考:此人说的对不对?为什么对?然后从各种史料、著作中找出证据。用他自己的话说:钻研的就是一个“点”!
为了研究古琴的乐律,陈应时还跟着梅庵派刘景韶学过一年古琴。这样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钻研一个点的同时触类旁通,现今已经少有人能做到,实属难能可贵。对于现在致力于民乐研究的年轻人,陈应时说:“民乐理论很枯燥,但始终牢记三步: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其实,就像自己解决《倾杯乐》重合旋律问题一样,他相信很多问题没有能得到解决是缺少“牛顿苹果”式的灵感,而这背后几十年如一日的钻研,世上又有几人能够做到?
一直以来,古代宫调中的燕乐二十八调究竟是“七宫四调”,还是“四宫七调”一直未有定论,陈应时最近在进行的国家课题“中国传统音乐宫调理论研究”就基于这一争议。尽管学术界外部环境千变万化,不变的是,陈应时还沉浸在他的乐律学研究中,今年5月,他的心血之作《琴律学》将问世。
文汇报记者 周敏娴
友情链接 |
|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 上海静安 | 上海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