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爱丽丝·麦克德莫特的长篇小说《第九小时》近期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第九小时》荣获费米娜文学奖外国小说奖,这也是这位久负盛名的美国作家首次被翻译引进中文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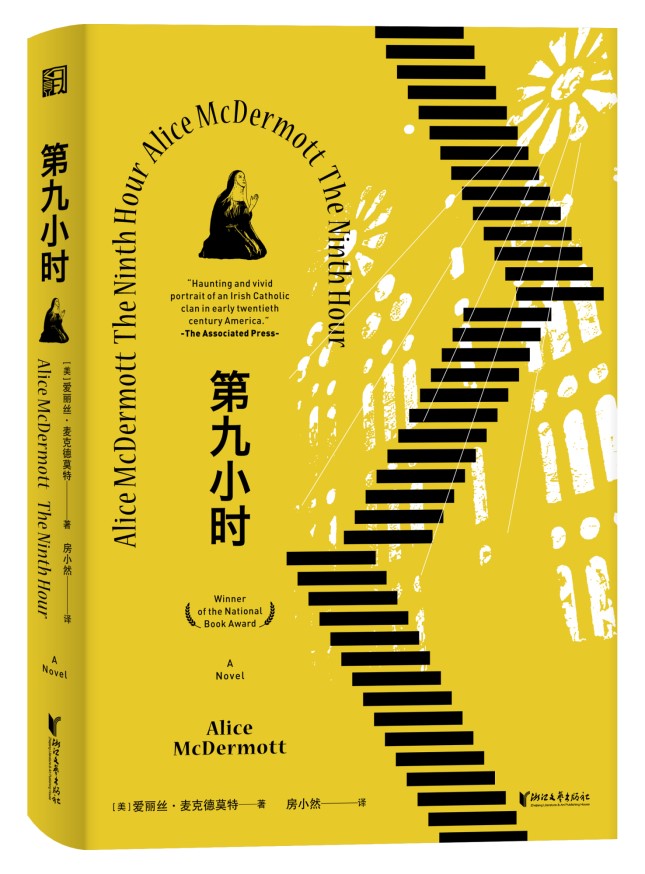
《第九小时》
[美] 爱丽丝·麦克德莫特 著
房小然 译
KEY-可以文化 |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第九小时》书名本身的涵义是从日出算起的第九个小时,那正是下午祷告的时间。小说保持着平静的叙述语调,以细腻动人的笔法,讲述了整整四代人的生活,其中女性之间的情谊尤为感人,她们如何承受生活额外的伤痛,并在艰难贫困中彼此支持、付出、牺牲,诠释了俗世之中爱的要义。
麦克德莫特对爱的诠释是复杂的,她把这种理解倾注在小说的每个细节之中,这不是空中楼阁的爱,而是透过世俗世界中真实的贫困、丑陋与肮脏,依旧闪出微光的感情。如果用她在小说中的话来阐释的话,那么最合适的即“爱是补药,而不是解药”。

爱丽丝·麦克德莫特
>>内文选读:
萝 丝
打父亲这边论,我们有一位身材矮小、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萝丝曾姑奶。一想到这位曾姑奶,眼前就会出现一顶天鹅绒帽和一套淡色、也可能是玫瑰色的细平布套装,仿佛又嗅到她走进屋时,身上散发着的玫瑰水香味。她那戴着手套的手扶着曾属于祖母的长托盘,稳住身形,同时另外那只手拂过餐桌旁成排椅子的靠背,拂过欢迎她的我们每个人的脸颊。父亲跟在曾姑奶身后,拎着行李,喊:“让一让!”同时教育我们,“要说‘下午好!’”“要说‘请再说一遍。’”身为一名门卫的后裔,父亲竟将两个手提箱撞上椅子腿,震得餐具柜子里的瓷器叮当作响。
那时我们还在亨普斯特德市生活,住在我们从小长大的老房子里。房子通风良好,红瓦白边,可隐患重重,总感觉好像房子要塌。人到中年的父亲也因此化身成讽刺漫画里在城市里长大却在郊区有房的倒霉蛋。我们还记得他肩上扛着梯子,手中拎着锤子或套筒扳手,在房间里到处巡视,可什么用也没有。我们的母亲在身体好时,一双眼睛会跟着父亲到处晃,脸上笑意盈盈。
噢,亨普斯特德的那所老房子!还记得房子侧门的玻璃把手已破烂不堪,还有跟肩膀一般高的斑驳脱落的墙漆。不论春夏秋冬,靴子和鞋子永远堆在屋里,破旧的碎布地毯令人想起黑乎乎的地下室的燃油味、煤渣块以及冰冷的煤灰。上三个台阶,就是家里局促的厨房: 深绿色的厨房台面,黑色油毡地板,几个红色橱柜,搪瓷和钢制厨具,丁香与肉桂的香气混合着阳光和灰尘的味道。走过一条狭窄通道就是饭厅。蕾丝桌布,蕾丝网眼垫,蕾丝窗帘,就连窗户上方也爬满了蕾丝。当萝丝曾姑奶稳住身形,挪步进屋,戴着手套的手扶着祖母的长托盘,另外一只手拂过我们的脸颊时,苹果树正在风中繁花似锦,但也可能不是花朵,而是骤雪堆积的雪花。
至于萝丝曾姑奶打哪儿来,为何而来,一直是个谜。“从北边来,”大人们只告诉我们这个,“因为她老了。”萝丝曾姑奶住我们家客房,父亲在前面给曾姑奶开路,我们则跟在曾姑奶后面,搀着她的胳膊,或扶着屁股,走走停停。还记得当时曾姑奶身子在颤抖,也许年龄太大了,但也许因为我们的礼貌周到而激动万分。

客房在亨普斯特德老房子的三楼,正位于屋檐下,是个逼仄狭窄的房间,屋里漆成黄色,有白色的窗帘。
回到楼下,父亲跟我们讲起萝丝曾姑奶和雷德·惠兰的事。他说,那是在波基普西市。内战刚刚结束。一家人正在吃晚饭,突然听到有人敲门。萝丝曾姑奶当时只是个小孩。门外进来一个男人:红色头发,红色皮肤,一条红色伤疤从脖子直到耳朵,像犁从脸上划过。雷德·惠兰只有一条腿和一只胳膊,上楼也是走走停停,每爬一级楼梯,拐杖的头咚地敲在阁楼裸露的木板上。当时还年轻的曾祖父帕特里克是个教师,当惠兰看着全家人给他准备的房间,瞧着房间里的床、洗脸台、小书桌和宽背椅子时,帕特里克默默站在狭窄的房间门口。雷德·惠兰在那个房间里一直住到去世。
萝丝曾姑奶当时还是个小孩子,手里端着给雷德·惠兰准备的晚餐,晚餐扣在盘子里。
十几岁时,每当我们在卧室里充满忧思和烦恼,早上不想醒,或者像母亲过去那样,睡一个下午,父亲就会冲着我们抱怨,语气里透着恼火,好像要大发雷霆,但也会被我们逗乐,因为他也曾是一个喜欢读书、喜欢沉思的人,抱怨时说的也是爷爷常说的那句话:“窝在里面像雷德·惠兰一样冬眠。”
但凡长着一头红发,脸上有雀斑的爱尔兰胖子就是雷德·惠兰。
但凡在客房里住得太久,都有变成雷德·惠兰的危险。
每次讲起萝丝曾姑奶漫长孤独的岁月,必然要提到她与雷德·惠兰在一起生活的四十多年。雷德·惠兰在内战时顶替萝丝的哥哥上了战场。守寡的老处女,嫁出去的修女,我们的父亲这样称呼萝丝曾姑奶。
我们会把茶和其他东西,还有少得可怜的晚餐端到楼上去,萝丝曾姑奶只吃一小碗糊状的东西:汤,苹果酱,再加上掺了奶油的谷粉。她躺在三楼房间里的床上,或坐在椅子上向我们眨眼。虽然在我们看来,她已老得动动身子都会落灰,可还总在脸上涂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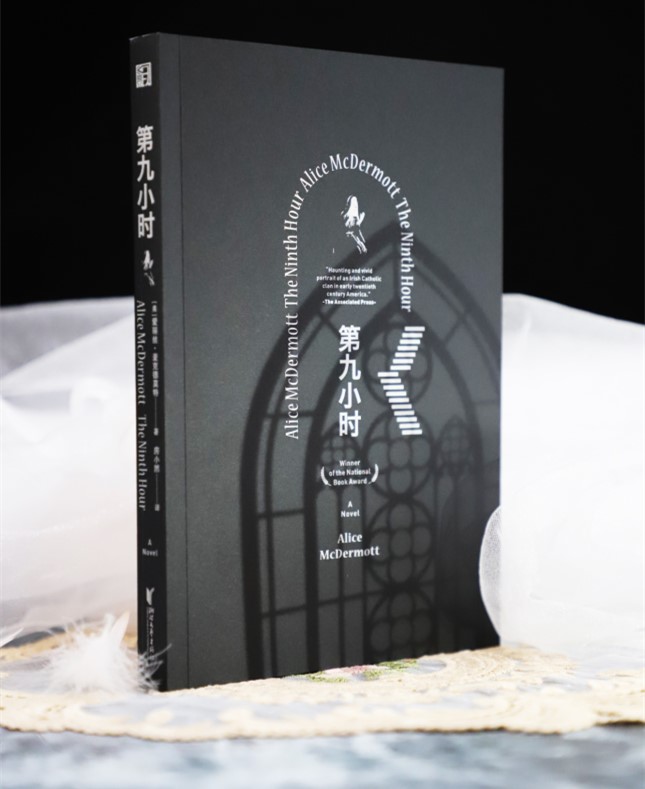
萝丝曾姑奶身旁站着贫病关怀小姐妹会的修女。“真是乖孩子!”给曾姑奶送饭或取走盘子时,修女会这样表扬我们。其中包括我们最喜欢的修女——珍妮。
至于贫病关怀小姐妹会的修女,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母亲也曾想过当修女,但用父亲喜欢的话说:经过再三斟酌,母亲最终打消了当修女的念头。
我们与修女的熟识是在发烧的早晨:醒来时,发现她们白皙的手贴在我们的额头和脸颊上,或者有人把温度计放进我们嘴里,我们睁开糊着眼眵的眼睛,瞧见白色系带帽中不怒自威的脸,命令我们不要咬坏温度计。我们瞧着她们忙碌的身影绕着病床四周转,夜里缠成一团的毯子和床单,在她们干净双手的拉扯之下又恢复了平整,而且变得凉爽。
我们与修女的熟识是在放学回家后漫长的下午,当我们的手握住破烂侧门的玻璃把手时,发现厨房里多了一位护理修女,站在那里如同黑白相间的信号塔。修女用手指抵住嘴唇,示意我们噤声,因为母亲又被带回自己阴凉的房间去休息,以消解忧愁。
在修女长袍经过改革,终于可以看见两侧、可以开车之前,她们总打出租车来我们家,父亲会冲到马路边,抢着付车费。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大家的生活都是如此,还以为但凡出现危机或有人生病,但凡需要圣母显灵时,贫病关怀小姐妹会,圣母玛利亚十字会的修女便会出现。
珍妮修女是我们的最爱。
那时,她已经上了年纪,个子比我们还矮,像穿着修女长袍的孩子。若是她给我们泡茶,她会加热牛奶,并用她的黑色挎包给我们带一小条饼干。从那之后我们再没见过那样的饼干,还记得饼干外包裹着一层巧克力,还有一层散发着夏天味道的薄草莓果酱。
作者:爱丽丝·麦克德莫特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