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近些年大热,美国80后作家莱斯莉·贾米森(Leslie Jamison)是近年美国非虚构文学领域升起的一颗新星。承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传统,她以文学笔调和主观视角展开调查写作,在主题上,她独辟蹊径聚焦美国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心理现实,探索人性共有之病,同时更进一步,在自己的非虚构写作里糅合了更多的私人经历和难能可贵的女性敏感,被评论家视为“用思想面对自我”的典型,极具个人特色。
贾米森的履历本身就颇为丰富,她做过面包师、办公室临时工、旅馆管理员、尼加拉瓜支教教师和医学演员——她认为,“每一段经历都是一个世界,他们还在我的身体里。”莱斯莉·贾米森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本科以及艾奥瓦作家工作坊,并在耶鲁大学攻读英语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非虚构高级写作班。

▲莱斯莉·贾米森
《十一种心碎:痛苦的故事形态学分析》是贾米森的成名之作。本书出版后,莱斯莉·贾米森被誉为“琼·狄迪恩和苏珊·桑塔格的继承者”“非虚构文学领域的下一个‘大事件’”。 在《十一种心碎》里,莱斯莉·贾米森写下了11个真实的人生故事,有些似曾相识,但更多的是闻所未闻。她时而以激越的新闻报道体、时而以犀利坦白的回忆体,抒情、有力地拉开了广袤世界里幽暗的遮羞布,让我们洞见这世上痛苦之深。她毫不避讳我们内心的脆弱,又紧紧地追随“理解”的暖光。她极力于解构和突破对于痛苦的认知,文字中饱含哲思与智慧的温度,反复追问痛苦在肉体和隐喻上的意义。
《出版家周刊》评论:“这是一场既严苛又激越的探寻,它不仅在探讨痛苦本身,也在探寻怎么面对痛苦,从而让我们理解彼此,也与我们自己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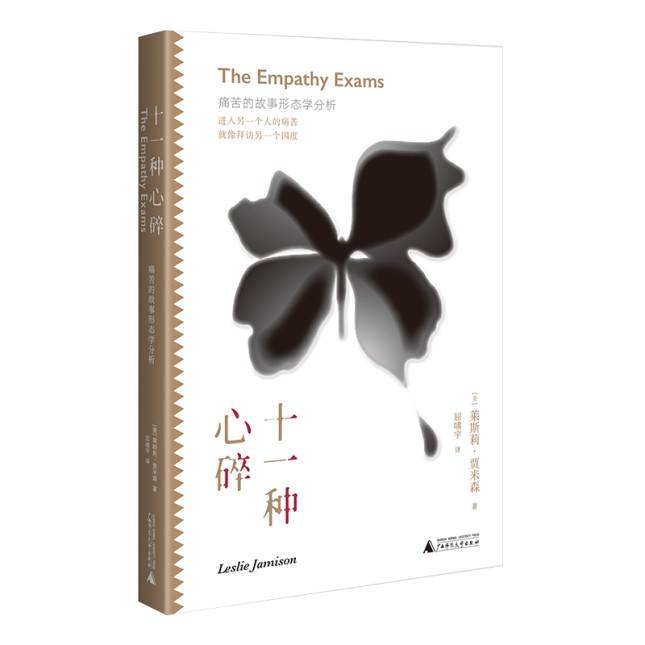
▲《十一种心碎:痛苦的故事形态学分析》
[美]莱斯莉·贾米森著
屈啸宇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摘:
崇高与改变
这档节目开头的一段话既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保证:“本节目所含内容与言语可能令部分观众不适。”这种保证就像一辆救护车、一道伤疤,或者一条因为事故封闭的高速公路,你会意识到自己将看到什么。
这档节目叫《干预》,每集都以一位成瘾症患者来命名:“珍宝”“卡西”“本尼”“珍娜”。丹妮尔在咖啡桌上一字排开12个处方药瓶,而她8岁的孩子说了一句:“我知道真妈妈正等着出来呢。”索妮娅和茱莉娅是一对厌食症双胞胎,两人在家中形影不离,互相监督,以防其中某一个烧掉更多的卡路里。这些成瘾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痛,比如格劳丽娅因为自己的乳腺癌而酗酒;丹妮尔偷吃母亲的止痛药,因为父亲是个酒鬼;玛西因为酗酒丢掉了孩子的监护权,这又成了她酗酒的理由。
安德拉29岁,她有丈夫,有孩子,但他们已经9个月没有生活在一起了。她妈妈小心地按量给她提供朗姆酒,天天如此。每天喝酒的时候,安德拉就咒骂她妈妈:“这都是因为你从来没问过我的想法。”她一手拿着一瓶摩根船长,另一手拿着一大瓶百事可乐。安德拉身上全是瘀伤,因为喝醉后她会从椅子上滑下去,会被门槛绊倒在地。节目告诉我们,大量瘀伤是肝功能衰退的一种征兆。这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得以从科学家的视角观察自我的逐渐毁灭。

摄像机成了一种可以将这单调乏味的一切变得有趣的实验装置:延时摄影拍下了酒瓶里一点点被喝干的威士忌;空镜头里的街角显得如此无可救药;一连串按时间排列的静态图片就可以展示一个人从罪人到殉道者再到一具尸体的全过程;你能清晰地看到一个笑容明媚的孩子如何一步步自暴自弃地成为一个一身针痕的冰毒毒虫,再一步步变成一张阴沉的嫌疑犯标准像。通过这件电子设备,成瘾症患者的疲颓与无望,就这样压缩成了一集集真人秀。
清醒的时候,安德拉谈的总是自己应该对这一切负什么样的责任,但一个醉酒的安德拉所说的只有她的苦难。安德拉的一生都在舔舐着两道伤口:酒鬼老爸的人间蒸发,还有14岁时她遭遇的那场强奸。当安德拉喝醉的时候,她不觉得自己除了承受伤害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事可做。
这档节目的架构就是围绕这样的受害者叙事展开的。节目需要这么一个故事,而安德拉的这个故事正好完美契合节目的要求。这样一个故事可以完美地匹配之后救赎、自我接受的桥段:被人强奸,变得沉默,被抛弃,然后去酗酒。这档电视节目需要的正是这样一张走向自我毁灭的路线图。从酗酒出发,我们一一观察这个女人身上那一出又一出伤痛,这样酗酒就有趣多了,至少比把酗酒当作这些痛苦的根源来得有趣。这些在节目中走向康复的酗酒成瘾者有时谈到这样一种感觉:其他人的人生仿佛有一份说明书,一切都按部就班,但他们的人生却一开始就混乱一片。但是在这个节目上,这些故事自有它们的因果逻辑:丢了工作,然后酗酒了;没了孩子,然后酗酒更凶了;最后,故事的主人公会失去一切。安德拉就是这样。那就清醒起来吧!安德拉,你能做到!也许。
杰森是安德拉的孩子的爸爸,但每个月安德拉来看孩子的时候,这个男人都对她不理不睬。不过安德拉还是会把这个男人叫作“我一生的挚爱”,而他只回了一句:“咋了?”就继续埋头做午饭。他拒绝了节目的采访,没有参与到节目中。他放弃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隔着浴室门哭泣,或者从安德拉手里夺去酒瓶。杰森就这么走了。
我们没有放弃,但我们只是观众。在安德拉和孩子说再见之后,我们依然和她待在一起,看着她再一次开始喝酒。我们亲眼看到了杰森为什么没法继续待在安德拉身边。
这档节目一再强调:参与者同意在真人秀中出镜,公开自己的成瘾症,却不知道他们面对的将是干预。《干预》现在在美国有关成瘾症的节目中排名第一,这让参与者的不知情显得难以置信,但关键在于观众们愿意这么相信。观众们希望了解那些连成瘾症者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看着充满悬念、强大而有力的干预过程一步步走向高潮。这让他们身临其境。“不要放弃自己,安德拉,”如果这些观众在拍摄现场,他们一定会高声呐喊,“我知道你能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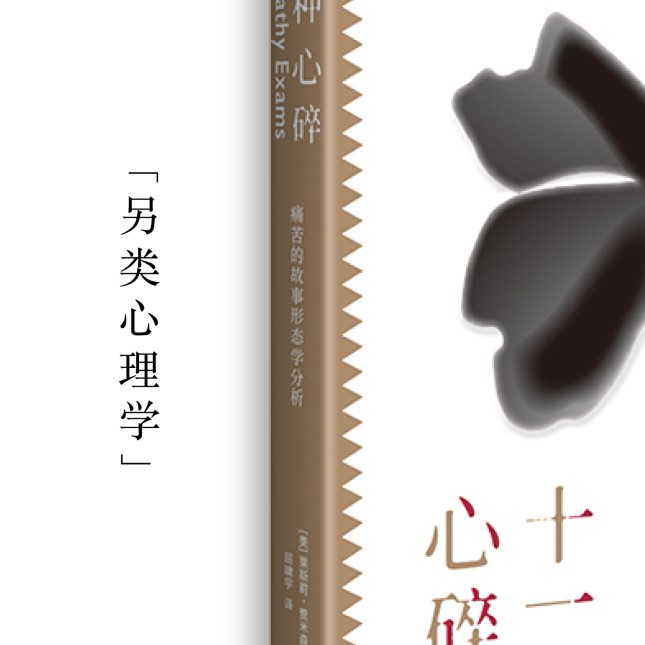
18世纪的哲学家埃德蒙·伯克曾在他的崇高理论中提出了“负痛苦”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建立在对人类恐惧的理解上,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在安全的环境下,在与恐惧保持距离的情况下感受到恐惧,那么这种感受会产生愉悦。一个女人坐在沙发上,拿着一杯霞多丽葡萄酒,看着另一个女人在酗酒中沉沦。电视让这样两个女人共处一室,但屏幕却又把她们分隔开来。这将伯克的崇高变成了一种崇高的窥私癖,人们不再敬畏这样的恐惧,却沉迷于人性深处的脆弱。
节目中负责干预的专业人员被称为“干预者”,听这个名字,你会以为他们来自一部关于末世的超级大片。在我的想象中,这部片子讲的应该是一群从天而降的英雄,身穿黑袍,给这个对资本主义和石油成瘾的世界下了最后通牒。但这些干预者们只是一些穿着职业装、循规蹈矩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在干预中几乎总会强调它的独特性,比如对成瘾症患者说:“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这句话说的正是他们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我们来了,成瘾症患者此后的生活会截然不同。
当然,这是事实。上过节目的成瘾症患者可能不会再接受一次这样的干预了,至少不会在真人秀里。但患者和观众是截然不同的。在普通观众这里,对成瘾者来说一生一次的干预会在每周一晚上9点准时上演。那些不可重复的干预一直都在重复,一周一次,上周的戒瘾誓言结束后,观众又在这一周被拉回到成瘾故事中。下一周,另一个成年女人将坐在母亲的沙发上呕吐,另一支注射器将插入又一根静脉。困扰如约而至,然后被记录在案并按计划解决,接着,整个过程再次被制作成片,下一次的拯救行动又将如约而至。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