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学者戴锦华和王炎合著,集结两人围绕电影议题所做七次深度对谈的《返归未来》一书,虽然谈论的是“银幕上的历史与社会”,其书名却正好可以用来作为本届上海书展的注解。
18日晚,2020年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落下帷幕。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在疫情防控要求下,寻求更智能与人性化的办展模式。除主会场与全国约150个分会场之外,主办方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搭建网上平台,线上线下同步、圈内圈外共享的“未来书展模式”由此初步成型。
而从书展内容上看,“未来”诚可谓频频出现在各大新书分享会、读者见面会上的关键词,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为疫情背景下,未来似乎多了一些不确定性,也就更有了谈论和研究的必要。在与戴锦华所做的题为“回首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对谈中,王炎表示,《返归未来》这本书可以说是全球化催生的产物,在过去几年里,似乎所有人都沉浸在全球化必将顺利推进的乐观氛围里,但通过这次疫情,包括后续越来越多的事情,我们都发现全球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我们不能因此以为,《返归未来》这本书,或者我们过去乃至现在围绕全球化话题展开的讨论已然失效。因为,对历史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未来的勾勒,历史是打开未来想象的钥匙。借用王炎新书的书名《穿越时间的纵深》,我们亦可以“穿越”为期一周的上海书展,在回望和打量中“返归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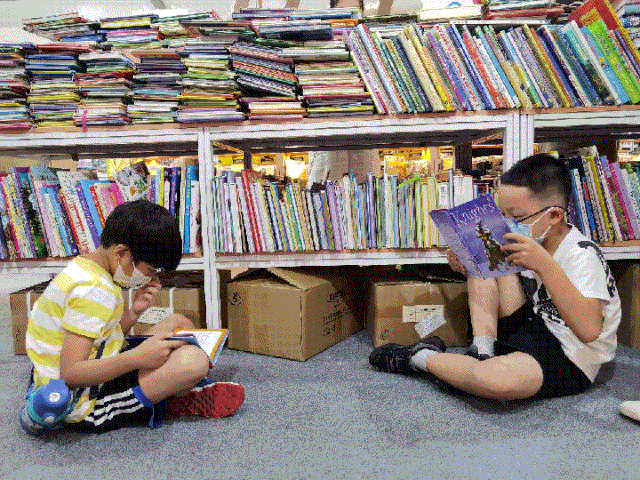
01.
返回历史方式的多样性,对应着历史的复杂多元
当然,所谓“返归未来”,首先在于“返归历史”。而返归方式的多样性,也对应着历史的复杂和多元。
举例而言,作为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一次获全胜的大规模进攻作战,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理当如战史作家余戈所说为更多人所知。但长期由西方主导的“二战”史叙事中,中国战场始终处于被刻意贬低或忽略的地位;战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对滇缅战场的军事合作均采取“冷藏”态度等等原因使得这段历史不为许多人所知。正因为此,余戈潜心十余年,以“微观战史”的研究方法,先后完成并出版了“滇西抗战三部曲”《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1944:龙陵会战》,并在此次书展上集中亮相。余戈运用战场“日记体”让叙述按日推进,以有评论的说法,其描绘的精微程度称之为“战争考古学”亦不为过。

“滇西抗战三部曲”
这并不意味着海飞的小说是对战争的图解。事实上,海飞写作向来追求细节饱满,让文字有画面感。在他的谍战小说中,“城市”向来是一个重要的元素,上海、杭州、重庆都是其作品中的重要地标。城市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背景,其本身也是小说的主角之一。《醒来》的故事起于大雪之夜的杭州,在孤岛时期的上海达到高潮,海飞细致地描绘了那个年代的城市风貌,那些重要的建筑物、市民活动的场所,以及种种风土人情和物质生活细节……在这细腻的历史复原中,那个特定年代里的城市影像和各式人物呼之欲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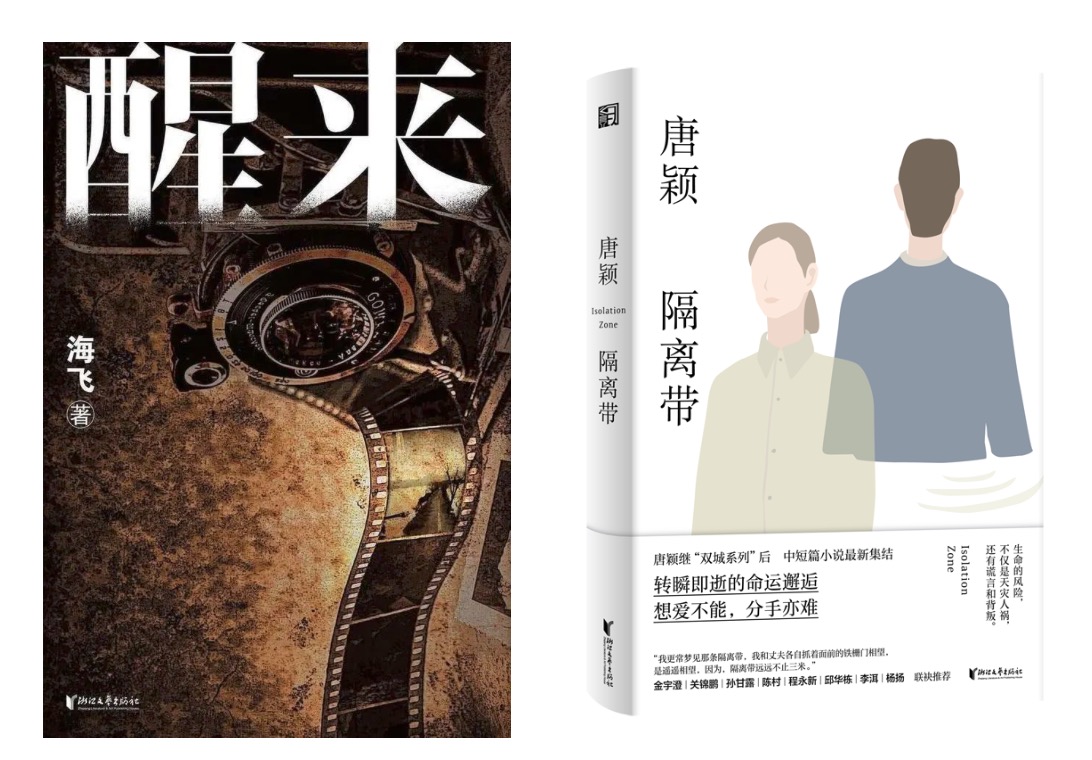
《醒来》&《隔离带》
这一评价也在某种程度上适合用来形容作家王松的长篇新作《烟火》。小说从天津老城的北门外一个叫“侯家后”的胡同开始。各色小人物,从拉车的伙计、做小买卖的和手艺人,到外国殖民者、买办;从革命党、地下党,到汉奸、地痞流氓等等粉墨登场,在历史风云翻卷的背景下,天津的民俗、风俗亦如一幅长长的图卷徐徐展开。在书展现场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王松这样表达他对天津这座城市的热爱。他说:“我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随着‘穿越’回过去的一百多年,在北门外的侯家后一带穿大街钻胡同,和曾经的这些人一起生活,我渐渐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城市,也喜欢弥漫在这个城市街巷里那种特有的烟火气。”
学者陈平原热爱的未必是北京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他热爱的方式与程度非同寻常。身为岭南人,他却是最早呼吁建立“北京学”的学者,并在北大开设“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主持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北京读本”,指导北京研究方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游走于书斋与社会关怀之间,以诸多实际行动为依托,试图借由想象和记忆的碎片来重构一个精神的古都。近期出版的《记忆北京》一书,就收录了他关于北京的二十五篇文化随笔。不止于此,在书展期间于上海图书馆举行的相关讲座上,他声情并茂推介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包含八部分共117图的《北京风俗图谱》,也可以算是爱屋及乌的一个佐证了。

《记忆北京》&《中国书写:紫禁城六百年》
如果说陈平原热爱的是宏大的北京城,作家、纪录片导演祝勇则独爱宏大的紫禁城。自1420年建成算起,故宫(紫禁城)已经走过六百年的风霜雨雪。在书展现场,他感叹,紫禁城的宏大不仅使营造变得不可思议,连表达都是困难的。“这让我心底生起来的那股言说冲动,每次都铩羽而归。它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我的讲述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在紫禁城面前,话语是那么无力。”但作为一名故宫文化的研究者,祝勇毕竟为读者献上了《故宫六百年》,他采用以空间带时间的写作手法,建构了一座王朝政治意义上的紫禁城,也展示了一座集园林、字画、藏书和工艺品之精华于一体的文化意义上的紫禁城。
祝勇最终选择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来呈现,也因为不想写得过于沉重:“在故宫,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一个时间的片段——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段,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回望与重温的是,如今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民众都知之甚少的,迄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他携新书《西边的太阳:秦始皇他爹的阳历年》《天文与历法》亮相书展,从一开始就谦称,自己也是为给北大历史系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学生讲课而自学了一点儿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虽然他在新书里对商代历法的推测和对二十四节气早期起源阶段一些重要环节的论述,但都是非常初步,也还非常不确定的探讨。因为中国古代早期的历法问题,由于数据太少,有些基本问题认识还很不清楚。
即便如此,他依然迎难而上,是因为与读书做学问多强调方法相比,他更加强调知识的价值与作用的。“天文与历法知识,在中国古代的总体知识构成中占有重要份额,更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北宋中期以前,天文、历法知识同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尤为深切。因此,若是完全不懂古代天文、历法知识,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史,必然会有严重隔膜。其结果,轻了,是总隔着那么一层,根本接触不到实际;重了,还不知道顺着这层隔膜滑到哪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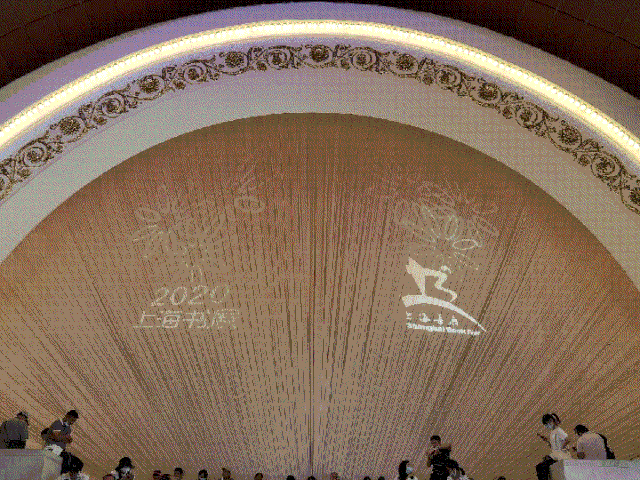
书展现场
以辛德勇的观察,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的学术层面上,学者们的研究工作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推广工作,也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缺憾。这就是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标尺来构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年表。“其缺陷,一是研究的内容缺乏与中国社会实际深切而又具体的联系,二是表述的形式大多没有能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出发,由内而外。”
历史学者姜鸣所著《却将谈笑洗苍凉》,虽非跨越长时间段的宏大叙事,却称得上是基于历史事实的,由内而外展开的大叙事。在书展现场举行的读者见面会上,姜鸣就书里涉及的李鸿章、张佩纶与晚清政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做了阐释。李鸿章是晚清重臣,洋务派代表;张佩纶是光绪年间的“清流”健将。然而在1880年之后,两人开始接近,从交流官场信息、沟通上层关系,到筹划铁路、海军等现代化建设,双方各怀动机,逐渐构筑起深厚而复杂的关系。张佩纶主张振兴国力,需要得到疆吏之首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也要在朝廷中埋设暗线,因而希望将张佩纶收入自己帐下。他们时而配合、时而龃龉,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运作一直延续到1884年“甲申易枢”。中法战争后,张佩纶被流放,李鸿章承担了他的生活费用,还将爱女嫁给他,使张佩纶由“清流”变为“淮戚”,而张佩纶的孙女,正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张爱玲……

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也迎来了十周年的特别活动
02.
身处人间,写人间的作家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方式充满魅力
如张爱玲这般文化名人的传奇身世与人生经历,总是能激发读者的强烈兴趣。评论家周立民在他于书展上首发的《星水微茫驼铃远》里,就为我们呈现了一批“巴金的朋友们”的肖像。本书以沈从文、卞之琳、李健吾、梁宗岱、方令孺、萧乾等六位作家、学者的人生重要片断、思想发展的轨迹为经,以他们和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之间的联系为纬,旁及巴金、郑振铎、沉樱等的交游和精神唱和,借此观照五四之后新文学作家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与时代间的契合、摩擦与冲撞,反思一代文人所走过的道路,并以此为观照,探寻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之路。
与沈从文有师徒渊源的汪曾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赢得越来越多读者的热爱,以至于如今很多孩子都成了“小汪迷”,也着实值得做一番探寻。在《汪曾祺别集》读者见面会上,“别集”主编、汪曾祺长子汪朗把其中原因归结为:一,汪曾祺的作品不端着,他不会摆着一副文人的架子高高在上的,而是给人家常的感觉;二是不装,就是他知道多少东西,他就告诉我们多少东西,他和我们来共同认识这个世界,共同欣赏美好的事物,共同做平等的交流和探讨。三是“蔫坏”。“他的文章好多地方是‘使坏’的,但是他藏得比较深,我们读他的东西读到一定程度,发现他在那儿悄悄地犯坏,就会心一笑。我们慢慢地读,一遍又一遍感受和体会,就发现他的东西比较耐读。”

《汪曾祺别集》
显而易见,汪曾祺即便是如汪朗所说在文章里‘犯坏’,他也是透着诚实的。“别集”编委之一、学者杨早认为,年轻人之所以喜欢阅读汪曾祺的作品,首先就在于他肯跟我们说老实话,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真实的世界。其次,汪曾祺是能够把这个世界描绘得好玩的有趣的人。第三,汪曾祺的文字和他的生活,还能我们带来了浓浓的诗意。“他总是时时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么灰暗、沮丧,或者是平庸,在这个生活里面还有美,还有可爱的、美好的人性,还有希望在人间。”
从七岁开始就读汪曾祺的作品,已与汪曾祺作品结缘30多年的编委李建新就喜欢汪曾祺作品里的“人间味”。在他看来,汪曾祺是身处人间、写人间的作家,热爱生活的读者定然会喜欢他作品里这种人间味。编委之一、作家苏北则把汪曾祺作品备受年轻群体中追捧归结为“灵性”。他说:“所谓灵性,是汪曾祺面对同样一个事物有自己的方式和眼光,他看到了我们没看到的地方。阅读汪曾祺的作品,翻到任何一页,都能很快就读进去。他的书、他的文字,可以反反复复去读,每一次读就像第一次读的状态。”
究其实,汪曾祺作品让人喜欢读,首先是他写出了好的汉语,其次归结到一句话就是,他看世界的眼光和方式是充满魅力的,让我们感到舒服。作家孙甘露喜欢读诺奖得主、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的短篇小说集《衣柜》,也因为他觉得那样的写作很有魅力。“她从具体的时空里抽离出来,但读者会感到许多与现实息息相关,却无法一一对应。” 简言之,托卡尔丘克的作品有现实感,同时富于超现实色彩,体现在她作品里的那种与现实若即若离的感觉,确实会让人着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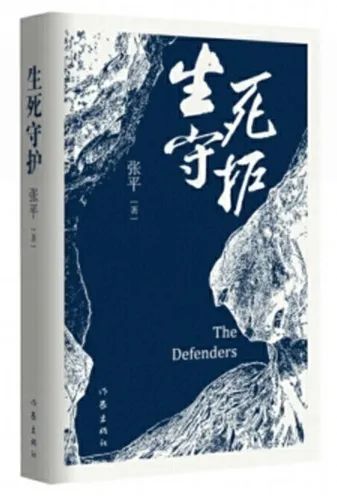
张平《生死守护》
相比而言,如张平这般有志于书写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与现实之间更应该说是存在着一种短兵相接的紧张关系。他的长篇新作《生死守护》从一项市政建设工程讲起,把各种复杂的矛盾由暗地里推到明面上,让各方矛盾突如其来地空前激化。如评论家阎晶明所说,张平在他的书写中直面现实中的矛盾斗争,在展现的过程中最终彰显社会正义、良知。“但张平的作品不断引起各种反响,获得广泛声誉,仅靠‘鲜明主题’是做不到的,在艺术上他的作品有许多可以称道之处。”在他看来,《生死守护》就是一部特别能显示张平在艺术上值得称道之处的作品。“小说的故事性很强,由复杂线索构成,入口又很具体,在进入故事之后,把社会在政治文化各个层面的复杂性展现了出来。这种展现,不是贴标签,也不是喊口号,而是通过充满悬念的故事,生动立体地展现出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好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爱尔兰“90后”作家萨莉·鲁尼的长篇小说《正常人》展现了年轻人初入社会内心隐秘的情绪波动。在对于阶层关系的微妙展现中,作家走走更为关注小说中对于阶层、金钱、原生家庭、暴力等问题的深刻揭示,以及人遵从内心和本性去生活究竟有多难。即便如此,难能可贵的是如评论家孙孟晋所说,这部作品在处理男女情感的矛盾关系中展现了每个人身上向善的一面,而不是让你颓废或沉沦。“萨利·鲁尼特别想去建立一种更有意义的、更特别的视角关系,这个关系其实基于一种平等。它超越了爱情,超越了性爱,这可能是萨莉·鲁尼更想表达的一些东西。”
影响了雷蒙德·卡佛、安·比蒂、爱丽丝·门罗等后辈创作的美国作家约翰?契弗更想表达的或许是人类在精神层面上那种具有永恒意义的居无定所,那种漂泊、流散甚至流亡的状态。他追寻这种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为他就像作家赵松说的那样“对深陷日常困境的那些焦灼心灵,有感同身受般的深刻体会”。这种深刻的矛盾性,也或许使得契弗没能像塞林格、卡佛那样受中国读者关注。如此,自1980年《世界文学》发表《巨型收音机》《绿阴山强盗》等短篇小说后,虽然国内出版过他的短篇小说集,但一直到今年译林出版社完整译介出版首版于1978年,收录其61部短篇小说的自选集《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我们才得以一窥契弗短篇创作的全貌。事实上,一旦我们深入阅读契弗的作品,是很有可能“一见倾情”的。在被问到“你最喜欢的当代外国外国作家是谁”时,作家王蒙曾提到了约翰·契弗的名字。因为在他看来,契弗的小说写得非常干净。“每个段落,每一句话,每个字都像是经过水洗过,清爽、利落、闪闪发光。”而契弗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像本书译者之一冯涛所说,一生挣扎于酒精与性爱之中的他一直对从未曾见过的国家充满乡愁,他一直渴望去往无法前往的地方。“或许人类天生就有这样的向往,用契弗的话说,我们天生就有这样的‘游牧血统’。但在他身上无疑表现得更为强烈。”
03.
对带有终极性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将指引我们在摸索中前行
那些偏爱科学幻想的纯文学作家,想来身上带有更多“游牧血统”的因子。他们热衷于表达目前还不存在的事物,或是有可能无法抵达的远方。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在写于1980年代的小说《使女的故事》里,将故事设定在距小说写作时间两百多年以后。小说以几名历史学家的发现,让一位侥幸逃出的,曾在基列国不幸沦为“使女”的女性,通过录在磁带里的声音,向读者讲述之前发生的故事,其间夹杂着大量主人公对上世纪80年代生活的回忆与反思。在续作《证言》里,阿特伍德呈现了一个发展变化后的世界。《使女的故事》结局十五年后,基列国的统治从内部显露出衰腐的迹象。在巨变将临的关键时刻,三位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的命运开始交错,进而引发了颠覆性的后果。用作家毛尖的话说,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是为《使女的故事》的读者和观众量身定制。“在这层意义上,它很独特。每个读者都能通过它找到看《使女的故事》时留下的那些疑问的回答。阿特伍德用一本书的结构来答疑,几乎是一种文本实验。”

《证言》&《我这样的机器》
英国作家麦克尤恩的长篇新作《我这样的机器》,又何尝不是一部答疑之作或实验之作。其部分作品的中译者黄昱宁透露说,作为一个对科技有着强烈兴趣的文科生,麦克尤恩早在1980年代初就有了第一台个人电脑。而且他还曾经在演讲的时候讲到,他在本世纪初写《赎罪》时就设定里面有机器人。他没法把这样的设定进行下去,就把里面的人物和情节提炼出来,写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赎罪》。“直到十八年后,他才终于写成了这部有关机器人的小说,可见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萦绕了多久。”虽然人工智能到现在也还谈不上高度发达,在麦克尤恩设定的那个1982年平行宇宙中的伦敦,却不仅有我们很熟悉的过往,也有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就像作家小白说的那样,把技术嵌套在过去的历史节点的设计,在科幻小说里并不罕见,如蒸汽朋克的小说,可以用技术决定论来结构故事。“但麦克尤恩做这样的设计,显然带有他对自己的反思,对人类社会的反思,他借助于一个机器人的故事来表达他对历史、伦理等方面的一些思考。”
事实上,很多具有前瞻性思考的科幻作品,即使不像麦克尤恩那样设定现实、未来和过去的三重复调,也多少包含了这三重维度。回顾世界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科学史研究学者江晓原表示,其历史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创作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等一批脍炙人口的科幻作品。在以他为代表的时代,科幻小说展现的大多是科学的美好。但1895年,威尔斯因小说《时间机器》一举成名,随后又发表了《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多部科幻小说。此后,这种带有科技反思精神的小说就成了科幻创作的主流。在江晓原看来,正因为科幻小说作家具有前瞻性,他们更有可能做出反向思考,也因此,也往往是科幻作品集中揭示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在书展现场举行的“恐惧与忧虑:科幻国际潮流与四大母题”对谈会上,他把世界科幻创作分解成四大母题,一是地球环境遭到破坏,在很多科幻小说和电影中,地球已经被人们废弃,成了遥远的传说。二是关于基因工程的前景,基因歧视是一些科幻作品经常涉及的话题。三是人类与外星生命的纠缠。四是造物主和被创造物之间永恒的敌意,这在有关人工智能的科学幻想中有生动体现。“这四大母题几乎涵盖当代绝大部分经典科幻作品。”
无论是科幻,还是科学,都会触及人类的终极问题。在《人类的终极问题》著者袁越看来,人类来自哪里?我们为什么会变老?创造力究竟是怎么来的?这三个问题触及人类的根本,因为只有了解了人类的过去,才能看清我们的未来;只有了解了死亡的本质,才能弄清生命的意义;只有了解了创造力的来源,才能明白人类为何变成今天的样子。他借助专业的科学背景、大量的阅读梳理、实地的采访调查,把目前已知的这三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和推理过程呈现出来,并借此传达这样的理念:今天世界上的所有人,是同一群非洲居民的后代。地球生态系统里每一位成员的利益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进化绝不只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互助才是进化的主旋律。而创造力,正是从这种万物相连的信息共享机制中诞生的。而我们“返归未来”,或许最终也是为了达成这样的诉求。尽管前路漫漫,但对带有终极性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将指引我们在摸索中前行。
作者:傅小平
责任编辑:李凌俊
*文学报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