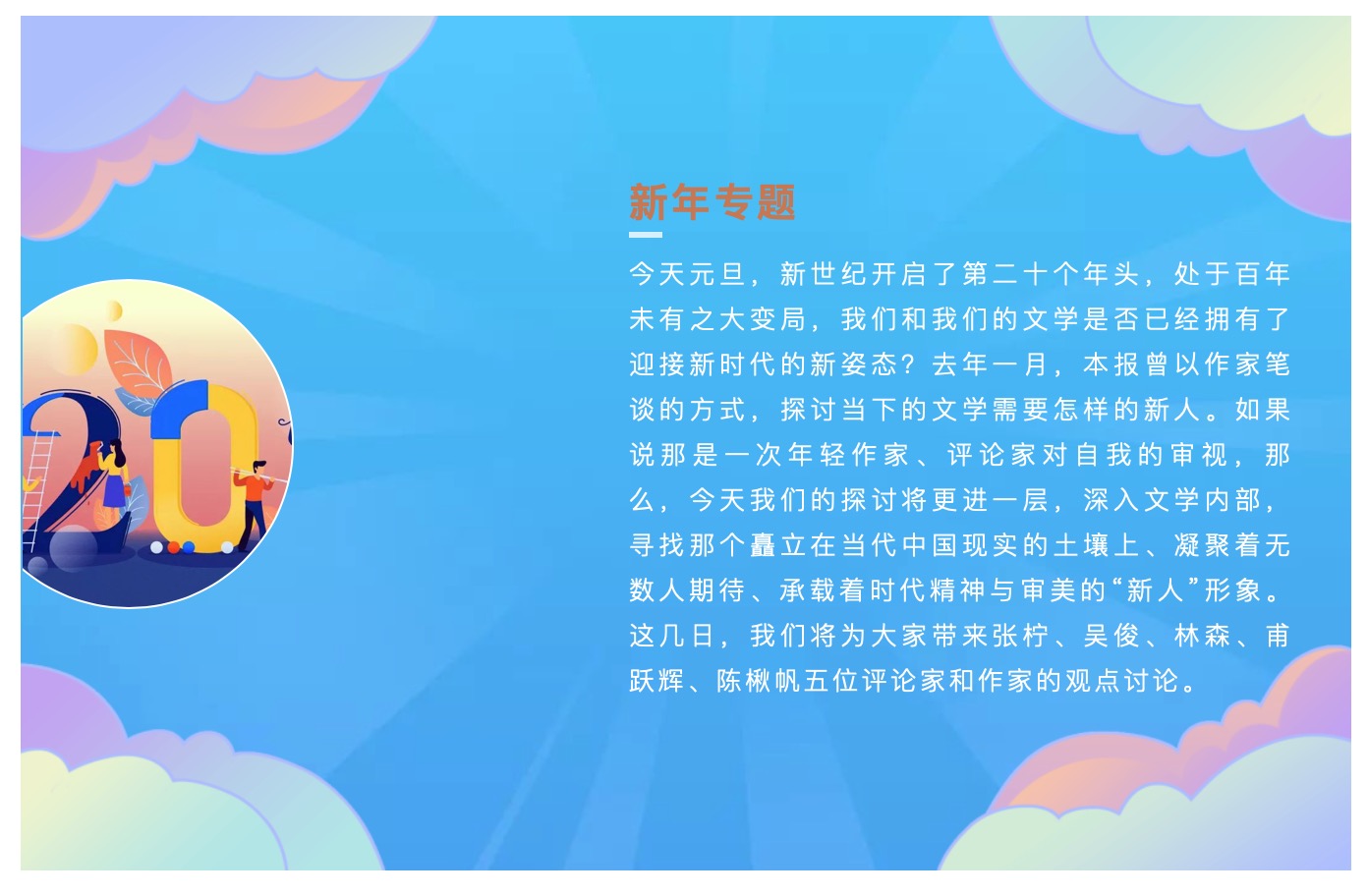

新年第一期封面
专题导语
作家内心机制的更新与重启
陆梅(本报主编)
文学报在去年年初做过一个作家笔谈专题《我们的文学,需要怎样的新人?》,也是呼应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第三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怎样理解这个“新人”之新,铁主席有过一段表述:“面对时代和生活的新变,我们的文学要积极塑造新人形象。新人的新,不仅是生活和工作形态的新,也不仅是社会身份的新,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新,是新的精神气质、新的生命追求,是对自我、对生活、对中国与世界的新的认识和新的想象,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行动与实践。”时隔一年,我们更深一层探进文学的内部,思考新人、新主题和现实题材创作的开掘。

我想所有的“新”都是从“旧”里孕育生长焕发出光彩的。“新”是“旧”的重温和唤醒。如果“新”意味着现代性和内在的精神性,那么这个现代性和精神性也是有母根和源头的。这一点,作家们都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弋舟在笔谈里强调,小说家要注意传统的新颖性,也即我们祖先早就说过的话——温故而知新。
这个“新”,文本之外,指向写作者的话,应当和年龄无关——拥有一颗年轻而苍老的心的写作者实在也不少。或许更首要的,是不拘囿自己,不给自己界限和标签,敢于打碎自己冒犯自己,从惯常的舒适区里跳出来。这一点,作家们心里也有数。
素有理论教养的年轻博士后唐诗人比作家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世界性的困境:倘若“不要以往的、既有的各种主义、话语,那我们的青年作家能够创造出新的贴合当下现实感的主义、话语吗?难以创造新的‘主义’,我们又如何树立起新的文学旗帜?”他给出了一个路径:多点现实,少点主义,回到基本的生活感受中去。
所以你看,清醒的写作者评论者不在少数,年轻一代也都在构建着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然是世界性的困境,那么就从世界性的阅读中我们来看看伟大作家的精神跋涉。这一年,我用上下班路上的碎片时间听了两部经典:《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被一种激情裹挟着,感同身受克里斯朵夫元气淋漓又与痛苦贴身肉搏的灵魂创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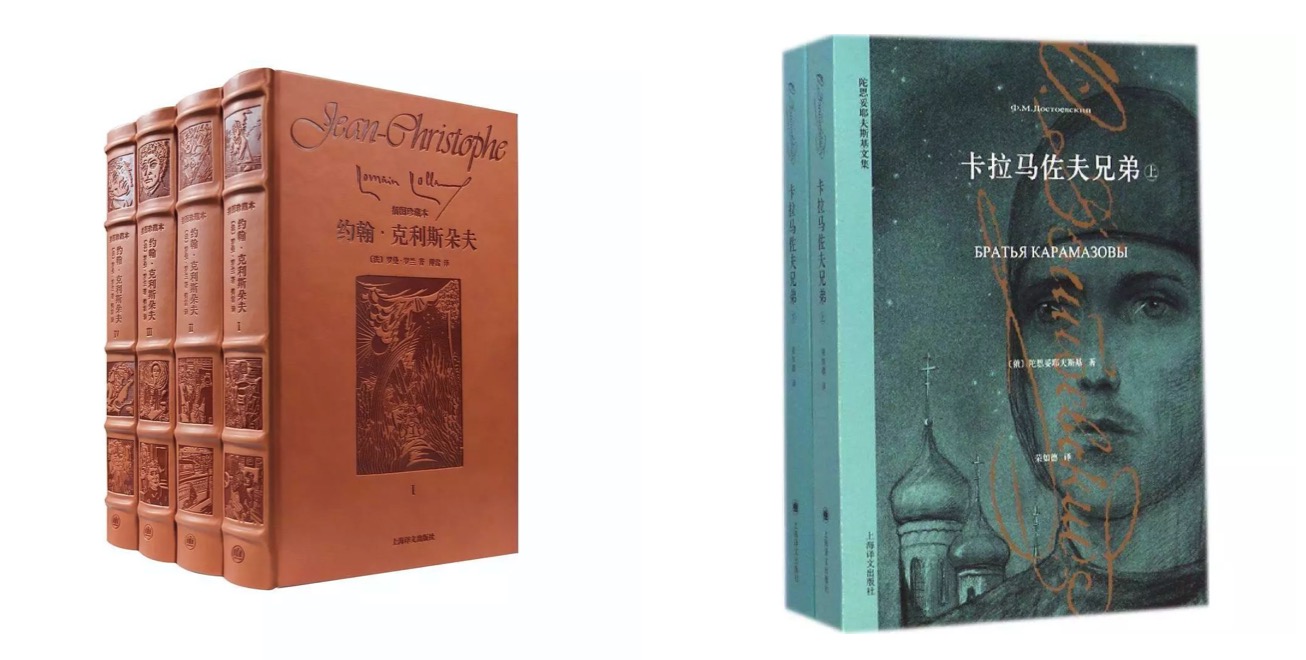
《约翰·克里斯朵夫》,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
《卡拉马佐夫兄弟》,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什么是艺术?一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家最该坚守的是什么?在罗兰还是一个年轻大学生、彷徨无助于十字路口的时候,他有幸得到了来自遥远俄罗斯的宝贵回应。那是老托尔斯泰用法语写给他的38页纸的长信。这封回信以“我亲爱的兄弟”开头,“‘我收到了您的信,它打动了我的心。我含着热泪读完了它。’然后,他试着给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阐述他对艺术的见解:只有那些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艺术才有价值,只有那些能为信念作出牺牲的人才称得上是艺术家。并不是对艺术的热爱,而是对人类的热爱,构成了一切真正使命的前提;只有充满这种爱的人,才能指望在艺术上作出宝贵的贡献。”
读茨威格在《罗曼·罗兰》传记里的这段话,我脑海里跳出一个久违的词:境界。一个写作者要拥有怎样的境界,才能具有自我审判、自我剖析、深刻自省反思的能力和天问精神?好比我们熟悉的俄罗斯文学里,响彻的即是这样一种宏伟的精神追问。如果说我们要在新人、新主题上有所开掘,除了注意传统的新颖性、突出时代的当下性,或许作家内心机制的更新与重启是更重要一环。
罗兰笔下的典型——克里斯朵夫,一个失败的胜利者,他的目标不是成功,是信念——“只有那些能为信念作出牺牲的人才称得上是艺术家。并不是对艺术的热爱,而是对人类的热爱”,一个写作者在提笔时,要经历怎样的煎熬才能走向一个辽阔世界!
也许这面旗帜太嘹亮了,我说一个乱世里的小人物,王安忆《考工记》里的世家子弟陈书玉。这个生活在老上海的一介平民努着力不被乱世吞没,以近乎执拗的愚钝和无畏守护他的老宅。他的一生,就是“乱世当中,低头做人的姿态”,似乎看不到新的精神气象,但王安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因为要保护一幢老房子,他在命运里的自我修炼,“考工记”考的是世道人心,是精神世界的自我磨砺,也是尊严的安放。也许一个好作家,有能力听从自己的内心,也能够深含博纳的巨大积存,滋养和提炼那个直指心灵的文学建制。
文学“新人”形象的可能性
张柠

关注现实,关注时代的精神状况,关注新人形象的塑造,无疑都是文学重要的责任。但我觉得这个话题更适合于讨论叙事性文学,所以尝试从小说的角度来讨论它。
广义的和狭义的新人
说到“新人”这个术语,我们并不陌生。它是十九世纪文学的一个老话题,我们自然想到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名字。其实“新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新人”属于文学创作范畴。凡是作家通过艺术创造而产生的、具有独特性的人物形象,都可以称之为“新人”“新人物”,它对应文学史上已有的“旧人物”。比如,鲁迅笔下的狂人、阿Q、孔乙己、魏连殳、涓生和子君;又比如,普希金笔下的达吉雅娜、奥涅金、连斯基、阿乐哥;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娜塔莎、聂赫留朵夫,等等,都属于艺术上的“新人物”。这些人物性格复杂,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我们称之为“典型人物”。他们有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有些是我们批判的对象。其存在的合法性,不是来自道德的正确性,而是来自于艺术的真实性。
狭义的“新人”,是指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艺术形象。这种“新人”既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又是作家根据历史规律及其趋向,通过艺术想象再造的“典型人物”。更重要的在于,这些“新人”,是作家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辩证统一的结果,而且具有一定的预言性,或者说具有乌托邦色彩。其合法性不只是来自艺术上的“典型性”,更来自历史的合规律性以及合目的性。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称这种“新人”为“中心人物”或者“时代角色”。比如,屠格涅夫笔下的英沙罗夫、巴扎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薇拉、罗普霍夫等。这些来自平民知识分子阶层的时代“新人”,取代了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成为俄罗斯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也是当时俄罗斯年轻一代学习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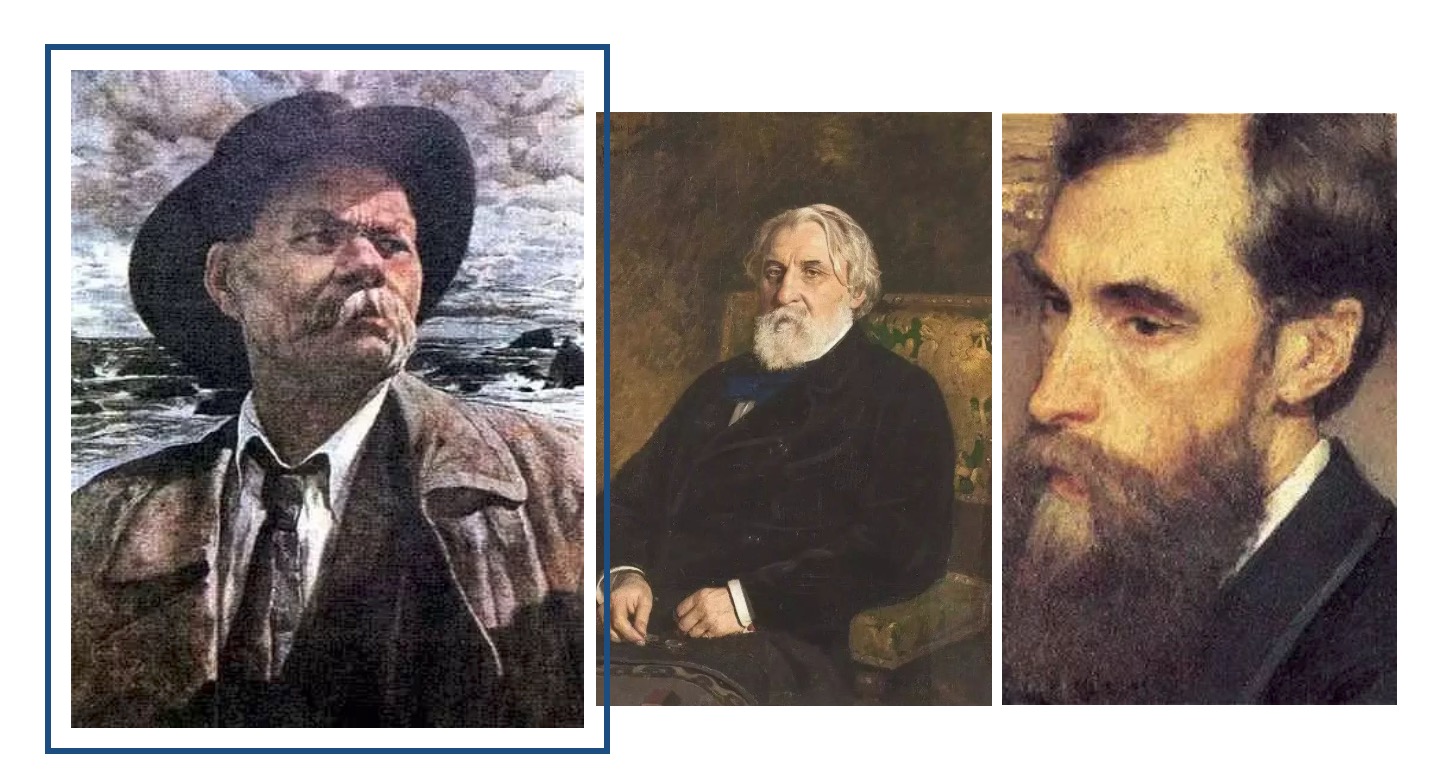
高尔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
作为时代和历史的产物,“新人”势必带有时代印记和历史局限,它们有可能会被更新的“新人”所取代。在高尔基眼里,屠格涅夫笔下的那些“新人”变成了“旧人”,巴扎洛夫们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尽管他们“思想是新的”,但他们的“情感是旧的”,特别是在对待少数族裔、女性、穷人等弱势群体的情感态度上,他们更多的是带有“旧时代的残余”。高尔基试图用自己塑造的“新人”取而代之,比如长篇小说《母亲》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巴维尔。
典型人物和新人形象
在文学发展史的每一个历史时期,文学艺术家都在创造着众多的独特艺术形象,或者用恩格斯的术语叫“典型人物”。但这些“典型人物”并不都是“新人”形象。比如,阿Q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但他无疑不是“新人”,甚至可是说是一个“旧人”,典型的“旧人”,是旧中国性格的缩影,是反封建运动矛头所指的典型。新文学的祖师爷鲁迅,在塑造“典型人物”的时候可谓得心应手,但在塑造“新人”形象的时候却捉襟见肘,最后留下了一个“《野草》的抒情主人公”。所以说,“典型人物”中可以有、但不必然有“新人”形象。个人认为,“新人”是更高意义上的“典型人物”,它们是类种关系。
比较而言,“新人”形象有一些重要的特质。首先,它不囿于人物性格的特殊性,它对人物性格的一般性也很着迷,或者说它不囿于人物性格中的偶然性的因素,而是将这种偶然性提升到必然性的高度,从而显示出“典型人物”的引导性特征,由此体现出它的“前瞻性”或者“革新精神”。第二,“新人”形象与社会环境和现实存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人物形象与时代重大问题和时代风尚之间,有着相互阐释的可能性,它甚至就是时代的“传声筒”。这种人物的“典型性”,与其说是属于自己,不如说是属于时代、属于他人、属于社会、属于历史的,由此体现出它的“时代色彩”。第三,它与其说是属于过去的,不如说是属于现在的;它与其说是属于现在的,不如说是属于未来的。它包含着对未来的美好信念的想象力,以及试图将想象变成现实的勇气。由此体现出它的乌托邦色彩和“理想情怀”。
这里的文学“新人”形象的出现,与其说是我们所熟悉的古典传统的产物,不如说它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古典文化是一种“后视镜文化”:祖先崇拜、圣人崇拜,越古越老的就越好、越有权威,比如,最牛的医生是黄帝,接下来权威性依次递减: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等。现代文明是一种“探照灯文化”,它面向前方和未来,在尊重和甄别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积极开拓。传统的意义不是把我们往后拉,而是为现代文明的探照灯提供新能源。我们所期待的“新人”形象的革新精神、时代色彩、理想情怀等多重要求,决定了它的高度和难度,使得它成为社会和文学历史进程中的稀有元素。
现代派人物形象的偏离

影视剧中的包法利夫人
就“新人”形象塑造而言,现代派文学思潮是一次偏离。在十九世纪文学人物谱系之中,有一种貌似“新人”的“典型人物”,比如包法利夫人,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其实她们跟“新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从审美理想的角度看,这些人物形象有其风格学意义上的“典型性”,从社会理想的角度看,这些人物则属于“终结的人”,也可称之为“永恒的人”,因为她们的生长性终结了。再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问题会显得更清楚。如果说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典型人物”,那么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则是“新人”。阿廖沙这个形象,因其浓郁的理想色彩和乌托邦性质,还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从而成为文学史上的另一种“新人”形象。但它又区别于屠格涅夫的民主主义“新人”和高尔基笔下的社会主义“新人”。陀氏的“新人”属于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斯拉夫派”的“新人”。而陀氏笔下的“地下室人”这个形象,则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物塑造过程中的一次偏离。这次偏离,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声,曾经让尼采大吃一惊,在二十世纪更是后继有人。而类似于阿廖沙那样的“新人”形象,则鲜有继承者。“地下室人”自称心理有问题,他自我怀疑、自我欺骗、自我折磨、自我否定,其实他是一个“自我”极端膨胀的人。他试图把世界塞进自己的小脑袋里,以至于自己不堪重负,濒临疯癫边缘。这种“地下室人”形象的出现,实际上是对“现代理性”和“人的神话”怀疑的产物,是对现实极度不满的剧烈反应,又是对那个时代的拒绝。这是“历史上升神话”衰变的征兆,也是古典“人的神话”幻灭的先声。怎么做“人”?如何创造“典型性格”?如何塑造“新人”形象?如果取消“人”或者“作者”,就像取消“上帝”一样,其结果如何?正如卢卡奇所言,历史衰变进程中的“人”,变得问题重重。
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学思潮,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将“自我的哲学”,变成了“自我的心理学”;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运动,变成了自以为是和自我放逐。这种思潮在文学叙事中,表现为一种极端个人化的描写和叙述。它看上去好像很具体、很有个性,其实它是最抽象的、概念化的,同时又是含混的和雷同的。托尔斯泰称之为“颓废派文艺”。我称之为“胆小鬼文艺”。经过几十年的培育,它盛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一战”和“二战”,“人”的神话以及相应的“资本主义神话”的幻灭,催生了一批另类“典型形象”和“典型性格”:甲壳虫、幻想家、老鼠、漫游者、局外人、拾垃圾者。其共同的特征就是:孤独无助、焦虑不安、怀疑一切、犹豫不决、不相信、不肯定、没有希望和未来。这种“典型性格”,对于“新人”形象而言,是毁灭性的。现代派文学的人物,当然也有自己的乌托邦和希望,比如,等待一个不存在的人,期盼一张不存在的判决书,写一封没有收信人的书信,参与一个没有被告和原告的诉讼,侦破一个没有结果的案件,等等。
现代新人形象的问题
文学道路荆棘丛生也意象丛生,这是一种迷宫或者梦魇体验。让我们离开地下室,离开迷宫和梦魇,重新回到文学的大路上来,回到众人相聚的广场上来,回到故事和故事的主人公这里来,这意味着走出沉思默想的书斋,走向行动和情节。这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新人叙事”的一个重要起点。回顾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学,我们也见到了许多的“新人”形象。作家在提供一大批“典型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在着力塑造“新人”形象。比如,茅盾笔下的吴荪甫,巴金笔下的高觉慧,路翎笔下的蒋纯祖,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柳青笔下的梁生宝,杨沫笔下的林道静、欧阳山笔下的周炳、浩然笔下的肖长春,乃至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和孙少平,等等。粗看上去,上述那些人物形象身上,的确具备了“新人”形象的诸多特征,有理想有明晰的方向和行动能力。但是,它们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最重要的环节(典型性)上面出了问题。比如,有过于概念化和类型化的毛病,使得它最终趋向了“高大全”,催生了“假大空”。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现代白话汉语文学传统中的叙事文学,其“典型人物”的艺术水准,要远远高于“新人形象”的艺术水准。换句话说,在“新人”形象塑造中,作家对“社会理想”的关注程度,要远远高于对“审美理想”的关注程度,从而导致了“社会学”压垮了“美学”,“席勒化”压倒了“莎士比亚化”。我们记住了“小二黑”,但记不住“王金生”。我们记住了“梁三老汉”,但记不住“梁生宝”,原因就在于此。“时代的传声筒”一旦缺少美学的支撑,它就仅仅是“传声筒”而已,而不能变成“精神的号角”。只有在美学的支撑下,才能艺术性地传递时代的声音!这也是今天我们讨论“新人形象”塑造问题时,应该吸取的教训。
猜想新人形象的模样
我们正在期待的、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形象,到底应该长成什么模样呢?由于它尚未诞生,所以我们只能猜想。首先,它应该是一位生活的实践家,“时代精神”的践行者,而不是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沉思默想者。它还应该是年轻的和乐观的,而不是一位察言观色的“智叟”。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作为一个“审美理想”的载体,它必须要极力避免“高大全”模式,首先让自己符合艺术形象的基本要求,我们才能进一步涉及艺术意义上的“新人”。
我想象中的“新人形象”,除了有着浓郁的现实基础和未来憧憬之外,它还应该像一根避雷针那样,矗立在当代中国现实的土壤上。它矗立在那里,吸纳着来自天空和地面的各种电流,聚集着各种信息,汇集各种问题和意识,凝聚更多思想的闪电,而不只是生动活泼的行尸走肉。它是这样一位活生生的人物:所有的人、事、物,都围绕着它,在它周围形成生活的、实践的、怀疑的、沉思的细节和情节的星云图。
我心目中的“新人”,还是一个满腹疑问和问题成堆的人物。它向自己,向他人,向世界提问,就像“提问之王”苏格拉底那样,追寇入巢,不断地追问和寻求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并试图提供答案。这样的形象,才可能成为卢卡奇所说的那种,具有智慧风貌的“艺术形象”或“新人形象”。由于它是艺术形象,因此它不是绝对真理的占有者。它仅仅是行动者、探索者、实践家。因它而生的所有的细节和情节本身,就成了“时代精神”的分子和元素。
我猜想中的“新人形象”,更应该是一位具有“生长性”的人物,它充分吸纳着时代的精神养分,扎根在问题成堆的时代土壤之中,它带着探索的勇气和激情,跟着这个时代一起行进和成长。
改革开放初期的“人物”,如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他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经过四十年的历史变迁,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最后战役的精准扶贫攻坚战也接近尾声,部分地区的“孙少平”,他们的黑馍就要变成白馍,裤子屁股上的补丁也将要彻底补上,进城再也不成为问题。面对这个“新时代”,我们时代新的精神问题是什么?“新人”故事如何开场?“新人叙事”怎么展开?这都是摆在我们“叙事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作家笔下出现了一批“新人”形象,显示出了一种可喜的“新人叙事”。从涂自强(方方)到张展(孙慧芬)再到陈金芳(石一枫),等等。他们或许依然是卢卡奇所说的“问题人物”,但这个时代却不是卢卡奇所说的“衰变时代”,而是一个生长的时代。这些人物,或许还在探求的中途踟蹰前行,或许还有诸多的迷惘。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问题的承载者和求索者。
本人在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三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中,塑造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叫顾明笛,也可以视为上述思考的结果。这位出生在1980年的年轻人,受惠于改革开放的成果,但他依然是一个问题重重的人物。他带着这些疑问出发,走在时代的土地上,不断地行动、探索、实践。顾明笛的问题,不再是孙少平的问题,不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而是在“物质匮乏”问题得以解决之后所面临的新问题:探索和实践的动力是什么?行动的目标在哪里?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呢?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将如何去解决?这些都是前千年未有的新问题。怎么解答?谁来解答?“新人”在哪里?这些都是摆在当代文学面前的新问题。
作者:陆梅、张柠
编辑:郑周明
责任编辑:李凌俊
*文学报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