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教学已经积累了一百多年的经验。早在1897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就开设了“创意写作”专业课。现在全世界已有几百所大学设立“创意写作”MFA项目。自200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经教育审批设立“创意写作”(MFA)专业以来,国内不少高校纷纷加入了培养创意写作本土人才的队伍。但相较西方,中国的创意写作学科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欧美的写作类教材虽然陆续翻译引进了几十种(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创意写作书系”),但能否适应国内教学实践的需求,尚待时间的检验。与其同时,复旦也在主动探索创意写作教学的本土化之路。

王安忆(中)与首届MFA学员合影留念
实践,是创意写作教学的灵魂
实践,是创意写作教学的灵魂。复旦“创意写作”学科带头人、作家王安忆的“小说写作实践”每年开设一次,至今已整整开了十次。每周3学时,一学期上满16周,选课人数限制在15人左右,王安忆几乎是“手把手”地把辅导每一个人。课程正式开始前,她会指定一个有来历的上海地标——比如由六家弄堂工厂的厂房改造成的“田子坊”、曾为“远东第一屠宰场”的“1933老场坊”、上海第十七棉纺织总厂改建的杨树浦“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等,选课学生要去实地探访,然后以当地为背景,虚构一个故事开头;开学后拿到课上讨论,课后回去修改,下次课再讨论,再修改……如此周而复始,最后形成一个情节连贯的故事。表面上看,这份作业很简单:搭一个舞台,任你在上面随性表演。但聪明的作者很快就发现:每一座舞台都有各自的物理结构和文化结构。故事的情节必定要与这舞台“接榫”,方能安顿妥帖。说白了,就是要让特定环境里的一草一木派上用场,而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田子坊(上图)、1933老场坊、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王安忆是一个严格的写实主义者,她常常用近乎严苛的写实标准来要求学员。检验人物和情节的金标准就是逻辑,也就是要合理。初学写作的人,通常想法很多而笔力不逮。他们有很多东西想表达,却找不到恰当的形式——也就是故事。他们往往设置一个看起来了不得的终点,急急忙忙不管不顾地飞奔过去。王安忆则试图告诉他们:小说所看重的恰恰不是那个终点,而是过程。小说写作的学习,便是对这个过程的琢磨和推敲。很多初学者还喜欢搬弄叙事技巧,错综的时间线、变换的视角、浮夸的修辞……这些,在王安忆面前都要经过严格筛选,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为此,每每听到学生抱怨自己张扬的想象、精巧的构思无用武之地。王安忆打过一个比方,让我记忆深刻:如果写实主义小说是一副完整的拼图,那么所谓的先锋小说就是把这块拼图打乱,甚至抽掉几块,但你首先要老老实实把这块拼图拼起来。我想这也是王安忆自己的写照,她的小说从不取巧,从来都是迎难而上,就像武侠小说里用一把玄铁重剑披荆斩棘的侠客。
在完成各自独立撰写的故事后,“小说写作实践”课便进入下半程——“故事接龙”:王安忆先指定一个主题(比如“邂逅”),每个学员围绕主题各自编一个故事开头,大家通过投票的方式选定其中一个,然后在课上讨论,各抒己见,共同补充后续情节,让故事发展下去。在整个“接龙”的过程中,王安忆不会轻易给出她的判断,她尽可能让每个学员凭借在课程上半段积累的经验,为这个集体创作的故事发掘各种可能性。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往往要先吃几次“闭门羹”:学员们最先选出的开头,经过几轮甚或只经过一轮“接龙”,便发现钻进了死胡同,无法继续下去,于是不得不退一步,或者索性另择开头。如此不断试探和修正,故事的发展虽然磕磕碰碰,却一点点有了起色,一点点壮大起来。在我看来,王安忆这门“小说写作实践”课归根结底就是要让学员们明白什么是小说,学会怎样讲故事。
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都是为了表达人类的共同经验和思想
“小说写作实践”之外,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的学员们必修的另一门学位基础课叫“艺术创作方法研究”。自2010年这门课程开设以来,王安忆先后邀请了中国连环画泰斗贺友直、著名画家陈丹青、舞蹈家舒巧、作曲家金复载、滑稽表演艺术家王汝刚、美学家刘绪源、书法家刘天炜等各艺术门类的顶尖专家来为学生做专题演讲,并要求学生就每个专题撰写报告。每次讲座后还会安排一场研讨,由王安忆点评每一个学员的报告。这样的课程设计,源于复旦“创意写作”的核心理念:创意写作是一门艺术。很多学员起初不理解:我们来学写作,为什么还要去了解音乐、舞蹈、绘画、戏剧?王安忆给出的解释,也是后来学员们在听课和写作过程逐渐领悟到的: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都是为了表达人类的共同经验和思想,区别在于表现形式的不同;而不同的形式,既对艺术创作构成限制,也提供了载体和条件。只有充分了解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基本特征,才能真正明白文学创作的特点,亦即文学这一形式的优势和缺陷。

贺友直连环画插图《我来自民间》
比如2016年初过世的连环画家贺友直先生,在为“创意写作”学员们讲课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为了表现农民扛着锄头一动不动的画面,他曾绞尽脑汁。因为绘画是空间性的艺术,画面本身就是静止的,要突出表现静态反而很难。最后,他想到画一只鸟停在锄头上。这便是成功利用绘画“语言”(形式)的绝佳例证。舞蹈家舒巧也曾感慨:人们往往以为中国有多民族的舞蹈,素材很丰富,但素材不等于“语言”。一个小小的素材可以形成一个的舞蹈,生发和渲染一种单一的情绪,却远远不足以构成情节丰富的舞剧。而舞蹈的“语言”就那么手和脚的几个位置,便要无尽地生发与推动下去。无论什么题材,都只能用这样一套“语言”完成作品。这就需要一种内在的逻辑动力,否则便只能将一个个素材堆积起来。她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我们的舞蹈只有字和句,没有严密的语法。”
似乎只有文学所仰赖的语言文字可以“无师自通”?
相较其他艺术门类,文学的“语言”就是俗常意义上的语言,而我以为关于文学创作的某些误解也恰恰与之有关。比如:既然文学和美术、音乐、舞蹈、戏曲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有基本的内在规律和创作原则需要遵守,那为什么总有人以为文学创作无需教授,甚至不可教授呢?是否因为其他艺术门类的表现工具都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很远,看起来有很高的门槛(比如绘画线条、音乐旋律、舞蹈动作、戏曲唱腔等等),似乎只有文学所仰赖的语言文字可以“无师自通”?传播媒介的日益丰富也起到了放大作用,博客、微博、朋友圈……似乎只要会写字就可以“搞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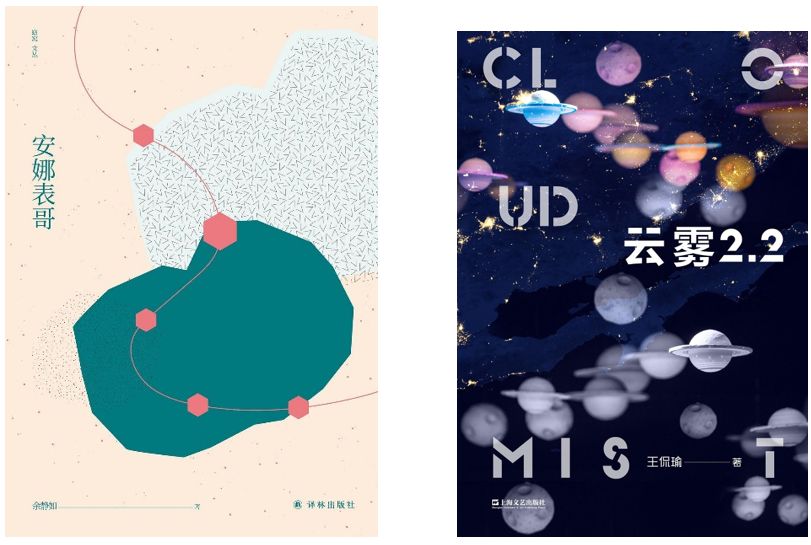
复旦MFA毕业生余静如、王侃瑜201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2017年,复旦“创意写作”专业增开了一门“文学翻译实践”课。很多人把翻译理解成一种再创作,甚至有译者主张译文应该和原文“竞赛”,但这门课的目的不在于此。王小波在他的杂文《我的师承》里曾指出文学翻译对于推动现代汉语臻于成熟发挥的巨大作用。他说,翻译家查良铮和王道乾“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那个年代,最好的文字不在小说里,而在翻译里,最纯熟、最优美的现代汉语是在翻译中诞生的。翻译和创作的区别在于前者已经给定了作品的内容,所要做的只是用汉语按照原作的意思重新书写一遍。“文学翻译实践”这门课的教学目的就在于语言的锤炼。当文字从纸面转移到屏幕后,它的使用变得恣意放纵,许多网络文学作品犹如洪水泛滥,野草蔓生。当我们写下一个汉字时,其实是在动用一个经过数千年生长而形成的庞大复杂的意义网络,每个字都是这张网里的一点,点点相连,互相依存,牵一发而动全身。连字成词,连词成句,既遵从这个意义网络的成法,又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它。如此想来,怎能不慎重一些呢?
翻译,于是提供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炼字”机会。在现成的内容框架里,不用考虑故事情节,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能力,把所有的注意力聚焦于文字。调遣词语,斟酌字句,尽可能忠实、流畅地传达原义。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因为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而饱受非议,但他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他说中国译者最大的问题不是外语不好,而是母语不够好。无论译者还是作家,最应重视的就是汉语素养,这一点却常常被我们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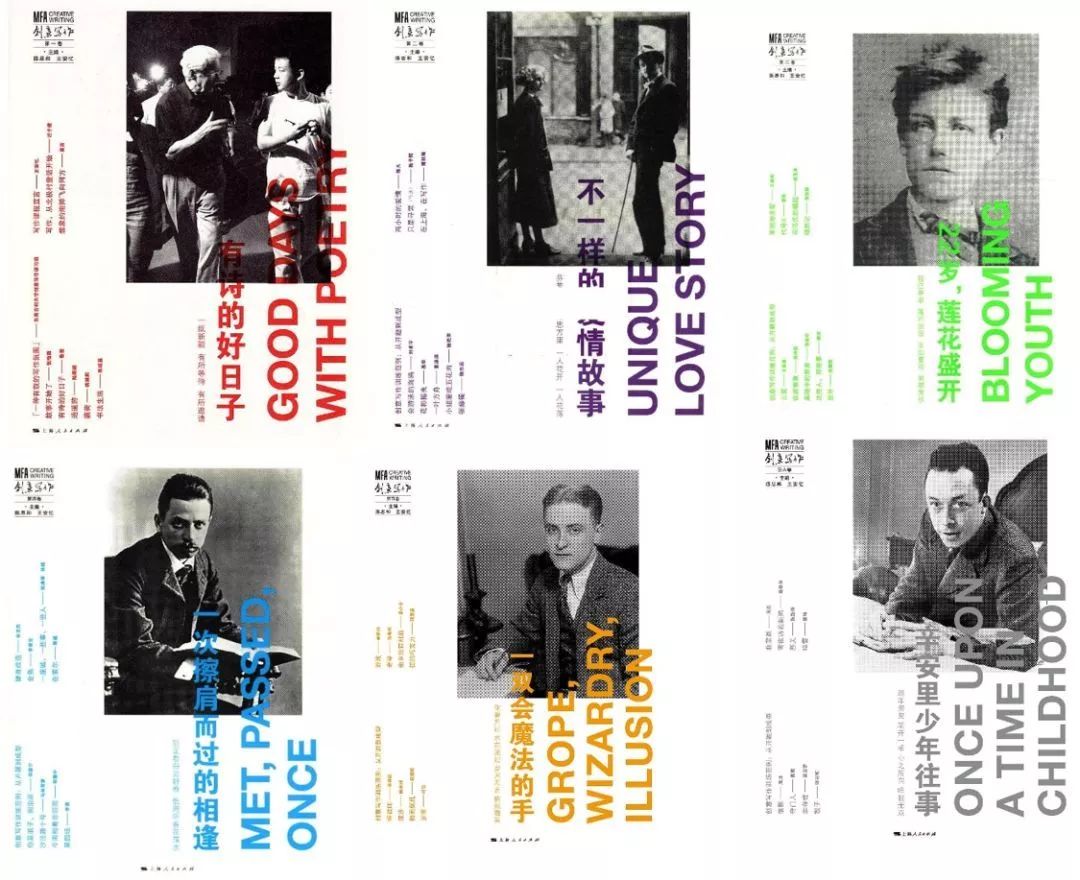
复旦MFA创意写作学生作品集1-6期
除了实践类的课程,复旦“创意写作”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所有学员必须修读“中国古代文学概论”。由于大部分学员的方向是小说创作,所以这门课的重点便是古典小说。我接手这份教学任务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它上成“创意写作”的专业课,而不是学究气的文学史。经过反复思考,我在教案中把汉代以前的“小说因素”分成神话、寓言和史传三大部分,逐一考察每一种“小说因素”经过怎样的酝酿和敷衍,在唐以后促成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又如何进一步影响清明章回的叙述,乃至渗透到一些现当代的小说创作中。以神话部分为例,我将散见于《山海经》《淮南子》等古籍中涉及神话的零星材料搜集起来,向学生展示这些材料怎样整合起来,怎样以不同的方式运用到后世的小说创作中。比如《淮南子》的《览冥篇》和《天文训》分别记载了“女娲炼石补天”和“共工氏怒触不周山”两则神话事迹,《列子•汤问》和《论衡•谈天篇》则是两个事件的整合,但顺序不同:
前者说:
“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
后者则引用“儒书”之言,称:
“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鳖足以立四极。”
简言之,《列子》的记载中先有“女娲补天”,后有“共工触山”;《论衡》相反,先发生“共工触山”,尔后是“女娲补天”。从学术角度入手,考据家们关心的会是文献的字句、断代、辨伪、渊源关系等;但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假如我们把“女娲补天”和“共工触山”看成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说的“事件”(event),那么《列子》的叙述(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只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故事”(story),《论衡》的引用(共工触山→女娲补天)才是具有逻辑关系的“情节”(plot)(因为“共工触山”,所以“女娲补天”),故而更具有小说的性质。这便是我将文学史“改造”成写作教学的一种尝试。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中国的创意写作学科还只是一个蹒跚起步的幼儿。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汉语和英语的巨大差异都决定了我们无法照搬西方的创意写作教学模式,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宝贵的本土经验。
作者:陶磊
编辑:傅小平
责任编辑:陆梅
*文学报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