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在新中国七十载风雨兼程的奋进路上,文艺工作者汲取着建设、改革的伟大力量,“为人民”的创作始终是时代的主旋律、最强音。
我们推出六位活跃在文学现场的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心得,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写作的切入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着相似的姿态——把写作的根深深扎入生活现场,用心用情书写属于人民大众的故事,向着人类的精神高地攀登。
丁燕:我是介入型作家,想留存下一个时代的记忆
文 / 本报记者 何晶

作家看起来貌似可以写很多题材,但事实上,只有那些与他个人经历血肉相连的题材,他才能真正写好。如果我不是在农村长大,我可能很难进入到农民工题材的创作中。
——丁燕
作家看起来貌似可以写很多题材,但事实上,只有那些与他个人经历血肉相连的题材,他才能真正写好。
距离2011年丁燕在东莞樟木头镇一家音像带盒厂找到第一份啤工工作,隐藏“诗人”身份体验生活,已经过去了八年。这些年来,她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纪实文学上。因为于她而言,这是深入介入生活、扎根生活的有效方式,“每当我设想自己将要进入采访现场时,都会异常兴奋,充满期待。”
丁燕说,小说家是通过不断地试错让文字向前推进,而纪实文学作家则会依仗一定数量的现有材料来展开工作。事实上,她正是在生活的第一现场,搜集、记录下人们生活着的时代留存和行进脉络。多年过去,她依然记得当初采访工厂女孩走在工厂路上的感受,“当我走在那条别人看来破破烂烂的道路时,心跳砰砰,感觉目光所及的一切都具有深意,都值得去仔细盯视。”这是一个纪实作家对时代和生活的热忱。
访谈
记者:自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工厂女孩》开始,你就扎根于生活的第一现场,长期的田野调查、跟踪采访,甚至是切实地体验工厂女孩、男孩们的生活。距离那时已经过去了6年,这些年来,你深扎生活创作有没有新的历程?
丁燕:我是2010年8月从新疆迁居到广东的。在新疆时,我的创作主要是以诗歌为主。但是面对广东的高速公路、厢式货车和穿着工衣的人流,我感觉到诗歌表达的有限性。当我转入纪实文学的创作时,一开始也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找了一些女工在办公室进行采访,但写出来的稿子令自己非常不满意。于是,那个想法是自然而然浮现的——“与其采访别人,不如自己去干一干”。事实证明,这个看起来非常笨拙的办法,其实是最有效的办法。到工厂去打工,我并不认为这个行为是“卧底”,而且,我一直很反感媒体将这个行为称为“卧底”。“卧底”带着强烈的目的性,而且有一种从上到下的俯视感,更有一种从里向内的偷窥感。对一个以现实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的作家来说,进入到被采访对象的世界,和他们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其实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当我骑上自行车,拿着身份证去找工作时,就和我要推开草原上一座毡房的门一样自然而然。在《工厂女孩》出版后的这六年,我将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纪实文学这个文体的研究和创作上——这是《工厂女孩》带来的最大改变。

《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封面书影
记者:这些年的深扎生活,感受是否有了不同?毕竟对于作家而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变化,要求他们敏锐洞察。
丁燕:作家看起来貌似可以写很多题材,但事实上,只有那些与他个人经历血肉相连的题材,他才能真正写好。如果我不是在农村长大,我可能很难进入到农民工题材的创作中。当然,在进入工厂做了实地考察后,我还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研究相关的历史和政策,之后才开始创作《工厂女孩》的。我发现,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关系。在创作《工厂女孩》时,我尚处于一种作家的自发状态,只是预感自己能掌控这个题材。但是在《工厂女孩》出版后,我发现也许应该有另一本书与它匹配。于是,便有了《工厂男孩》的创作构想。2016年,当《工厂男孩》出版后,我还是感觉意犹未尽,因为这次采访积累的大量素材还没有用尽,故而,我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工厂爱情》。我觉得有时候并不是作家有意识地去选择哪种文体,而是当他进入生活后,他所面对的那些素材决定了他所选择的文体。“工厂三部曲”的创作从2011年至2019年,这三本书同时成为中国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型时的小小注脚。这个系列作品并非一开始就设计好,而是一步步累积而成的。
记者:这是一种贴近人的生活的写作,你期待自己能够给予时代做下一个怎样的文字留存?对生活着的人们、生活、时代、历史做出自己的一种阐释?
丁燕:我觉得有些中国作家经常会走向两种极端:一种是标榜绝对的自我,有意忽视时代,另一种是打着宏大写作的旗帜,满嘴空话套话。这两种做法都是我所摒弃的。在我的文章中,我也会写到我,但我绝不是因为自恋,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所以才要写自己。相反,我认为我的经历和大多数迁徙者的经历都很相似,当我把它表达出来时,我不仅是写个人的经历,更是留存下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我觉得在创作中,作家要解决好“小我”和“大我”之间的关系。
记者:不难看出,你仍然有巨大的热情深入生活的第一现场,这是自身写作的一种内在需求吗?
丁燕:我觉得作家是分为很多类型的。有一些是书斋型的,有一些是介入型的。这和作家的性格、气质、曾接受的教育等都有关系,也不能强求。对于书斋型作家来讲,当他进入到生活现场时,也许会感觉非常恐惧。但我是属于介入型作家。每当我设想自己将要进入采访现场时,都会异常兴奋,充满期待。记得那时候为了采访工厂女孩,我就住在东莞樟木头镇樟洋社区的工厂路上。当我走在那条别人看来破破烂烂的道路时,心跳砰砰,感觉目光所及的一切都具有深意,都值得去仔细盯视。事实上,小说和纪实文学的创作难度是一样大的,但是,小说家是通过不断地试错让文字向前推进,而纪实文学作家则会依仗一定数量的现有材料展开工作。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在未来的创作中,我依旧会以纪实文学的创作为主。

丁燕重返音像带盒厂
记者:你接下来的创作,是书写中国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母亲的一生。这应该和你特别长于探索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幽微心理相关。
丁燕:在中国历史上,也许像李清照这样的才女比比皆是,可惜因为各种原因,她们并没有留下自己的作品和姓名。女性地位的高下,完全可以生动地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我自然对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有着更深切的关怀。
我即将去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深入采访,以彭湃母亲为原型创作一部虚构类作品。虽然我已做了一些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但还需要长期蹲点,切实体会。因为我要和写作对象之间,建立起一种心灵的沟通——我要真正地理解这个人物,才能写活她。我觉得写一部描述重大社会事件的作品,恰恰不能够用社会的眼光去关注这个事,反而应该写出其中的日常,以及属于个人的发现。
中国工业史在我生命里留下漫长的行走痕迹
文 / 齐橙(网络文学作家)

改革开放40年的工业史,是小说创作的丰富源泉,随便截取一个片段,或者抽出其中的一缕,加入对应的人物以及适当的场景,就可以构成一部小说的架构。
——齐橙
写第一部工业小说《工业霸主》的时候,我已经年满40岁。小说完本之后,我对朋友调侃说,这部作品用掉了我40年积累下来的全部素材。
创作工业题材小说,对于我个人而言应当算是水到渠成,大多数的素材都是在以往的工作和科研实践中积累下来的,并未刻意地追求“体验生活”。工业小说的创作,涉及到三方面的知识:工业技术、工厂经验、工业史。多数读者往往只注意到我作品中涉及到的工业技术和工厂经验,但其实就我本人而言,更擅长或者说更熟悉的,反而是在工业史的方面。
我已经完成的三部工业题材小说《工业霸主》《材料帝国》《大国重工》,反映的都是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工业领域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都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结合的,与其说这三部作品是工业小说,不如说它们只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史的艺术化呈现。有心的读者如果愿意去梳理每本小说的故事脉络,可以发现它们其实只是一部工业编年史,从中可以读到企业放权、承包制、国企脱困、入世、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典型的时代构造出典型的环境,典型环境下有着典型的人物,这便形成了一部工业小说。

《工业霸主》封面书影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家省属中型企业,这家企业与同时代的许多国企一样,经历过计划经济年代里的旱涝保收、上世纪80年代的“政策性亏损”及承包制改革,到90年代,由于不适应市场经济下的竞争环境,它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这家企业的兴衰史,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在我创作的小说中,屡屡能够看到这段历史的痕迹。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进入大学,所学的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专业——国民经济计划学。给我们上课的许多老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上课时随口讲一个故事,便是计划经济年代里行业管理的真实写照。这样的段子,写在小说里便能有鲜活的感觉。
读研究生以及随后在高校任教的工作,都是与国民经济和企业管理相关的。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日常工作除了教学之外,便是看文献、做课题、参加各种项目评审会和政策研讨会等。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冷门知识,了解各种政策的来龙去脉,还能够与不同层级的政府官员、企业干部和普通职员进行深入的接触,体会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和语言特色,这些都是小说创作的良好素材。
例如,上世纪90年代国企面临严重亏损的时候,我曾受某中央部委的委托,前往东北老工业基地调研下岗再就业问题,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走访了下岗工人所在的社区,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我在几部作品中都写到了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内容,其中的许多细节便来自于那一段的经历,甚至有许多对话都是模仿当年接触过的当事人的口吻编写出来的,带着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

改革开放40年的工业史,是小说创作的丰富源泉,随便截取一个片段,或者抽出其中的一缕,加入对应的人物以及适当的场景,就可以构成一部小说的架构。
1983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成立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对包括千万吨级露天矿成套设备、大型火电站成套设备、大型化肥成套设备等一系列重大技术专项进行统筹管理。在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从引进技术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走过了几个阶段,由当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发展到今天跻身世界前列,甚至某些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工业人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也经历过各种曲折、徘徊。一部重大技术装备的发展史,充满了矛盾冲突,也洋溢着澎湃热血。2013年由原国务院重大办牵头编写出版的《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史话》洋洋数千页,随手一翻便是一幕幕令人唏嘘的往事。
曾获得若干文学奖项并即将获得改编走上荧屏的小说《大国重工》,便是基于这段历史创作出来的,这或许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中国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历史的长篇文学作品。
兼具学者和作家的两重身份,我在小说创作时不会满足于对事件和人物本身的描述,而是试图用理论的视角去剖析故事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工业霸主》中关于中国能不能模仿“亚洲四小龙”,完全走“大进大出”发展道路的讨论,并不仅仅是一个小说情节,更是对中国产业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要看懂这一段,需要读者略有一些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材料帝国》里关于地条钢泛滥现象的分析,用到了曾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柠檬市场”理论。这种“把小说当论文写”的创作方式,也算是一种个人的创作风格,在这种风格的背后,是多年学术训练的积淀,这或许也是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吧。
脚踩大地书写时代
文 / 杜文娟

多年前,作家陈忠实曾对杜文娟说,作为陕西作家,希望你写出在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品。在杜文娟的理解中,这不仅是对于中原作家在书写上的寄望,更是将立足现实与现场的写作精神传播向更远地方的期许。这句话,她一直铭记于心底,也在写作中践行始终——从2008年的汶川震后现场,到历经沧桑变革的雪域高原,杜文娟一直在奔走、采访、写作,以小说和纪实文学将见闻和经历的一切镌刻于笔端。在她身上,流淌着广袤大地和奔涌时代所赐予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个人嘹亮终生,都绕不开童年记忆。
我出生的时候,曾经在陕南农村老家生活过十年,即便是后来到了小小的县城,租住的土坯房无门板无窗户,石板瓦片房子冬天飘雪夏天漏雨,缺衣少穿依然是常事,12岁以前没有见过袜子,脚后跟的冻疮成家以后才愈合。最刻骨铭心的是,在我18岁到西安读书以前,没有见过地平线上的太阳,更不知道什么叫广阔无垠,见到的所有太阳、月亮、星星,都在群山之间,山峦之巅。
太阳原来是有大有小的,地平线上的日出日落远比山里的太阳瑰丽辉煌。从此,我喜欢上了远方,在我正式成为写作者以前,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无数次行走和思考中,逐渐感知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伟大魅力,感悟到脚步决定视野,视野决定高度,高度决定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其实这也是脚力与笔力的正比关系。我在风雨兼程和烟火磨砺中逐渐褪去了与生俱来的自卑和怯弱,童年赋予我的品质则一直流淌在血液中,多年以后,方万分感念——敏感、好奇、坚韧、独立思考,是一个作家良好的素养。
呈现边疆普通人的精神高度
2003年第一次前往西藏,是为了看风景,2010年我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前往堆龙德庆县定点深入生活,县上可以派车接送,但我经常乘坐公交车往返于县城和拉萨之间,公交车是203和204路。每次上车,所有人都冲着我笑,其实也不是冲我一个人笑,而是大家相互微笑致意。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欠着身子让一让,我也乐此不疲,挤到他们中间,咧着大嘴打着手势,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颠簸中不乏热心的翻译,如果哪一句翻译不恰当,就会引起哄堂大笑。我深深地喜欢上了那片圣洁苍穹之地,把自己融进去,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我相信真诚和真实的力量。截止2019年,我先后十次前往西藏,四次抵达藏西阿里。触动最深的是雪域高原上的万物生灵,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农牧民、老西藏、在藏干部、边防战士、援藏干部,生死问题是青藏高原众生碰到的常态。

杜文娟在西藏
一次,我随南疆军区一支演出小分队到某边防哨所慰问演出,当时是八月底,冷风夹杂着冰雹,大家都在看演出,回头间,看见一位哨兵正在执勤,便走过去向他问好。离开哨所的时候,与这位战士告别,他向我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对我说,阿姨,非常感谢你。
我吃了一惊,睁大眼睛望着他。
他说,阿姨,你是我半年来见到的第二个陌生人,是我当兵两年见到的第一个女人。半年前一位首长来这里视察工作,跟我说过话,今天你跟我说了这么多话,所以,我要感谢你。
他说自己快十九岁了,来这里当兵两年,没有见过城镇,没有逛过商店,没有见过树木。寂寞压抑想家的时候,跑到蔬菜温棚,看看绿色的黄瓜叶子,红色的西红柿,大哭一场,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下次难受的时候,再去温棚。
扎西罗布是措勤县工商局的年轻干部,他说18岁考到内地读书,路过拉萨的时候,见到路灯以为是天上的星星,看见水龙头源源不断流出水来,吓得四处躲藏,抱住柳树大呼小叫,这花可真大呀。在他广袤的藏北羌塘家乡,没有高过脚踝的植物,不知道树是什么样子,花开什么颜色。
杨保团曾经在藏北一个县担任分管农业科技的副县长,花费三年时间好不容易养活了齐腰高的两株红柳,这件事在县城两百多名干部群众中引起轰动,人们争先恐后地来看稀奇,结果一株被羊啃食了,一株被尿“烧死”了。从来没有见过树木的当地人,善意地以为尿能使树长高,便纷纷给树浇尿。
塔尔钦小学的校长对我说,校园里哪怕有一棵树,一小片绿草,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会提高。
初秋的一天,我到尼木县吞巴村走访藏香、藏纸、藏经雕版艺人,这里也是藏文创始人吞弥·桑布扎的故乡。我亲眼看见人们把破旧的衣服裤子缠裹在粗细不一的小叶杨树干上,一株一株,一片一片,从雅鲁藏布江河岸一直绵延到半坡上。就在这些小树附近,在冰雪融化的潺潺流水缭绕中,巍然挺立着多株两人环抱才能抱住的古老红柳。
我被这种景致震惊了,在这些穿衣服的小树和沧桑古树之间站立了很久,全然不顾紧随身后的野狗和独自一人的恐惧。那种感觉弥漫周身,浸进肌体,润泽心灵。人们对绿的向往,对环境的珍重,对生命的呵护,对人自身的深情,需要多少代人的虔诚延续,多少冬去春来的用心和坚守,这不就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和文明吗?
巨大的困惑日益强烈,既然人们千百年来费尽周折适应和改善生存环境,为什么不迁徙到更适合人居的地方。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难道他们是无福之人?
喜马拉雅山脉腹地有一所小学,全校师生不到20人,有一位公办教师,一位民办教师,公办教师也是校长,实际年龄30多岁,看起来则像50岁左右。所有师生住校,一年购买一次粮食,每个月从县城购买一次蔬菜,一学期见不到一个外乡人。整个冬天洗不了一次澡,夏天老师领学生到河沟洗澡,有时候到边防连队和边防派出所洗几次热水澡。校长对我说,现在一年还能洗几次澡,老一辈人没有洗澡的条件和习惯,为了减少虱子叮咬,在腋窝和裆部各放一团羊毛,吸引虱子,再多的虱子都不会太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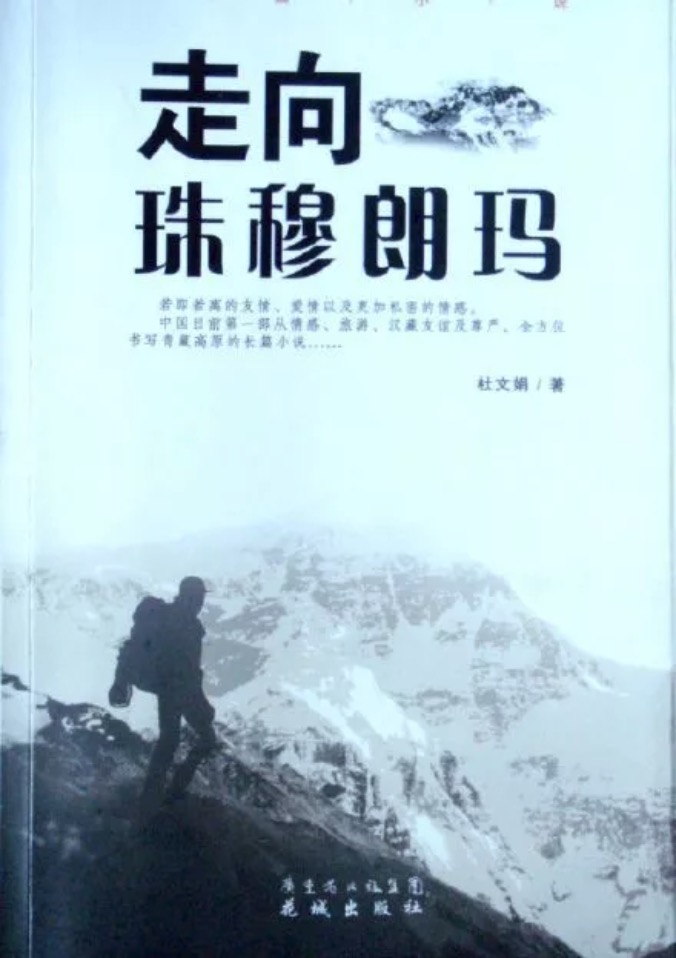
杜文娟长篇小说《走向珠穆朗玛》封面书影,花城出版社
望着苍茫的雪山,我则想,这些孩子是否和他们的祖辈一样,一匹马,一杆枪,一个老婆,一群羊,在边境上放牧一生,孤寂一生。正因为他们同边防战士一样,无论大雪纷飞还是赤日炎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一生一世驻守边疆,才换来了内地的繁荣富庶,和平与安宁。
那一瞬间,我茅塞顿开,边疆不仅是名词,更是动词,保家卫国不只是口号,而是真真切切的常年相守。一位老西藏对我说,西藏的军事位置非常重要。我更加理解了习总书记指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
我把这些经历和认知写进了长篇纪实文学《阿里 阿里》。原本想写成小说,但庞杂的素材无法用小说表现,便尝试着用纪实手法呈现,忠实再现了阿里人跌宕起伏的生命韵律和惊心动魄的历史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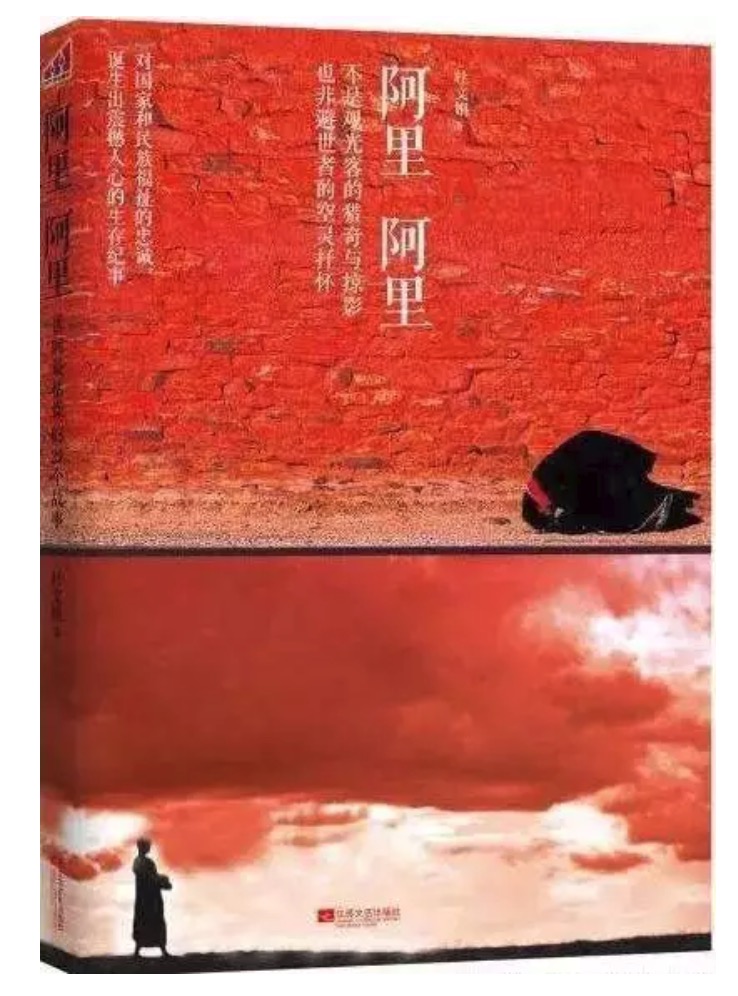
杜文娟长篇纪实文学作品《阿里 阿里》封面书影
访书写高原精神的缔造者和传承者谈
随着在青藏高原行走年岁的增加,愈加觉得应该为这片高寒之地写出更有分量的作品,以此来对应广博深厚的雪域圣地。写什么和怎样写是每个写作者必须面临的考验,为此我辗转纠结,惆怅满怀。
日常生活中,我惊奇地发现,许多人不知道西藏在何方,更不知道西藏短短几十年间发生的跨越上千年的巨大变化,对中央政府几十年来的援藏举措甚为陌生。我不是藏族人,一生一世也融入不了藏文化,但我有一双外来者的眼光,一颗关照远方的心,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我的责任与担当。
的确,我不应该沉默,要以自己的方式和情感向更多人诠释一个领域,一种姿态,一个人的万千思绪。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和回望半个多世纪,即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多年以来,内地人在青藏高原的生活情感,以及与藏文化藏民族的交融与碰撞,一直是我思量和叩问的主题。
当我翻过一座又一座雪山,爬过一条又一条沟壑,终于俯瞰到喜马拉雅山脉褶皱深处的一个县城时,有人指着荒芜中的小城对我说,这个地方原本没有树木,有位县长从新疆带回了白杨树苗子,几十年过去了,县城终于有了几十株白杨,风过时哗啦啦响,那声音真醉人噢,这是方圆几百公里内唯一的树木,许多人骑马步行几天,专为看一眼树木的风采。
我问县长在哪里。对方说,退休后回上海了,听说回去以后也不适应内地生活。他年轻时支援边疆来到西藏,为了修通从县城到阿里地区狮泉河镇的公路,带上锅碗一走就是数天,翻山越岭勘察路基。一个春节,大家发现他不见了,四处寻找,原来他在丈量一个沟坎。老县长也不容易,从参加工作到退休都在西藏,同事朋友全在西藏,也照顾不了妻儿老小,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孩子,夫妻长期分居,得不到家庭温暖,回到上海多孤单呀。
在西藏自治区驻内地一家干休所,我拜访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西藏。他面容慈祥,靠滑轮支架行走,听力和口语都不错,我把《阿里 阿里》双手递到他手里,他摸着四个大字,嘴角抽动,眼睛亮了一下。我说,中央医生,我来看您来了。他望着我,看了许久,脸上忽地腾起笑容。
那一刻,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因为在不同场合听过他的故事和传说。他曾经在国民党部队服过役,新中国成立不久,随一支中央医疗小分队从北京到阿里,原本援藏时间为一年,为了工作需要,往后的几十年都在西藏度过。由于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生活,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终身未娶,却抚养了多名孤儿。
诸如此类的故事如同高原的星辰,璀璨繁密,雪莲花一般鲜活坚强,牧草一样普通坚韧。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民族的脊梁,高原的精灵,高原精神的缔造者和传承者。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平视那片高地,历时四年完成了38万字的长篇小说《红雪莲》。
传递苦难中的人性光辉
“5·12”汶川大地震后第五天,我只身前往灾区当了一名志愿者,和志愿者一道翻越风雪夹金山,将消毒粉押运到离成都800里外的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附近的救灾物资集散点;为映秀一对夫妇联系上久无消息的儿子;在帐篷学校给孩子上课。白天为灾民送粮送药,晚上写稿,走遍了所有重灾区,通过部队海事通讯向外界发稿。在川29天,完成了5万多字的《震区亲历记》,发表在《十月》《北京文学》等刊物上。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的120救护车将我从死亡线上救出来,脖子上的术后疤痕至今清晰可见。震后第一个春节和地震一周年之时,我先后两次重返震区采风采访。
2018年5月至6月,我第四次入川,走访了都江堰、映秀、汶川、绵阳、北川等地,采访了一批在地震中遭受重创的家庭。在栀子花飘香的都江堰,一位女作家真诚地对我说,你到北川以后不要随便问东问西,北川是一个碰不得的地方。当年的北川中学高二学生,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百米蛙泳冠军,“无腿蛙王”代国宏对我说,他用两年时间恢复身体,用六年时间恢复心理。可见,地震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山河破碎家园坍塌,更重要的是心灵重建。
采访中发现,这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叶小舟,冬去春来,时光潋滟,十年,在历史长河中犹如一粒苔藓,大难中煎熬过的身心受创的人们,生存状况有喜有忧,众多生命还在寻求希望。苦难中的坚韧与豁达,顽强中的不屈和善良,正是人世间最美的品质和普通中国人的精神核心。震后心理援助持续十年,甚至代际传递,人性恶与人性美花朵般绽放,作家便是花粉的采集者。在重大事件中不能缺席,写一部正史给当代,就是我创作相关主题作品的目的和初心。从萌发念头、书写到完成,经历了11个年头。
文学是向善向好的事业
阅读和实践告诉我,写重大历史事件和苦难作品不能“轻”和“近”,尤其是非虚构作品,要长久思考慎重落笔,所有文学作品都离不开人,不但要掌握人物背后的风土人情,还要钻研当地的人文精髓,植被地貌。要有一定的时空沉淀和历史纵深,培育史诗般的情怀和文献文学的信念,每一个文字都从心中流出,真实、真情、真挚,才能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作家的责任与担当。
我越来越感知到作家的黄金创作期是有限的,在最好的年华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才不负青春和生命。优秀的作家是独唱演员,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都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就考验作家的脑力和眼力。巨兽向来凛冽而孤独,既然是独唱者,必然是孤独的,作家是一个扎堆没有力量的职业,许多人没有被宏伟目标压倒,却倒在了浮躁的花丛中。珍惜没有成名的安静时光,把理想交给文学,不要倾诉你的孤单。
有同行多次提醒我,为什么放着身边人不写,非要跑到万里之外挖掘自己不熟悉的素材。我也常常反省,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了解更多人的生命体验,会使作品厚重人物丰满。作家的营养来源一方面从阅读中借鉴,一方面从生活中汲取,两者缺一不可。
作家的经历都不会浪费,在能跑的时候尽量跑远一点,能跳高的时候尽量跳高一点,当无心再跑的时候,心中的歌儿自然会吟唱出来。感谢所有走过的路,感谢所有受访的人,感谢快乐和艰辛的经历,感谢不能复制的追问和思考。
凌晨一点,冰雹雨雪突降,雷鸣闪电,羌塘无人区辽阔得毫无道理,狼的绿眼睛由远及近,极力屏气敛息,生怕雷电击中汽车,引爆燃烧。
凌晨两点,我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的横断山区网吧写稿子,拳头、腰刀、香烟、唾沫星子在我头顶飞来飞去,叫骂声声,寒光闪闪。

神山冈波仁齐远眺 来源:摄图网
凌晨三点,神山冈仁波齐脚下,雪粒打得手、脸、屁股生痛。冷风利剑一般,把四肢穿刺成透明体。为了不被冻坏,快速方便完毕,跟人争抢避风的座位。一路上,紧紧抱住用哈达包裹住的笔记本电脑,防止再次被颠坏。
凌晨四点,堆龙德庆县医院院长带着一位医生,进到我的房门,给我吸氧服药,将我从死亡线上拽到鲜亮的人世间。
半夜时分,我被冻醒,整个县城停电,电热毯形同虚设,只能蜷缩成“团长”。
同样是半夜时分,我被饿醒,在借住的村委会找吃的,好不容易摸到一个麻袋,以为有萝卜土豆或者风干的生羊肉,抓起的却是牦牛粪。

青藏高原风景 来源:摄图网
在路途遥远的青藏高原,我学会了要饭,学会了与所有人和平共处,在炽烈的阳光和寒冷的日月里,总是形单影只。刚刚洗过的头发,三分钟就冻成一条条细冰棍,叮当作响地敲打着肩膀和后背。耳环在晨风的摇摆中,滴着鲜血。接打一会电话,手就冻得麻木僵硬。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和磨砺,我的性格逐渐变得坚强和豁达。有评论家说,当我们每天用尺子丈量着分厘得失,用怨怼向着世界讨公平,却不知道杜文娟笔下那些断了前程,赔上性命,善良隐忍的主人公们,还在用生命坚守信仰。
在无数次采访采风和行走中,甘苦自知,同时也有收获,获过几个奖,作品被翻译到国外,随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书架”漂洋过海到多个国家,去往本人足力无法企及的地方。2018年4月,我受哈萨克斯坦文化部邀请访问哈国,在哈中作家论坛上做了题为《我生机盎然的祖国》的演讲。
十余年来,我关注的不单只是青藏高原和汶川震区,还接触过石油、煤炭、电力、铁路、农牧业等,其中一位四肢只剩一条右胳膊的女士令我万分动容。她躺在沙发上,满脸平和温婉,不停地打电话,为一位四十多岁四肢健全的男士找工作,而那位男士只是慕名而来的陌生人。这个画面令我久久不能平静,作家难道只是码字工吗?
我利用到机关、学校、书城讲座的机会,极力宣传受访者的精神和人性之美。一次到西安一所中学讲完课以后,校长当着八百名师生宣布,从今年开始,每年教师节前后组织全校师生为西藏募捐一次。有读者主动联系到我,为西藏的农牧民送去温暖。有的读者和听众因此成为援藏干部和支教工作者。受此启发,我与西藏札达县和改则县民政局取得联系,接收来自内地的爱心传递。采访汶川地震伤残人员时,我也为需要帮助的人联系义肢更换,羌绣出售等事宜。
这些善举只是表象和微弱的,塑造有温度有普世情怀的人物形象才是主旨。文学是向善的事业,作家是自带光芒的职业,这是我近年来深切体会到的。作家在呈现和创造文学作品之外,应该成为自觉的文化传播者和慈善者。
这大概就是文学赐予我的美好吧,也是我以实际行动对习总书记提出的“四力”的诠释和理解。
作者:本报记者
编辑:李凌俊
责任编辑:陆梅
*文学报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