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书特别适合夏日将尽时阅读。黄昏格外漫长,青空上彩云变幻,一本书读至结尾,心里突然清明起来,你从中获得了一点点力量,去面对新的生活。比如赫尔曼·布洛赫的《未知量》。
最初知道布洛赫,是因为托马斯·曼、汉娜·阿伦特、乔治·斯坦纳等人的推崇,昆德拉将他与卡夫卡、穆齐尔、贡布罗维奇并列称为“中欧文学四杰”。但布洛赫在中文世界里至今还是个面目模糊者,译本只有这本薄薄的《未知量》。

米兰·昆德拉:穆齐尔和布洛赫给小说安上了极大的使命感,他们视之为最高的理性综合,是人类可以对世界整体表示怀疑的最后一块宝地。他们深信小说具有巨大的综合力量,它可以将诗歌、幻想、哲学、警句和散文糅合成一体。
汉娜·阿伦特:布洛赫生命的线路和创造力,他的工作场域,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圆;相反,它更像一个三角形,其每一边都能被准确地标识出来:文学—知识—行动。唯有他,才能以其独特性充满这个三角形地带。


托马斯·曼:我对赫尔曼·布洛赫怀有崇高的敬意。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优秀的诗人。他的《梦游人》是一部令人钦佩的作品,而且我认为他的《维吉尔之死》是迄今人们运用小说这个灵活的手段所进行的最独特和最透彻的尝试之一。

赫尔曼·布洛赫
赫尔曼·布洛赫,1886年11月1日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家庭。在维也纳接受工程师的训练并研习哲学与数学。他逐渐融入了维也纳的知识分子生活,结识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诗人里尔克、作家穆齐尔等。《梦游人》是其45岁时出版的首部重要作品。1933年发表《未知量》。1938年,他受到纳粹迫害,随后在朋友们,包括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发起的营救运动中获释,流亡至美国。晚年一直在耶鲁大学研究群众心理学。1951年5月30日因心脏病去世。代表作《维吉尔之死》初版于1945年,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清白无辜》在1950年出版。
有评论认为,昆德拉关于小说的两个最重要的认识:发现说和媚俗说,都来自于布洛赫。昆德拉在接受访谈时说:“我将不遗余力地重复,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而他的这句话,正来自于布洛赫所说的: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而“媚俗说”据考证也是布洛赫首先提出。
汉娜·阿伦特曾在评论中写道:“赫尔曼·布洛赫不由自主地成为了一位诗人。他天生就是诗人,但他并不想成为诗人——这正是他天性的根本特征。这一特征启发了他最杰出的书中的戏剧性情节,并成为他生活中的基本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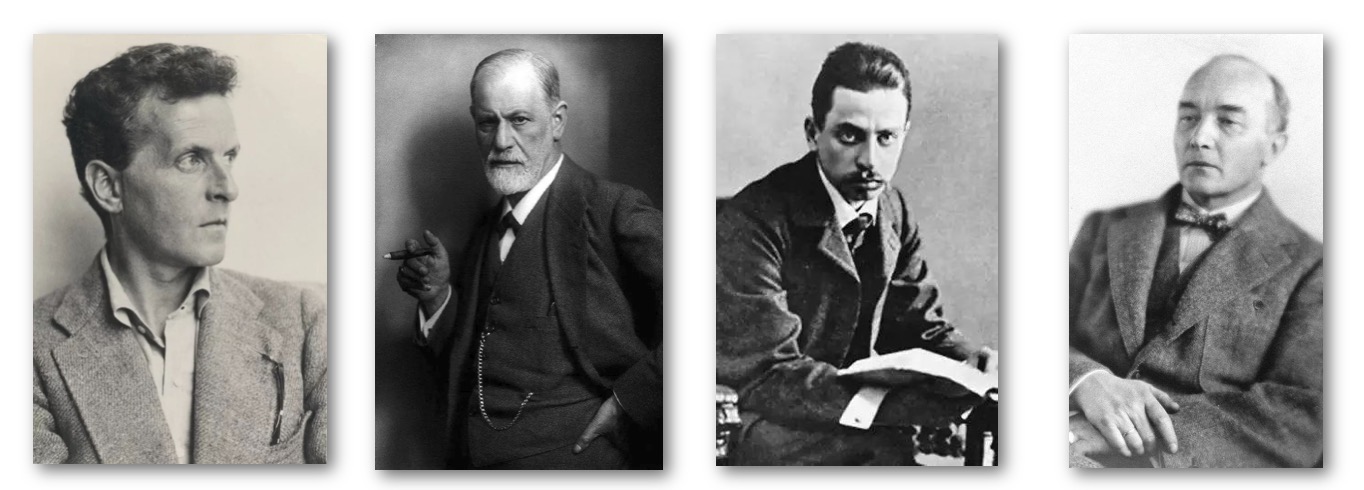
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里尔克、穆齐尔等都曾在布洛赫的“朋友圈”里
虽然我们至今只能看到《未知量》,但布洛赫的写作特征已经可以经由阅读这部作品而凸显。故事围绕数学博士理夏德·希克的工作、家庭和情感展开。理夏德的父亲生前是个如苦行僧般的天文学家,他的过往在家庭内部留下了巨大的暗影。他死后,其余的家人都在暗影的围困中焦灼不安地摸索前行,试图在科学、艺术、宗教、情感中找到生活的支点——理夏德从事科学研究,弟弟奥托痴迷于艺术,妹妹苏珊皈依宗教,母亲卡塔琳妮则对奥托的同学卡尔产生了某种暧昧情愫。
由于父亲投下的童年阴影,出于对模糊的恐惧和忧虑,对精确的渴求和追寻,理夏德选择了全然由理性主宰的科学——数学及天文学,试图以确定性不变应万变,从而找到某种坚定的,可以借此抵挡现实世界中的非理性,并使自己继续生活下去的东西。但令他意外的是,在他看似精确的生活背面,依旧有一团包含着不可知性的暗影,不断发酵膨胀,生活的真实面貌就是他的“未知量”,这种不可知性最终演化成让人不知所措的激变——他与女学生坠入爱河,一家人中最感性和软弱的奥托则毁灭于非理性的欲望。理夏德被毫无预兆的死亡震撼,在痛哭声中,理性与非理性最终和解,他豁然开朗,意识到在关于科学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知识,就是爱。面对现实世界他不再如履薄冰,即便看到了它的骇人之处,即便知晓它终将从黑暗走向黑暗,却依旧能够投身生活与爱,坦然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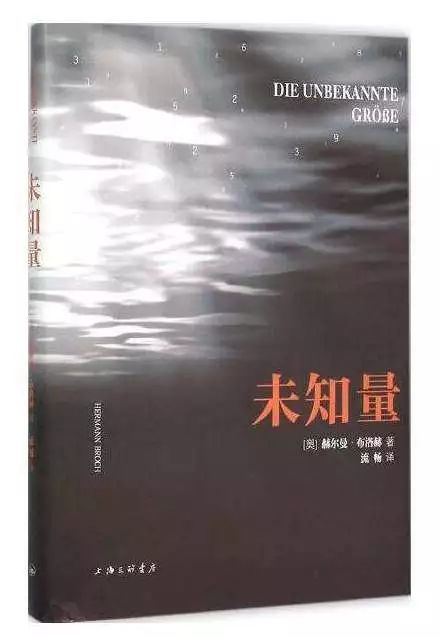
《未知量》
赫尔曼·布洛赫/著
流畅/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5年12月版
从故事本身来看,关涉的命题可以将之归于成长小说,但《未知量》成书的1933年,纳粹的阴影已经笼罩欧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中父亲留下的巨大阴影,每个家庭成员在理性与非理性中做出的抉择,便多了一层隐喻意味。
《未知量》并不是一本好读的小说,碎片化的线性叙事,大段大段的哲学思辨,各种数学和天文学名词,都对阅读构成了干扰和挑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小说又有着如同音乐般均衡的结构,关于知识、生活和爱的主题跌宕其间,布洛赫的文字轻盈、简洁、深邃,充满决断力。读这样的作品,如同行走在浓荫下一条笔直的路上,四周是无尽的溪流,但你知道,它们终将带着你奔向同一个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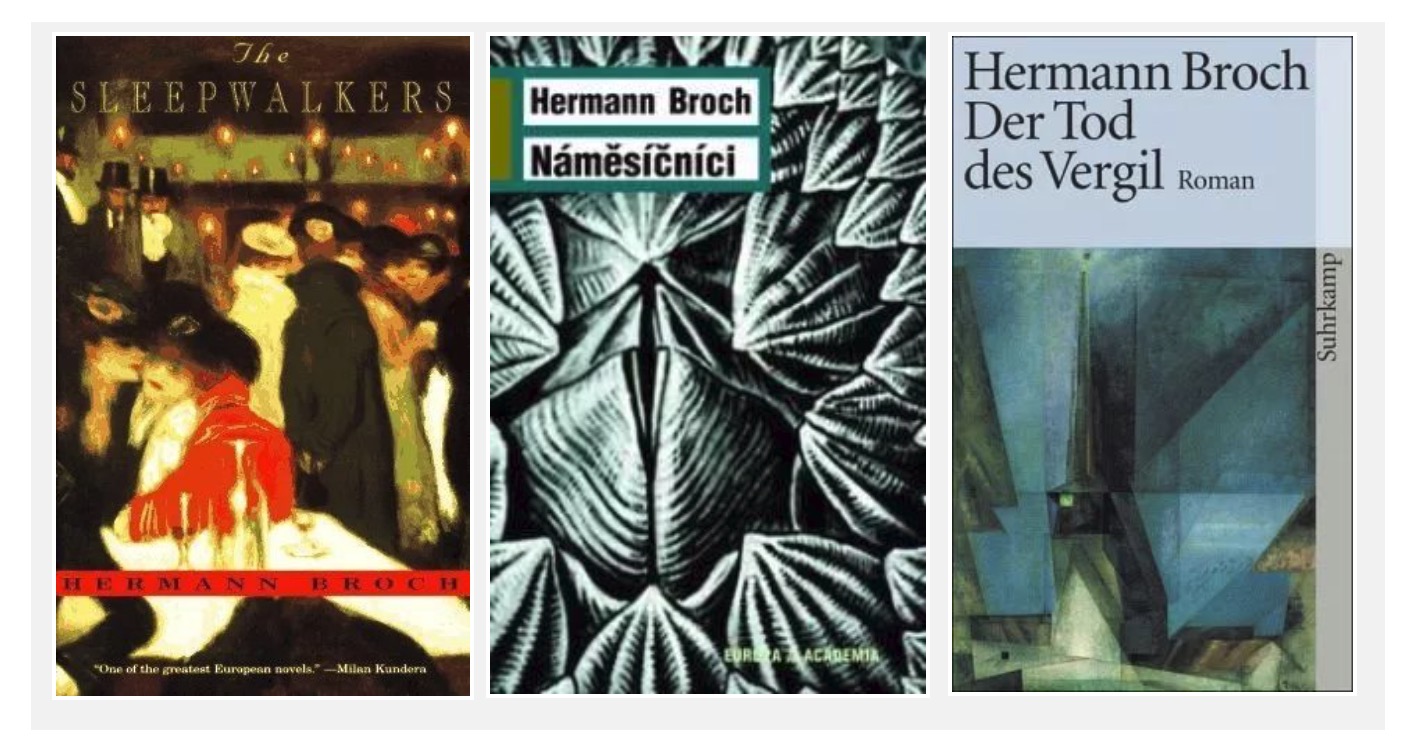
赫尔曼·布洛赫部分作品
作者:淼淼
编辑:李凌俊
责任编辑:陆梅
*文学报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