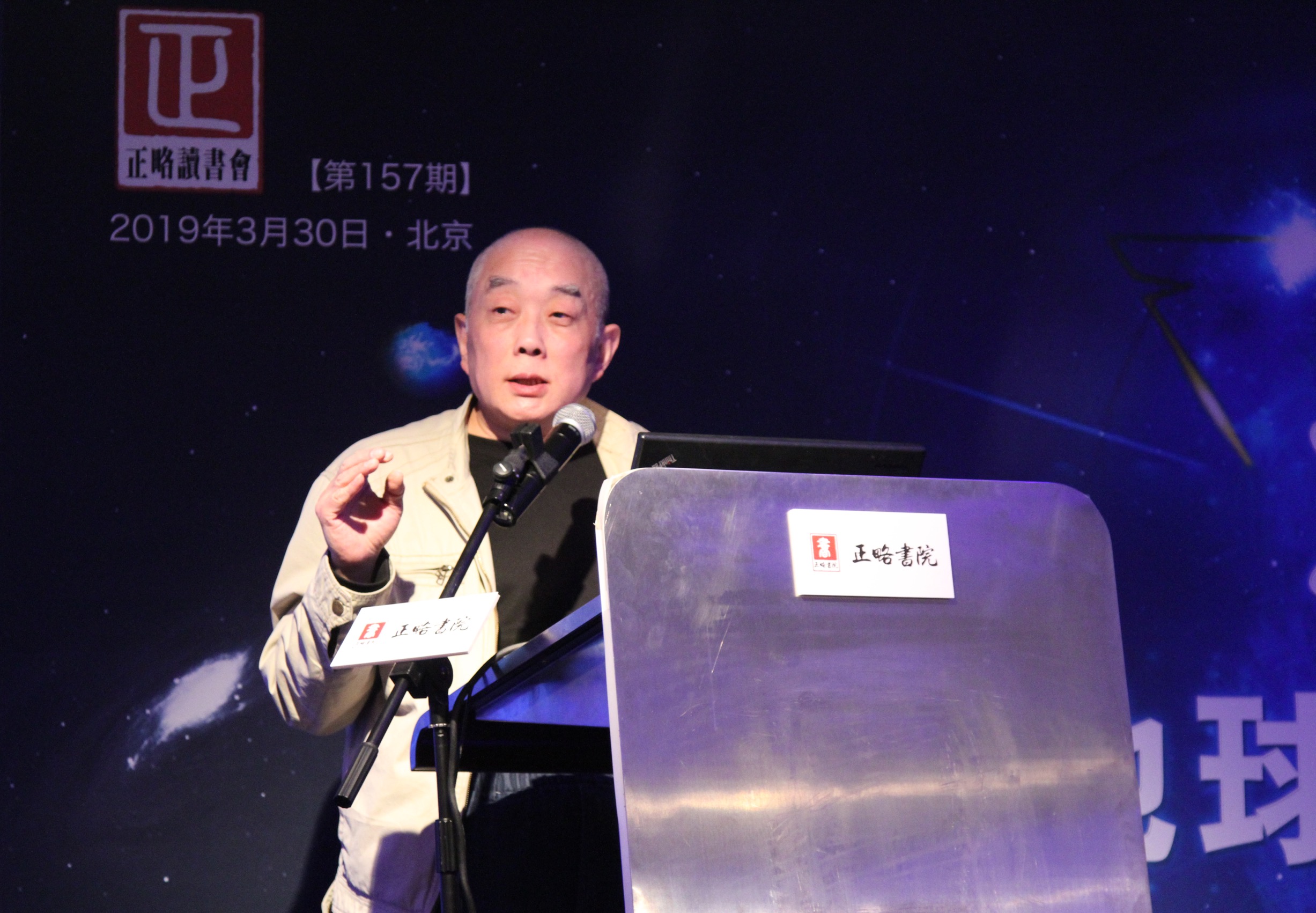
江晓原做客由正略集团、正略书院举办的第157期正略读书会暨日月论坛第6场活动
“中国科幻进入了元年,此后要远离科普,告别低端。”日前,作为资深科幻影迷、科学史专家、科幻作家的朋友的江晓原,在由正略集团、正略书院举办的157期正略读书会上与听众分享中国科幻与国际科幻潮流,并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展开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值得一提的是,还在2015年,文汇讲堂的老朋友、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前院长江晓原,就在他的书《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中做出如下预言:中国科幻元年,它只能以一部成功的中国本土科幻大片来开启。去年由刘慈欣小说改编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国内票房突破46亿元人民币,证实了江晓原的预言:中国科幻终于迎来了元年。
面对许多赞誉背后的反对声音,江晓原说这是因为许多掏钱的影迷并没有可以发声的话语权。由此有了这场“江晓原:《流浪地球》与国际科幻潮流”的讲座。
科幻元年必须满足诸多条件,包括改变国人认知
科幻元年从何时算起,不同的人大概会有不同的解读。就如同谈到国际科幻的源头,有些人追溯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也有人认为科幻的祖师爷是天文学家开普勒所写的《月亮之梦》,想象了生活在月亮上的生物。对于江晓原来说,要成为“元年”必须满足一些必要的条件,并不是但凡第一次出现就可以承担起这一重任。元年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资源进入到科幻产业,意味着更多的科幻电影和科幻作品的问世,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优秀作品逐渐涌现。不仅如此,对于江晓原来说,开启中国科幻元年,还要求根本改变国人对待科幻作品的基本认识。因此,元年必须要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流浪地球》的票房成功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激励机制,足以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到这个行业。事实上今年已经有好几部科幻电影都在投拍,可能2019年就会上映。在江晓原看来,《流量地球》无疑是一个标志。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
在改变中国传统刻板印象方面,《流浪地球》也颇具优势。江晓原认为,国人对科幻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在很长的时间里把科幻想象成一种非常低幼的东西。认为科幻是针对孩童存在的教育读物。因此,导致科幻在中国的社会功能被减弱了,成了低配版的科普读物。这与国际上将科幻作品作为反思科学发展的潮流完全不接轨。
《流浪地球》成为中国科幻元年的标志性事件还有一段机缘巧合。同样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更加被世人所熟知的是《三体》,《三体》的一、二、三部常年位列各大网站的畅销排行榜前十。江晓原透露,《三体》刚开始火爆,但还没有在国际上得奖时,就有人向刘慈购买了电影版权,第一次有人问中国科幻作家购买电影版权,刘慈欣非常激动,一口答应下来。但买下版权之后,《三体》的电影一直没有能够成功开拍。如今只有等合同到期以后,才有可能盼到《三体》电影版的到来。《流浪地球》于是机缘巧合地担起了这份重担。

《流浪地球》电影镜头
想拿奥斯卡的电影无法做到诺贝尔奖的“现实性”
《流浪地球》的上映引发了一系列的关注,在这些关注中,不乏反对之声。舆论场上对它进行攻击的一个主要方面针对的是片中的科学硬伤,其中也包括了很多科学家。江晓原却认为在讨论《流浪地球》的科学硬伤前,应当先对硬伤下一个定义。在一部科幻电影里,何种情节叫做“硬伤”。他认为,如果它直接违背了现有的科学常识,叫做硬伤。但是如果它想象着人类的努力,那么这样的就可以不算,否则怎么叫做科幻作品呢!科幻作品当然意味着幻想,幻想当然意味着眼下还没做到的事情,这不能叫做硬伤。所以我们要强调,有了人类的努力,就可以不算硬伤。
从具体的例子来看,电影《火星救援》里有一个蕴含线索的开头,火星风暴导致了主人公受伤,这就是显而易见的硬伤。因为火星上的大气浓度是地球的0.8%。在那么稀薄的空气里,不可能有电影里所展现的风暴。后来小说的作者也承认,“我知道风暴这个事情是不科学的,可是我一时想不到什么别的灾难,我得让主角有个灾难,所以我就用了风暴。”在同一部片子里,主角在火星种植土豆,由于火星上的日照比地球要弱得多,又缺乏液态水,在那样干燥的环境里,应该不能种植土豆。但是江晓原却不认为这是硬伤。我们可以假想,人类培育了某种特殊的土豆品种,需要很少的日照就能进行光合作用,主人翁也弄了一个小的装置,可以弄出一些水来,我们姑且接受它,这就是人类的努力。所以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承认不是硬伤。
科幻电影,其中包含了科学以及电影娱乐两个部分,而这两个部分又好像奥斯卡和诺贝尔一样似乎水火不容。美国有美国科学院科学与舆论交流协会,这个机构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专门给好莱坞电影找科学问题。因为好莱坞拍电影的人要拿奥斯卡奖,而科学家想拿诺贝尔奖,这是两回事情。江晓原认为,一个想拿奥斯卡奖的人关心的是,怎么让电影好看,而科学家则关心的是可能性、现实性。

电影《火星救援》
科幻的娱乐包括反思,放大人性的黑暗以警醒世人
科幻作品具有娱乐性,但江晓原提出了科幻作品所应具有的两种功能。
第一,科幻作用可以作为科学探索的一部分。作为科学史专家,江晓原说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科幻作为科学探索一部分的明确轨迹。18、19世纪时,国际顶级科学期刊上就发表了大量的在今天看来是科幻的东西。因为当时西方的前沿科学家所思考的就是今天看来非常科幻的事情,比如思考月球上的生物,甚至思考太阳上人类的生存问题。江晓原所著的《新科学史:科幻研究》一书中,他就曾论证过科学与幻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两者的互动如此密切,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两者间的边界几乎可以认为是不存在的。
第二,科幻能够提供一个反思科学的平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被誉为西方反科学主义科幻作品的开始。通常,《我们》《美丽新世界》《1984》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此后反乌托邦电影层出不穷,广为熟知的就有《黑客帝国》《雪国列车》等。江晓原认为,当代科幻中的一个特点是黑暗的未来。科学主义者如刘慈欣,在他的《三体》中,结尾人类文明终结了,这是因为他对人性没有信心。他设置出一种特殊的科幻刑讯室,在那里面对人性进行刑讯逼供。逼供的结果是,他发现人性是黑暗的。
科学技术能放大人性中的黑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性中都是有黑暗的,但是这些黑暗通常在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约束下,每个人都会约束自己,教养、修养,这就是约束我们自己人性中的恶。但是科学技术一旦不恰当地使用以后,这个恶就放出来了。因此,要警醒世人,他们只能弄出一个黑暗的未来,要弄出一个光明的未来,它怎么能警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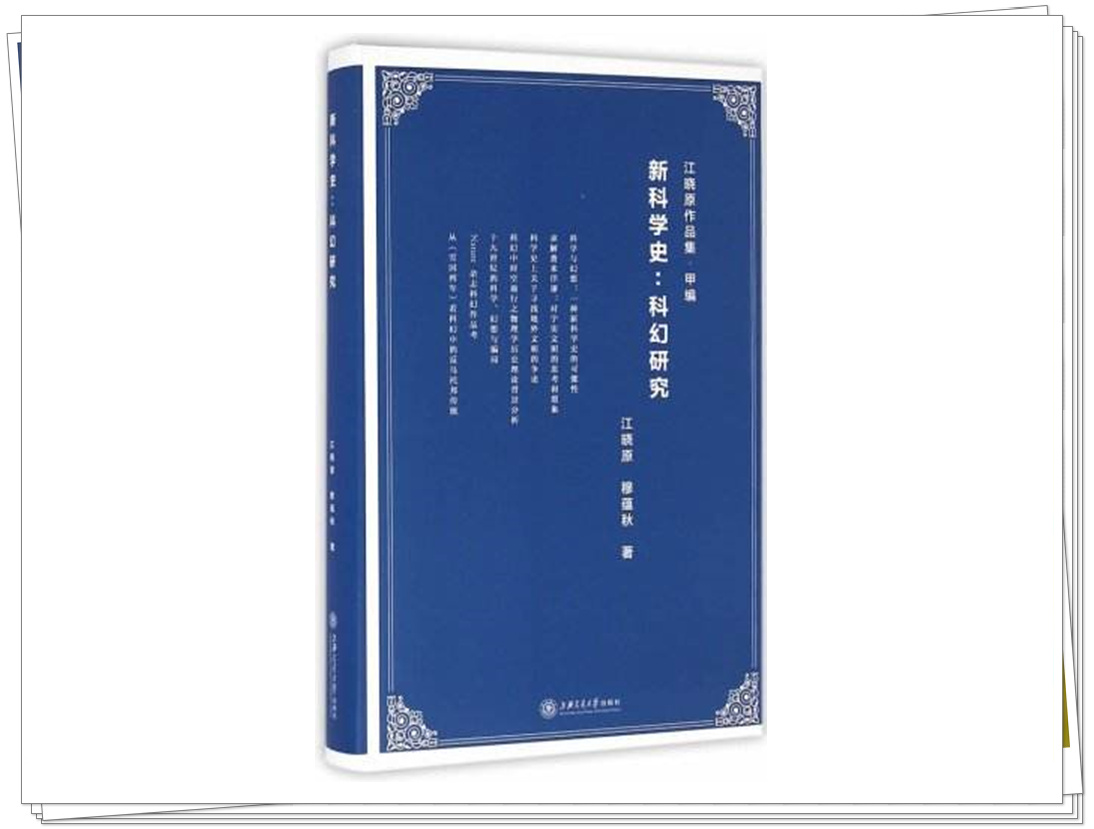
江晓原所著的《新科学史:科幻研究》
科幻作品有三重境界,科幻作家应当追求最高的哲学境界
作为学者,江晓原也经常对科幻界的人鼓吹,科幻作品存在着三重境界。第一重是科学境界,第二重是文学境界,第三重是哲学境界。
第一重境界,它很容易和以前的科普搞在一起,里面就是要讲科学的。在这重境界里,往往推崇硬科幻而轻视软科幻。软和硬的差别在于作品中所包含的科技细节,越多就越硬。所以通常人们推崇硬,鄙视软。实际上软更有思想性,因此没有理由推崇硬或者推崇软,其实这个事情只是技术上的不同。
第二重是文学性。即使在科幻盛行的美国欧洲,情况也是差不多的,文学殿堂是不接受科幻作品的。以前在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那些登科幻作品的杂志,都是通俗杂志,文学殿堂根本不屑一顾。刘慈欣的《三体》,即使在畅销榜上但也没进入文学殿堂。文学家的殿堂是一种高度社会建构的东西,一个小说也许只能卖出几百册,但是它是殿堂里的东西,它是高大上的。这里当然有很多傲慢与偏见。获得文学界的认可是很多科幻作家的期望,但江晓原认为这个境界不值得科幻作家积极追求。
江晓原觉得更应当追求的是第三境界——哲学,即要有思想。在一个用故事形成的虚拟环境里,可以思考平常不思考或者不方便思考的问题,在这样的平台上,才能够思考得更深刻、更深入。那些对技术滥用的担忧,对未来世界悲观的预测,这种东西它本身都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很多作品采用了类似于归谬法、反证法的方法,就是我替你把这个故事想象到极点,让它推到极致,在那样的情境里,你将看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远离科普,告别低端”是江晓原给科幻界的建议
《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元年。“家园不能放弃”是中国科幻电影的一个独有特点,江晓原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世人要开始慢慢习惯“中国英雄拯救世界”的另一个特点。他预言,以后会有更多的中国电影甚至好莱坞电影会安排中国英雄拯救世界。
而从1990年代起,中国科幻作家开始与国际接轨,开始写一些反科学主义的科幻作品。“远离科普,告别低端”是江晓原给科幻界的建议。
现场照片提供:正略书院
作者:童毅影
编辑:袁琭璐
责编:李念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