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靴子的猫2:最后的愿望》(2022)剧照
两位近代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1863-1929)和瑟诺博司( 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在百余年前合作撰著过一部《历史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问世不久便风行一时,很快就有了贝里(George Godfrey Berry)的英译本(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虽然早就时过境迁,但后世学者仍然追崇他们两位为“历史方法的大师”,并称“《导论》一书是有关方法论的手册,是法语著作中最丰富的”(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鲁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亚著,顾航、吕一民、高毅译《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第二章《方法的时代》,商务印书馆2016 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倡导“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近代中国,《历史研究导论》也备受瞩目。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一篇《导言》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史料问题,在篇末所附《参考书举要》中提到,“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看C.V. Langlois and Seignobos’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已经借鉴过此书的英译本。数年之后,留学法国、亲炙瑟诺博司的李思纯,依照法文原本并参酌英译本翻译而成的《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更是得到众多新旧史家的青睐。刘咸炘《治史绪论》(尚友书塾1928年)阐说“史学可分四端”,首先标举“考证事实”一项,就指出“前哲言之已详,近译法人朗格罗、瑟诺波所撰《史学原论》,亦详密可参”。洪业在讲授“初级历史方法”时,明确规定“选习者并应细阅朗格诺瓦及瑟诺博司合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历史学系》,1935年)。杨宽所编《历史教学法纲目讲义》(收入《杨宽史学讲义六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在各章所附参考书中也多次列入“李思纯译:《史学原论》”。王绳祖《评李思纯译〈史学原论〉》(载1941年金陵大学文学院主编《斯文》第二卷第二、第四期)尽管指出译本中的若干疏漏,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大学历史系开设“西洋史学方法”课程,“不以此书为课本,即以之作参考教材”。凡此种种,均足以说明此书在当年受欢迎的程度之深。
在正式付梓之前,李思纯曾删订润色译稿,“间于篇中征引事实有不能明者,为附注于章后焉”(《译者弁言》),设身处地为书中列举的不少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等加以诠解,以方便中国读者阅读。然而稍事覆按推敲,其中也难免偶有疏失。在该书中篇《分析工作》的第二部《内容鉴定》第七章《忠实与精确之反面鉴定》里,两位作者详细讨论了鉴别史料时所遭遇的各种复杂情况,其中包括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荒诞传说与琐闻逸事”的问题。他们认为其研究方法有“粗浅”与“精细”之别,其中“粗浅之分析行为,乃将一种荒诞传说之记载,凡其中详细之似为怪异矛盾,或不合理不可能者,皆屏弃之,而保留其余合理部分之俨然有关于历史者”。为了更好地演示具体实施的方法,他们随即举证道,“例如斥弃彼所谓着靴之猫,而承认彼所谓Carabas侯爵,以为具有历史性”。可惜点到即止,并无任何申说。李思纯在附注里就此补充说:“本章所举着靴之猫,原出小说。法国十七世纪小说家Perrault氏(一六二八—一七零三)曾为一小说,纪Carabas侯爵广蓄多猫,猫能着靴,侯爵以猫技致富云。”这番简介就有些似是而非,很容易误导读者。
“着靴之猫”的故事在欧洲各地流传极其广泛,近代以来,德国语言学家格林兄弟(Brüder Grimm)编纂的《儿童与家庭故事集》初版、英国民俗学家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蒐集的《朗格童话》,都相继收录过这个故事,而最脍炙人口的毫无疑问当首推法国作家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在撰著《鹅妈妈的故事》时所整理改编的版本。故事略述猫为了帮助出身寒微的主人而刻意攀附国王,并谎称自家主人为侯爵以博得对方的好感,在其出谋划策之下,主人最终得以与公主结为夫妇。两位法国史学家在论述时信手拈来,无非是要强调穿着靴子能说人话的猫虽然子虚乌有,可是故事中出现的国王、公主、侯爵等贵族阶层在历史上却真实地存在过,经过删汰别择,仍能为历史研究所用。这则童话在法国家喻户晓,法语读者一看便心领神会,行文之际自然毋庸饶舌赘述,却在无意间给汉语译者制造了些许障碍。所谓“Carabas侯爵”原本是猫信口开河编造的头衔,译者却想当然地信以为真;童话里明明只有一头猫,译者又误以为“广蓄多猫”;至于“以猫技致富”云云,也有些含糊其辞而语焉不详。所以附注里虽已指出“着靴之猫”源自佩罗的小说,但李思纯本人大概并没有认真读过原作,只是道听途说或望文生义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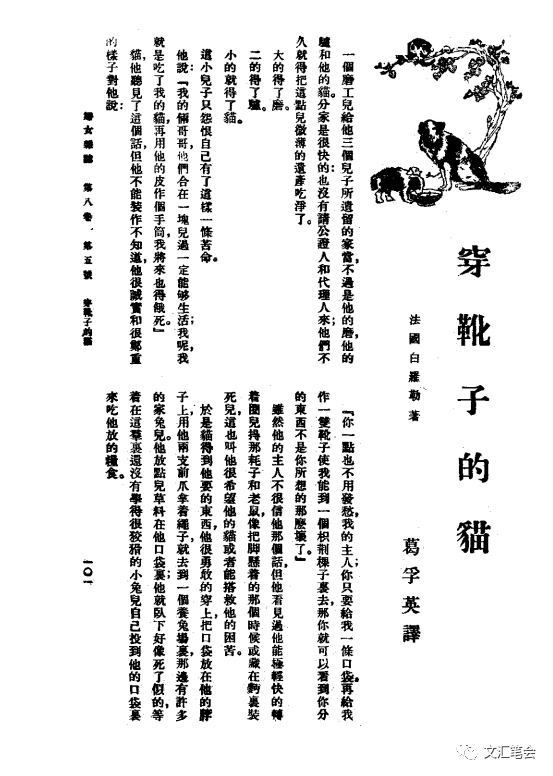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童话”观念的传播,这则故事实际上很早就引起不少中国译者的浓厚兴趣,先后出现过黄洁如译《穿靴子的猫》(收入黄氏编译《童话集》第一辑,群益书社1921年)、葛孚英译《穿靴子的猫》(载《妇女杂志》1922年第八卷第五期)、唐小圃译《穿着靴子的猫》(收入唐氏编纂《家庭童话》第一集第九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童心园译《靴中猫》(收入童氏编译《良晨童话》,良晨好友社1924年)、永如译《着靴的猫儿》(载1925年《少年》第15卷第6期)、戴望舒译《穿靴的猫》(收入戴氏译《鹅妈妈的故事》,开明书店1928年)、韦丛芜译《着靴猫》(收入韦氏译《睡美人》,北新书局1929年)、许达年等译《穿鞋子的小猫》(收入许氏译《法国童话集》,中华书局1933年)等,各家译本风格各异,细节也偶有出入,不过稍加比勘,可知大抵都本于佩罗版童话。

戴望舒译《穿靴的猫》
与此同时,西方学界围绕这则童话所做的研究,也陆续被引介给中国读者。赵景深翻译了英国学者麦苟劳克(John A. Macculloch)所著《童话学》(连载于《文艺创作讲座》第一卷至第四卷,光华书局1931至1933年),第一章就题为“友谊的兽:穿靴子的猫”,研讨了同类型故事在世界各地的分布状况和递嬗过程。杨成志与钟敬文合作翻译了另一位英国学者雅科布斯(Joseph Jacobs)所撰《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将复杂多变的民间故事化约归并为七十种类型,其中就包含着“靴中小猫式(Pussy in Boots Type)”,还概括总结了这一类型故事所共有的基本情节。
在学习揣摩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余,中国学者对这个故事也有关注讨论。姑以赵景深为例,他编著的《童话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系统介绍了各种理论及相关成果,在第三章第一节《万物精灵论》里提到,“所谓‘万物精灵论’(Animism)的意思,就是说,在初民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有灵魂的,它们一样的也会说话,并且还与人类做朋友”,“童话中如《穿靴子的猫》《小红帽》《无猫国》等,都是以动物来做主人公”,以此来探讨图腾信仰与童话创作之间的密切关联。在《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载1928年《民俗》第廿一、廿二期合刊)里,赵景深又特意补充说,“靴中小猫式(第六一式)以培罗脱(Perrault)的记载为最有名”,可见他对这个童话印象相当深刻。
有了这么多相关的翻译和研讨,不难窥知近代以来国人对“着靴之猫”的故事实际上并不陌生。当然,李思纯在译注中出现如此疏漏也情有可原,不必求全责备。据其《译者弁言》自述,他在1920年秋入法国巴黎大学追随瑟诺博司研习历史,“吾自是年秋迄于一九二一年冬,凡阅时一年,朝夕挟书册亲受先生讲课”,在此期间全神贯注而心无旁骛,想来无暇顾及诸如佩罗童话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而他决心着手翻译此书,则始于“一九二二年三月,游柏林,居康德街,日长多暇”之际,上述绝大部分汉语译本及论著此时都尚未问世,自然也无法通过母语了解到相关情况;而整个翻译“日成数章,二月而毕业”,在文无加点、一气呵成的同时,势必也来不及做个别细节的斟酌完善。但这个并不起眼的讹误,倒恰好印证了古人所强调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论语·子张》),更让人不由联想到《史学原论》开卷便郑重警示初学者的一段话:“虽以精确方法,从事史料之校雠考证,结果将全无价值。特以作者于某种史料偶未寓目,致无从据以疏解修补及订正其引用之例证耳。”(上编《初基智识》第一章《搜索史料》)看似危言耸听,仔细寻绎回味,还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作者:杨 焄
编辑:吴东昆
责任编辑:舒 明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