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某次电视“诗词大会”上,关于李白和杜甫,一位专家嘉宾说:“在同一个时代,两位伟大的诗人往往都是互为对方的铁粉!”(大意)我颇以为然,李杜一为诗仙,一为诗圣,两人“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互相欣赏,亲如兄弟,在这里就毋庸赘言了。
我想说的是德国的歌德和席勒。他们两人也可说是德国文坛的“二圣”,1794年两人订交,掀开了德国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古典文学的一页。

歌德(左)和席勒
席勒的成名作是剧本《强盗》,扉页上写着“打倒暴君”的字样。首演于曼海姆剧院,反响极其强烈,剧院变成了“疯人院”,席勒的名字一下子传遍德国和整个欧洲。席勒对歌德仰慕良深,但歌德总是众星捧月般被人簇拥着,致使席勒无法与其单独交谈。歌德是公国大臣,生活优裕;席勒虽有名气,却是负债累累。两人在气质上,哲学观点上,甚至在生活习惯上都大异其趣。席勒曾向友人寇尔纳抱怨命运之不公:“……我常想起命运对我是多么残酷,而他的命运是多么轻而易举地将他的天才托起;可我要达到这一天还不得不进行艰苦的奋斗!”正因为如此,两人虽然曾经同在魏玛小城,“低头不见抬头见”,可彼此不相往来。
歌德对席勒一直保持距离,直至1794年夏天才登门拜访席勒。席勒紧接着就写信给歌德,让后者真正意识到:“席勒是以其整个的生命存在伸出友谊之手。”席勒向寇尔纳报告说,“歌德终于向我表示信任”,两人的思想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一致。有趣的是,“这种一致来自观点的巨大不同”,“他现在感到一种和我联结在一起的需要。迄今为止,他是独自一人行进,没有得到任何的鼓励,而今他要和我联袂前行。”
歌德请席勒进驻他在魏玛的弗劳恩普兰深宅大院的三个房间,两人结合成一个紧密的工作团队,以巨大的热情和独有的创新精神展开了工作。在此期间,席勒完成了伟大剧作《华伦斯坦》《玛丽亚·斯图亚特》《奥尔良的姑娘》。歌德重又写起他的长篇《威廉·麦斯特》;完成了长篇叙事诗《海尔曼·多罗蒂娅》,《浮士德》的写作也有了很大的进展。1797年,两人都写了许多的叙事谣曲。歌德的名篇有《科林斯的新娘》《魔术师的弟子》《掘宝者》《神和舞女》等;席勒则有《手套》《潜水者》《伊比库斯之鹤》《斗龙纪》等。这一年被称为叙事谣曲年。两人还通力合作撰写了不少讽刺短诗,鞭挞德国落后鄙陋的状态;他们还探讨艺术在一个由法国大革命完全改变了的世界里所扮演的角色。歌德为此写下了《文学的平民主义》,席勒则以《论素朴和感伤的诗》相媲美。
直到1799年席勒迁往魏玛为止,这两位朋友的通信多达一千多封,相互在对方家作客长达60个礼拜。
歌德在将魏玛的家安排就绪之后,便把工作地点移往耶那,为的是离席勒更近一些,便于相互切磋。他在耶那城堡中找到了一个非常安静的住处,“在这里比我在地球上任何地方更富有创造性。”
席勒写道:
歌德每天下午四点来,吃过晚饭才回去。平时都是悄悄地进来,坐下来,用手支着头,拿起一本书看,或拿起铅笔画起来。有一次我那野孩子手执鞭子不小心打到了歌德的脸上,这一下子打破了那寂静的场面:歌德猛地跳了起来……有时歌德忽然没来由地激动起来;通常两人就会展开有趣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深夜。
席勒高度评价歌德的《罗马哀歌》的艺术性,但将其中露骨的性爱描写删除了,以免过于违背当时的礼俗。《罗马哀歌》发表在席勒所主编的《时序》杂志上。哀歌虽经删改,在魏玛还是遭到了非议,甚至传为歌德的“丑闻”,而耶那的浪漫派对它却是一片欢呼和赞扬。
歌德和席勒还想将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情谊延续到下一代。当歌德的妻子克里斯典娜身怀第四胎时,歌德多么希望她生个女儿啊!他写信给席勒:“小小儿媳妇还一直没来”,意指生了女儿就要给席勒两岁的儿子卡尔做媳妇。
1805年5月9日,席勒与世长辞。他的遗体被几个年轻的学者抬往墓地,在雅可比教堂举行了安葬仪式,并奏起莫扎特的《安魂曲》。而歌德的家人都不敢告诉他这一噩耗。席勒之死给歌德的生命烙下了一条深深的伤痕:“我曾想到我自己会死,而今我失去了一个朋友,同时也失去了我存在的一半。”在这里,席勒的地位甚至超越了歌德最终也是明媒正娶的妻子克里斯典娜。歌德失去了他的朋友、他的合作伙伴和谈话对手,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攫住,这也使他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歌德对其精神伙伴的思念成了一种煎熬。他很想找人谈谈文学,克里斯典娜显然难以担当此任。多年与席勒的合作之谊使他养成了“成双”的思维习惯:和席勒一起探讨创作和学术乃是歌德的内在需求,克里斯典娜对他只是属于家庭的范围,是“家庭的宝贝”。
其实,“文化粉丝”现象还可以穿越时空,运行于古今中外——冯至和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就是这样一对。

里尔克(左)和冯至
冯至学贯中西,头上有各种桂冠。但他最为珍视的乃是诗人的称号,鲁迅先生曾称他为“最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诗,在八十年代被顾彬(Wolfang Kubin)译介给德语世界,引起了轰动。198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他“格林兄弟文学奖”。1987年,他又获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际交流中心艺术奖和代表联邦德国最高荣誉的“大十字勋章”。
冯至青年时代喜爱德国浪漫主义,他曾在给笔者通信中写道:“Undiene(《水妖》,笔者注,下同),der blonder Eckert(《金发艾克贝尔特》),Michael Kohlhaas(《米歇尔·科尔哈斯》……都是我青年时期喜欢阅读的作品,不管其中的世界是现实或是奇幻,都曾经使我神往。”(见2010年6月14日《文汇报·笔会》)冯先生那个时代的青年总为苦闷所笼罩,找不到出路,看不清前途,他性格内向,多愁善感,情钟于浪漫主义,可说是顺理成章。然而随着岁月的增长,他慢慢认识到,“浪漫派的东西,太惹人爱了,但它总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东西。”(《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24页)他似乎一直在寻寻觅觅,他深知德意志文化的博大和复杂,面对德语文学,他的选择很是慎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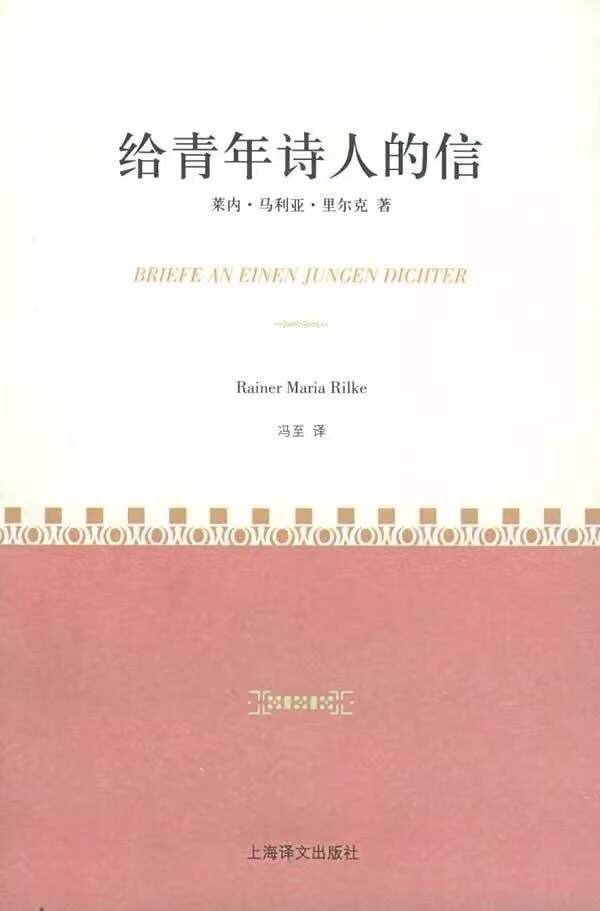
奥地利诗人赖伊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出生于布拉格,他是现代派诗歌的奠基者之一,是海涅之后最具世界声望的德语诗人。他也像海涅一样,在富有叔父的资助下读完了大学。他的诗歌色彩绚丽,音调铿锵,传达出一个忧郁的主观世界,苍凉的内在的自我。
1930年9月冯至留德到了海德堡,里尔克和歌德便占据了他的闲暇时间。没过多久,他便“完全沉在Rainer Maria Rilkede世界中”:“上午是他,下午是他,遇见一两个德国学生谈的也是他。我希望能以在五月中旬使你收到一点东西(这是我现在把别的书都丢开,专心一意从事着的),使你知道里尔克是怎样一个可爱的诗人!他的诗真是人间精品——没有一行一字是随便写出的。我在他的著作面前本应惭愧,但他是那样可爱,他使我增了许多勇气。恐怕自歌德同荷尔德林后,德语诗人只属他了,自然还有Stefan George……”(《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167页)冯至初到,满脑子就是里尔克,他犹豫了数十天,花了四十马克买来了里尔克的全集,打算“永久”地读下去。
他的作品与冯至对诗的梦想不谋而合:“作一首诗,像是雕刻家雕塑一座石像,想不到来到德国遇见里尔克的诗。他后半的诗多半是一座座的雕刻。——我简直为了它而颠倒了。”(同上,第168页)
意想不到的是,诗人冯至和诗人里尔克在上海“重逢”了:今年夏天,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浙江文艺出版社等共同举办了“里尔克诗歌配乐朗诵会”。先是朗诵里尔克的原诗,继而朗诵中文译诗,自始至终有音乐伴随,不期然有种庄严、肃穆、神秘、神圣的气氛。在这里,冯至是作为译者出现的,人们传颂着他译的《豹》《秋日》《Pieta》(《圣母玛丽亚怀抱耶稣尸身之景象》)。冯至认为,里尔克的表现方法都是别出心裁,和歌德以降的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但他强调,“读懂了一首,便得到一首的好处。”
冯至说,读了里尔克的作品,使他看植物“不亢不卑,忍受风雪,享受日光,春天开它的花,秋天结它的果,本固枝荣,既无所夸张,也无所愧恧……那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同上,169页)。这里说的固然是另一个物种,但又何尝不是对另一个人、另一种文明的深刻的理解与同情呢?
作者:袁志英
编辑:谢 娟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