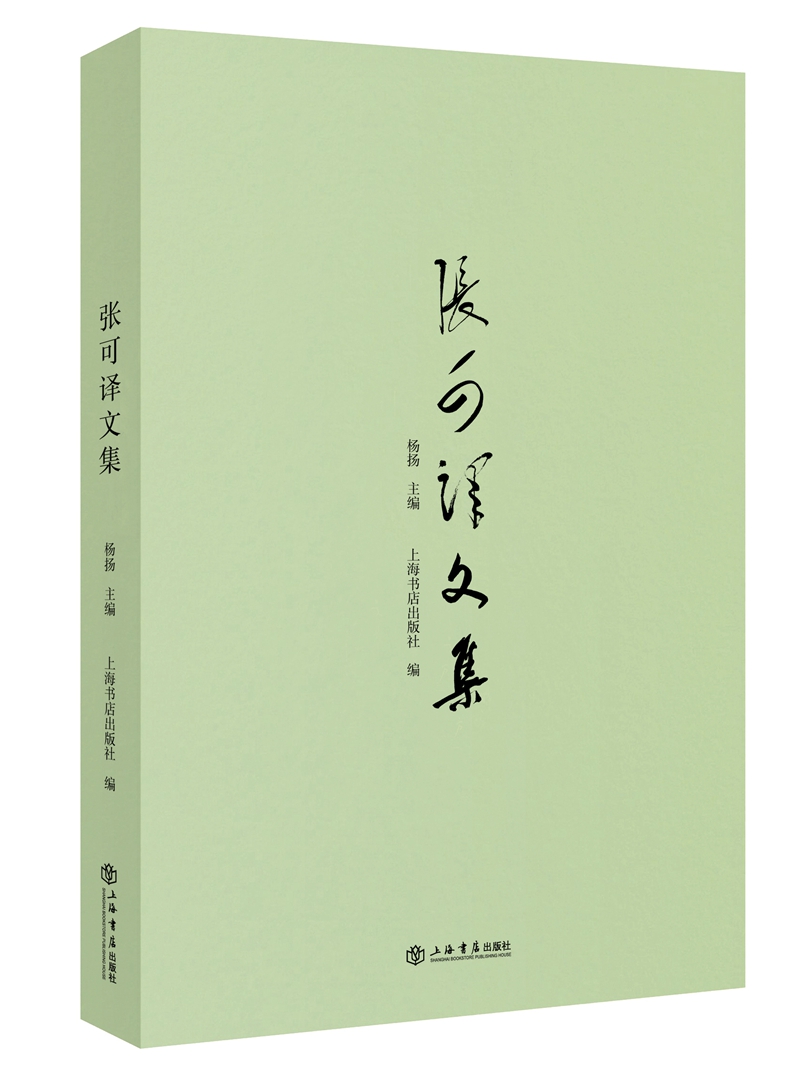
我从没想过,会为张可先生的文集作序。因为要为张可和王元化先生做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作为分管责任人,我无法推卸。事实上,我到上海戏剧学院工作后,张可先生的相关材料一直是我留意关注的,可惜,能够找到的文字太少了。我向相关的老教师了解,获得的信息也是寥寥无几,大同小异。估计张可先生当年在上戏是很低调的。遗憾之余,我只能凭自己的印象,谈谈对张可先生的认识。

1992年张可与王元化游杭州九溪十八涧
张可的名字是与王元化先生连在一起的。我第一次见她,是1984年下半年,因华东师大学生社团的事找王元化先生,那时我大学四年级。他们住在淮海路高安路附近的宣传部宿舍,她为我开门,问明情况后,对里面的王元化先生说,有人找你。印象中的张可先生,声音很轻,态度和蔼,动作缓慢,是一位慈祥雅洁的老人。1990年代后,我去王先生家多一些,每次去,总见她笑眯眯地站在一边,静静地听大家聊天,有时也会插上几句。遇到下午去,她会招待大家吃午茶和点心。记得有一次她招待大家吃饭,有烤鸭、大葱和大蒜之类东西。王先生兴致勃勃对大家说,生大蒜好。他一餐下来,吃了好几粒生大蒜。张可先生劝我们多吃一点烤鸭和别的菜。那是我印象中王先生、张可最开心的时刻,那种主宾之间谈笑风生、和谐相处的氛围感染着在座的每一位。后来,王先生住进衡山宾馆,张可也住进医院。再后来就是传来张可病逝的消息。我去看望王先生,但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好。听说葬礼是在国际礼拜堂做的,因为她信教。我曾听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多次谈起张可,称赞她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对于身处逆境中的王元化先生不弃不离、始终相伴。

张可王元化在寓所
王元化先生谈张可的文字不多,收入他《思辨录》第374中,有他为余秋雨先生《长者》中涉及张可而写的一段文字。这是在余秋雨原稿基础上的修改。他最初的修改是:
张可心中似乎从来没有仇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疾言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一个重字眼说话,总是那样善良、柔和,待人总是那样宽厚。几十年来,我的坎坷生活给她带来无穷伤害,而她从未流露出丝毫的不满与抱怨。知识分子是很敏感的,只要一个眼神稍有表露,就能立刻感到,但在她的眼睛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眼色。
王先生最后改定的文字是:
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疾言厉色的态度待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三十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受过屈辱后会变得敏感,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和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善良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1947年,张可与王元化结婚前偕两家家长兄妹等摄于沪江大学
上面这些文字可以看出王先生对张可为人处世的一种长时期的观察和真切细腻的体会。而对于张可先生作为知识女性和大学教师学识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我们可以从王元化先生的《莎剧解读》的序跋中体会到。王先生说,“我倾心于莎剧,主要是受到张可的启发。”因为张可有过良好而全面的戏剧文学教育。她大学时代的老师中,有像孙大雨、李健吾那样的莎剧翻译家和戏剧评论家,张可自己的英文水平相当高,18岁时,就翻译了奥尼尔的《早点前》。她还是暨南大学学生剧艺社的台柱,有过舞台表演的体验。所以,她对于莎士比亚戏剧的爱好与认同,有来自文学审美方面的,也有舞台表演方面的。张可还受到她哥哥满涛的影响。满涛是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文艺聚会和沙龙活动,他家还曾一度是进步文艺青年聚会的场所。1930年代,国难当头,社会问题剧和街头剧因直接关切到社会现实问题而深受推崇,张可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活动,对于很多党组织推动的负有实际政治斗争使命的戏剧形式,并不陌生的。但她的教育和成长背景,让她对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西方戏剧毫不排斥。她不仅不排斥,而且能够真正体会到其中的艺术妙处,享乐其中,丝毫不受到外界政治因素的影响。当与思想激进的王元化先生发生意见分歧时,她也不争执,“只是微笑着摇着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事实证明,张可对于莎剧的理解和判断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随着岁月推移,包括王元化先生本人在内,逐渐体会到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刻性和在人物塑造上的独特价值,不仅爱上了莎剧,还由衷地赞叹莎剧的永久魅力。此后,在他们人生的最困难时期以及人生的最后岁月,莎士比亚戏剧始终是他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张可婚纱照
张可先生性格随和,不做刻意为之、让人勉为其难的事。她与王元化先生是1948年结婚的,此后,有一段时间她过着家居生活,完全沉浸在家庭的幸福之中,没有出去工作,甚至连原来热衷于参加的政治活动也疏淡了。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后,在姜椿芳、夏衍等人的劝说和鼓励下,她才走出家庭,到新成立不久的上海戏剧学院任职,在表演系担任形体训练课的教师。但形体训练等基础课,对教师的体力要求比较高,张可身体羸弱,最终不得不离开表演系,到戏文系担任莎士比亚戏剧教学。十年动乱,张可、王元化一家的处境可以想见,那种受侮辱受损害的屈辱生活,给他们的晚年生活留下了深深的伤痛。“文革”结束后,张可先生病体缠身,已经无法再上讲台,最后,是在上戏《戏剧艺术》编辑部退休的。我阅读过张可先生1950、1960年代的相关材料和她在粉碎“四人帮”后向有关部门提交的申诉材料。读罢这些东西,或许不相关的人会为这样一位品质高雅的知识女性的坎坷人生感到惋惜,好像没有做到物尽其美,一个好端端的大学教师,一生之中,没有几个时间段为她提供发挥才能的舞台。对于我而言,尽管对张可先生了解不多,但仅有的一些接触中,还是让我感觉到她的那种艺术修养和善良品质,这不是靠后天学来的,而是自然天成。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与世争,她有她自己的是非观和爱憎情感,她只想做自己喜欢做,也愿意做的事。但这样的人,一生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巨大的磨难中度过的。

张可为王元化抄写译作《文学风格论》
张可先生要一百岁了,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将为她和王元化先生组织纪念活动,邀请他们生前的朋友、学生,认识和不认识的,相聚一堂,感怀前人,共同追忆那逝去的美好时光。我想,此刻如果张可、王元化先生天上有知,一定会高兴的。
2019年12月于上戏仲彝楼
本文为上海书店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张可译文集》序
作者:杨 扬
编辑:谢 娟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