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在世文坛就有这一说,去世后仍不时有人有文章这么说。国人好说“最后”和“第一”,譬如林徽因,奉她为“民国第一才女”。第一者如何排定出来的?排得出来吗?实在不敢轻信。可也无须较真,姑妄说,姑妄听。
汪曾祺开始文学创作,除了剧本,什么都写,小说,散文,诗歌。年轻时他喜欢读翻译小说,尤其心仪阿索林,写得很洋很现代,每一种体裁无不洋得可以。当初未涉足剧本的汪曾祺料想不到,他人生旅程最后一站落在了剧团,最具知名度的作品是经他手打磨的《沙家浜》,民族得不能再民族了。
年前读一位博士文章,他解读汪曾祺小说《金冬心》,意欲翻案,推倒汪乃中国“士大夫”的流行说法。博士认为,金冬心这个“士大夫”“是被揶揄和讽刺的对象”,“是有批判的”。文章没有论及汪的其他作品,单以《金冬心》一票否决了创作整体倾向。这也不大叫人信服,“士大夫”偶尔也会反省一下自我,批判批判自己,反省士大夫弱点的人未必就不是士大夫。我倒也不大赞同往汪曾祺身上贴“士大夫”标签,但并非因为《金冬心》。我心目中的士大夫,和他们说汪曾祺的,不是一个样子。充溢汪氏身上和作品中的,该是书卷气,书生气,文人气,比较平民,还够不上士大夫。
是“士大夫”,或不是,于汪曾祺作品分量毫不增减。爱说汪曾祺是“士大夫”的人,要么自身有点儿“士大夫”习气,要么向往这习气。这样的习气往往和人性融而为一。“文革”年代,扼杀人性殆尽,人性式微久远。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复出,《受戒》名噪一时,缘由之一正是作品里这久违的人性气息苏醒了人心,引发了读者对传统精神的眷恋或憧憬。
能否以“士大夫”一言以蔽汪曾祺(我们又常常一言蔽之),能否排定他属于最后一个,且不管它。我想说,由汪氏作品诚然容易联想到所谓的“士大夫”气,但汪曾祺小说写得多写得更好的,恰是并非“士大夫”的三教九流。打鱼的,吹号的,做媒的,把和尚当职业的,芸芸众生,一个个鲜活,传神,且又不着痕迹地寄寓了作者感慨。创作此类平民题材小说,汪曾祺不同于那些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的小说家,不像他们与笔下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汪曾祺或褒或贬,俱是旁观者小知识分子目光。并且与纯粹的旁观不同,他写他们,同时显示了自己,笔调,性情,志趣,皆烙下小知识分子印痕。他熟悉、同情,以至赞赏他们所言所行,这难免浸染一点市民的观念意识。市民意识与“士大夫”观念看似两端,哪里就冰炭不容。到汪氏笔下,两者汇结成人性人情的崇尚。“士大夫”自觉地追求人性,市民本能地体现人性。汪曾祺的小说,蔑视礼法,忽略伦理,个别篇章还有出格之嫌,不在乎传统道德的底线。
我特别喜欢汪氏文字,无论小说、散文,以及关于文学的非文学的随笔,哪怕是评论,行文都别具魅力。琐琐碎碎的细枝末节,汪写得有滋有味,而且,见性情,见氛围,见意蕴。不论叙述还是议论,十分口语,苏北读者尤能读出浓浓的乡音。尽管是口语,绝不粗俗,俗里藏雅,经过了难以察觉的提炼。单看一词一句,仿佛十分寻常。词词句句连起来,意味,张力,魔幻般光彩四射。他平实而绚烂的文字,很上乘的。置诸多名家中,汪氏烙印鲜明。单就文字而论,汪曾祺可谓后来居上,比他恩师沈从文实有过之。汪曾祺是独特的,甚至空前。百年来没有一位名家与之相似。相近的沈从文、废名,与这位后起之秀亦明显有别。“五四”新文学以来语言风貌,要么鲁迅,要么赵树理,或者巴金、茅盾,汪曾祺别开生面,不无新开一路的意义。

汪曾祺和沈从文
古人常言才高八斗,担当得起的作家不多,汪曾祺可以。他写小说,开头颇费斟酌,腹稿想好了则一挥而就。他的多数小说,貌似散漫,实在散得精致。刻意求精,不露痕迹。他很唯美,如他这般自觉的唯美,尤其体现于意境、文字的自觉,亦不多。甚至个别大作家的个别垂史名著,文字方面竟也顾不过来。汪曾祺是入了文学史的,而且丰富了我们的文学史。
丰富了文学史的汪曾祺自有其短板。他的小说多真人真事作底,往往虚构成分不及素材。他不大有耐心发挥小说家的想象力,不写篇幅长的小说。连中篇小说也不写,不必说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尤需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组织必要的复杂、跌宕的情节,他似力所不逮。虽健清谈,却不会说书。他小说的散文化颇得赞誉,而得与失均在散文化上。偏嗜归有光的汪曾祺欠缺大气,成不了韩、柳、苏东坡。有人捧汪曾祺为大师、巨匠,事实上他距此尚有距离。汪曾祺是十足的才子,而仅凭才气成不了大师、巨匠。这由气质所定,他不具广博胸怀、阔大气象,称得重磅作品的不多,不少小说纵然精致,隽永,绝句而已。只凭绝句,充其量王昌龄、孟浩然。李白、杜甫若仅有“床前明月光”、“迟日江山丽”,若无“蜀道难”、“三吏”、“三别”,决不是现在文学史上的李杜。即使绝句,李白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杜甫有“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般气势的短章汪曾祺没有。说到当代小说,沈从文在《边城》之外有《长河》。话再说回来,写高邮城乡题材的几十个短篇,合起来读,不妨当做长篇小说来感受。各篇之间有人物关联,事件关联,更是共处同一自然环境、时代背景,可组合为一幅长卷高邮“上河图”。话又要说过去,它到底并非一体构思的鸿篇巨制,不可能有长篇小说体裁独具的魅力。
毋庸讳言,汪曾祺某些篇章过于随意,特别是后期的作品,放纵散文化,似乎忘了是在写小说。譬如《小学同学》题目下的几篇,其中《王居》一篇更其突出。它们归为小说,委实勉强了一些。纯属一篇一篇素描,几同素材实录。毕竟,小说是小说,散文是散文。而他的小说《薛大娘》和《一辈古人》那两组散文里的《薛大娘》,同题,同内容,不同体裁,对照来读,即相形见“异”。散文《薛大娘》全是本色纪事;小说《薛大娘》则有了素材提炼、细节虚拟,有了典型化,添了小说技法,是篇成功的散文化小说。
再是,颇为别致的表述,形成了套路。开篇第一句往往是:“李三是地保,又是更夫。”(《故里杂记》)“詹大胖子是五小的斋夫。”(《桥边小说三篇》)“小姨娘章叔芳是我的继母的异母妹妹。”(《小姨娘》)“皮凤三是清代《清风闸》里的人物。”(《皮凤三楦房子》)印象里这么开头的不下十几二十篇。这么表述,朴实、简短,反而鲜明,更与全篇格调吻合。还譬如,他喜欢这么写:“银匠店出租花轿,不知是一个什么道理。”另外一篇写:“城里人叫他小货郎,也叫他小陈。有些人叫他小陈三,则不知是什么道理。”碰见这“不知”不止十篇八篇。全知的小说作者,故意说到他不知什么,挺别致。陈仓暗度,增添了真实感。然而,再好的开头,再怎么别致的描述,一而再,再而三,一次鲜亮,二次还可以,第三次就勉强了,再多,魅力会所剩无几。特别是连着读上几篇,这个瑕疵愈发碍眼。这又是他与巨匠差距之处。
汪氏读者将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汪氏也必影响后人小说创作,这影响虽为细流,却可能绵远。迷恋汪曾祺的后辈,好几位死力模仿他的小说,近乎重排样板戏。几乎没有一位全像的,当然是没有全像的本事。有本事也不必全像,学得再好,形似而已,不备汪曾祺的阅历、品性、学养、识见,哪得神似。应该如汪曾祺师从沈从文,汪氏才是得了恩师精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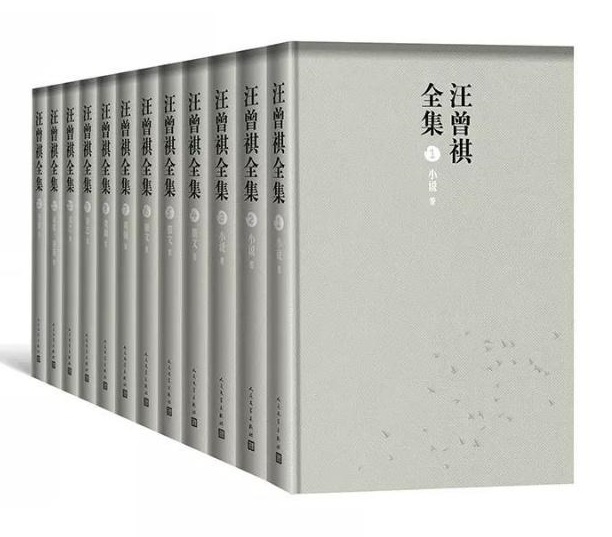
汪曾祺走了许多年,许多年来,报刊时时谈到他,出版社不断印他的书。新近问世的十二卷全集,据说出得很是精致。汪曾祺,汪曾祺的书,今后会被继续谈继续印。赞美汪曾祺的文章很多很多,笔者以“汪粉”一员,静下来思忖思忖,说些闲话,也算姑妄言之。
作者:陈老萌
编辑:吴东昆
责任编辑:舒明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