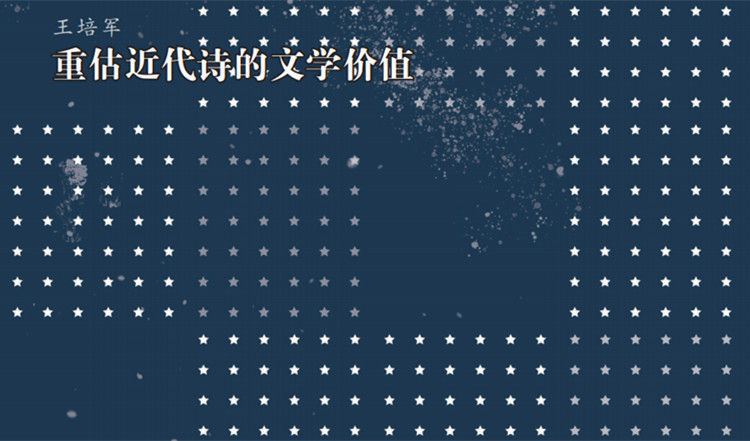
【导读】近代诗并非新文学之先导,而是中国三千年古诗之结局,且为一光辉的结局,为中国诗的“龙尾”。其价值不仅是文献的,思想史的,而是文学本身的。有见识的学者,是甚至以为超过宋诗的。
近代诗的研究,最近十许年已大被关注,虽是如此,也还存在不少误会,或者说是某种疑惑。如有些人如是问:“近代诗到底有什么好”;“其诗艺的价值何在”;“近代诗比唐诗好吗”;“有了唐诗宋词,我们还要读近代诗吗”?诸如此类,在研究者那里,也是不难碰见的。问者的意思,无非是近代诗在诗学上的价值是不大的,他们认为,近代诗的主要价值,在于史而不在于文,质言之,即近代诗之价值不是文学的,而是史料的。即使是近代诗的第一大家陈三立,亦难免此种对待。
如此的大判断,毫无疑问的,是为晚近的主流意见裹挟所致。我们知道,在民国时期,胡适是倡研《红楼梦》的,但他于 《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之估价,却非常之低,他屡言《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只算得二三流,不仅于此,在中国古小说中,也不及《海上花列传》、《儒林外史》,甚至比不上《老残游纪》(见《与高阳、苏雪林书》)。就是专力于 《红楼梦》的俞平伯,也不好多少(见《红楼梦辨》中卷;如云:“《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这在今天看来,皆颇为荒谬。其所以有此,无他,乃是在彼时诸君接受了西洋文学的标准,尤其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准的影响,而移之于中国文学的批评,且于中国文学又不能自信,遂尔削足适履,发此谬说。另如我国的书法,自为一古雅艺术品,此在今日,固已无待赘说,但在民国的学者,据其所读西方之书,亦怀疑其不能与于艺术之列(如郑振铎、傅斯年等,皆是。不知其见内藤湖南说西洋人看懂中国画要三百年的时间,毕加索说绘事西方应以中国为老师,又当作何想)。凡此谬妄,皆足令人发噱者也。
在钱锺书《围城》中,有一节写到方鸿渐往苏家拜访文纨,而邂逅了写旧诗的董斜川。文纨出于好奇,请教斜川,问近代诗数谁最好,因为她对于近代诗人,根本是无知的。斜川当场嘲笑,说留学生看的近人诗,无非两家:一为苏曼殊,一为黄遵宪。并说:“东洋留学生捧苏,西洋留学生捧黄”, “还是黄好些,苏诗里的日本味儿,浓得就像日本女人头发上的油气”。此语当然是调侃时人的。其实,董斜川的一番话,拿来说近七十年的情况,也并无不可。据此,一般人对于近代诗的认识,其浅薄为如何,也就可以想见了。
其所以有此情形,原因固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主要缘故,不可不一说。那就是:一、时间过近;二、新文学的兴起。因为时间过近,在作判断时,就引致了如是干扰:一是古来所说的 “贵远贱近”心理,因为这,而倾向于贬低近人;二为时间过近,则我们身犹在其中,所取的坐标系,亦必欠准确,不能脱身于外,如苏轼诗所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确然的。不能“出”,所以不能“识其真”。今日距晚清才不过百年,对于近代诗的性质,一般不能正确认识,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即新文学的兴起,它所生的负影响,尤为巨大。在新文学兴起时,其代表人物力图打倒 “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并以之为职志的。近代诗自也在被攻击之列。胡适在《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中,就有对近代宋诗派的严厉批评,后来陈子展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持说也相一致。此外在那时也还有王国维所倡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其说见《宋元戏曲史》自序。其实王氏为此说,是为其研究戏曲张本的,因戏曲在当时不为人重,借助此说,可抵挡俗见),其说影响至大。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不过是一个旧说,其源头可追至元人(见钱锺书 《谈艺录》所考)。但此说既经王氏重提,在当时所生的影响,几乎是笼罩一代的。既然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么顺理成章,“唐诗之后就是宋词”,“宋词之后是元曲”了。亦以此,冯沅君、陆侃如所撰《中国诗史》,便只写唐诗、宋词、元曲,而于宋诗便一句不提了。冯沅君早年为新文学作者,其所著的小说,尝为鲁迅称赏。于此,我们可以推知新文学的人物,对于此说态度为如何了。
在这样几重影响下,近代诗之真面至于湮没,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但是历史并不真正过去,在后来的时间中,往昔之事,有时显有时晦,意义随之亦别,而显晦之际,历史是不恒定的。这对于近代诗史的认识,也必然如此。
一般论者把近代诗看作新文学之兴起的预备,或云是一过渡,这实是错误的看法。笔者认为,近代诗并非新文学之先导,而是中国三千年古诗之结局,且为一光辉的结局,即云它是中国诗的 “返照回光”,也无不可。新文学是极西化的东西,是从他文化移植过来的“逾淮之枳”,笔者向以为现代文化史上的胡适,其情形,颇类似于佛学史上的唐代的玄奘,玄奘从印西传来唯识学,而胡适则借欧西来造新文化,所以要截断众流。其结果,自然就是否定近代诗。这是胡氏的题中应有之义。
无疑地,中国诗盛于唐,变于宋,而衰于元、明,中兴于清。近代诗为中国诗的 “龙尾”,它绝非新文学的滥觞,新诗滥觞是西方,至少,其形式是西方的。笔者记得施蛰存评郭沫若的新诗,也说过“他的内容是诗,形式却非诗”。施氏也是新文学家,但他写旧诗,其意,是并不认可新诗的形式的。陈寅恪的尊人散原老人,亦认为新诗很肤浅,只徐志摩还有些意思,也不过是明初杨基那班人的境界。此亦为有意思的批评,可与施氏之语比观。从五四以后,写中国旧诗的人,大抵皆为研究传统文学的学者,不再有专门的诗人,专门诗人只写新体诗。如从胡适写作《尝试集》算起,那么,新诗也已将近百年,百年已经过去,新诗中迄未有大作家出现,目前也已为衰落之象。所以,胡适所提倡的新诗,其运势是否亦如玄奘所传来的唯识学,我不敢说。
无论如何,近代诗是中国诗的一个好的收尾,此自无可疑,而且,其价值也不仅是文献的,思想史的,而该是文学本身的。换言之,近代诗的文学价值,必须重估。有什么理由可以如此说?笔者拟从下面三点,来一睹近代诗的深度,此三点不过举其荦荦大者,其他可说的自然还多,但为了简省起见,以管窥虎(语见《三国志》),只谈这三点也可以了。
近代诗的“现代感觉”
近代日本最杰出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吉川幸次郎,在论及《散原精舍诗》时,认为:“在鲁迅以前时期承担文学之责的当数以陈三立为顶峰的一群诗人。”(见《中国诗史》)这是一个目光极准的判断,其优于我国近代学者如胡适、冯沅君等,可云不可以道里计。吉川并且认为,陈三立的一些诗,“完全是现代的感觉”。如下面这首《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四首之三)云:
露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散原精舍诗》卷上)
此诗作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 11月 14日,散原那时祭扫父墓后,正在归途的长江轮船上。近人狄葆贤《平等阁诗话》评价此诗云:“二十字抵人千百语。”何以“二十字抵人千百”?狄氏未详说。其实此种写法,极大胆而新鲜,其意理与境界,皆为现代人所有,而古之所无也,狄氏知而不能言而已。吉川氏解之云:“露和波都象活的生命那样蠕动着涌来,月光束缚着诗人。诗人感到苦闷,在抗拒。”(见《中国诗学》)其所绎说,差为可听。
不仅在散原诗中,有此种“现代感觉”,在其他诗人集子中,也有具现代感之作。笔者更举一例。如郑孝胥《杂感》诗云:
积伤不成哀,放眼阅众死。短长虽几希,颇复悟意理。三十四十间,正似重围里。被创兼饮血,枕藉动相倚。脱身老牗下,殆出神鬼使。疲形堕坚念,冲想驻驰晷。谬云中有得,寸铁恐难恃。(《海藏楼诗》卷三)
此诗作于郑孝胥四十五岁时,其年另有一诗,题为《叔衡来沪疗疾相见泫然因有斯赠》,诗后有一小注,云:“叔衡言可庄、弼宸皆以四十五岁卒,吾今年亦四十五岁矣。”知此首所感,乃是中年人的生死之思,写法可云惊心动魄。诗人将人生比为一场战斗,谓人之活至老死于牖下,亦如从战斗突出重围,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好运气所致,不是可以预期的。此一感觉,在古诗人是从没有过的,为确然的现代感觉。
笔者曩在法人蒙田 《随笔集》中,亦读到过此种想法,《随笔集》上卷有一篇《论年龄》,略云:老死是罕见的、特殊的、非一般的死,不比其他的死更自然,它很难获得,吾人不应指望,而出于某种特别的优待,在几百年中,此种自然的老死,仅赐予少数几个人,使其在漫长的一生,不遇到死亡所布下的各种险阻。若吾人既见世人纷纷死去,而自己一次又一次逃脱,就应承认此为幸运所致,而非人力所能者。
按此一思想,与郑孝胥诗所云云,是可以笙磬同音的。郑孝胥固不能读法文(据《郑孝胥日记》,郑学过一阵英文,但并未掌握),蒙田随笔在晚清,亦似未有汉译之本。此不过中西闇合而已。而其中所包蕴的现代感觉,是较然可见的。后来潘伯鹰《玄隐庐诗》卷二《吴秋尘三十生日》前半云:“人生三十匆匆度,绝似孤军转战来。嗟我裹创犹喘息,看君盘马亦迟回。”则是从《海藏楼诗》中作贼,非创语也,可以不论。
近代诗中的西学
前云郑孝胥诗与西方文学之冥契,是比较偶然的,其实除了此种冥契,近代诗中运用西方故典,在那时也是风气。关于此种风气,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曾有批评,已为世所知。另外,梁启超所批评的夏曾佑、谭嗣同等人诗中运用洋典故,即所谓的“亚椠欧铅”,也只是比较浅显的例子。
于此,钱锺书《谈艺录》中亦有论及,其所着眼则是从中国诗的艺术角度出发的。钱氏最推崇严复化用西谚的一联,为《复太夷继作论时文》一五古起语云:“吾闻过缢门,相戒勿言索。”称为“喻新句贴”,并且如盐着水,不见痕迹。但若换一种眼光看,就可能要别作论议了。因为,我国传统诗的主流是抒情的,惟此亦仅是事情之一面。而从宋诗开始,中国诗就向学问化发展,即所谓“以学问为诗”,或如清人所云 “学人之诗”。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这个新趋向感觉不满,提出他的批评,他主张应回到抒情传统,他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严羽的此种针砭,得到后人的许多同情,姑不论其所说之是非,只就其所提的事实言之,则其所谓“以才学为诗”,正是“学问化倾向”,正是宋人之新特点。不妨说,宋人与清人都是有意向此方向发展的。而元明诗则是蕲向于唐人,此即中国诗史的“唐宋之争”之本质。宋诗是对于唐诗的趋避与开拓,是学问化的诗,是中国诗之有效的发展,自然也是成了大功的。中国诗至于宋代,遂不复独以抒情为其特色,而同时加入议论、学问了。其以学问为诗,在清代更得大的进展,在乾嘉时期,其间最突出的代表,为翁方纲,他是以考订金石入诗的,当时反对他的人便骂他“错把抄书当作诗”。此一批评,或许是不无道理的,但其昧于古今之变,也是很显然的。到了晚清,此种学问化的倾向更厉害,一时之间,西学也进入中国诗,中国诗中的学问化,又复具有了新趋向、新发展。换言之,中国传统诗之“旧瓶”中,已装“新酒”。此与印度佛学进入中国后,禅宗兴起,于是禅学精神进入宋诗,其情形是极相似的。
关于近代诗的运用西学,可举一典型的例子,即吴士鉴《咏袋鼠二十韵同樊樊山丈作》。吴士鉴主要是学者,其传世之作为《晋书斠注》,此自为人所知。此外,他还为皇帝讲过《西洋通史》,于西史、西学,下过不少功夫。当然他也是一位诗人。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评其诗“喜用近代掌故及西史事实,能雅能隽”,其语非虚。汪氏《近代诗派与地域》又云:“吴絅斋(士鉴)为识时之俊,喜览译籍,间事篇章,运今入古,差有理致,要皆与康、黄笙磬同音者也。”他有一首咏袋鼠的诗,运用西学新知,可谓极诗家之能事的了,其诗云:
火地穷荒辟,西班牙人初觅得澳大利亚时,名之曰火地。奇珍袋兽稀。格卢胫或短,英人韦门道《百兽图说》:有袋之兽,曰更格卢,生于澳大利亚,其形前腿短。以美人潘雅丽《动物学》之说,即袋鼠也。欧白体同肥。欧白生为袋兽之一,生南美洲,形大如猫。牝牡原区类,牝者有袋,牡者无之。攀援善审机。时常攀树搜寻食物。五能殊矫矫,鼫鼠五技:能飞、能缘、能游、能穴、能走。此许叔重之说。中国古书无言鼠有袋者。八月尚依依。初生仅寸许,装于袋内,至七八月时,可以自行。似鹿圆颅耸,如猱信足飞。凌髯度温带,垂颈胜寒衣。襁属难离乳,囊探许贮餥。蹲趺知力巨,其足长而有力,恒蹲踞于尾。幽頞问名非。潘氏《动物学》:幽頞产于美国,小兽亦居母之袋。蒲米兰坚韧,潘氏谓土人捕袋鼠,系用湾曲之木,名曰蒲米兰。枞榕树馥馡。美人白雷特《澳洲风土记》谓:澳洲植物园中,松枞竹榕错置其间,颇形畅茂。盎悬疑腹硕,穴斗恨身颀。茂惹长河饮,澳洲大河,一谓之茂惹河。巴斯估舶归。巴斯为澳洲海腰。雪梨居远近,澳洲首府曰雪梨。露草啮芳菲。韦氏谓袋兽之属,分二种,一系食肉,一系食草。鼨辨斑斓采,分黑白围。无条除竹折,有螯莫嘘欷。缎鸟方成构,钻蛇敢逞威。皆产于澳洲,见《风土记》。卵真猪箭育,字岂獭窠腓。西国有袋箭猪,乳哺而卵生,生卵则置诸袋。又鸭嘴獭,亦产澳洲,其腹下有袋,亦卵生,每窠生卵两枚。均见潘氏《动物学》。赤道遥输赆,金环匪降禨。殊形栖桂苑,诡态隐松碕。郭璞图谁补,张华志漫讥。即今征异物,山海陋西騩。
按,此诗见于四卷本的《含嘉室诗存》卷三,全诗之所咏,皆根据于西书,不复为传统之博雅,而为中西融通之新趋势。据此诗,可见近代老派诗人在新方向上的努力。又如大史学家柯劭忞,则以英文入诗,其《严绍光西湖雅集图》开头云:“古来图画难俱述,谁似符头孤列勿。译言撮影。镜中鉴物能留物,十有三家皆阁笔。”“符头孤列物”,是英语 photography的译音。此亦为新学人诗之佳例,钱锺书在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注六十二中提过,不再赘述。
近代诗技巧之新进展
此为最后一点,关于此点,可举律诗之对仗言之。对仗为汉语文学中的特有现象,也是中国诗中的核心技巧之一,在五四时期,胡适等新文学作者最喜攻击的即为此点,此亦古所谓“射人先射马”之意。胡适有句甚谬而有名的话,即谓中国文化中的律诗与小脚、鸦片,此三样东西,是最为糟糕的。其实小脚、鸦片,皆为陪衬语,其用意自是为了攻击律诗。此一谬说,在当日是有大影响的,但是,陈寅恪先生不以为然,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云:“对偶确为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而欲研究此种特性者,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所产生之对子。”(见《金明馆丛稿二编》)无论陈、胡,撇开其持说的是非,实皆已认识到对仗之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技巧,所不同的是,胡是要批倒中国诗,为无对仗的新文学开路,所以就有如此的一个谑虐的话,而陈寅恪则是 “中学为体”、要发扬中国文化的人,评价自然反对了。就对仗在律诗中的发展说,前人公认是到了南宋的陆游,则几乎有了令人叹止的表现,南宋末年大诗人刘克庄就早说: “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 (见《后村诗话》)其所举的例子有:“子午谷,丁卯桥;一弹指,三折肱;乞米帖,借车诗;虎头,鸡肋;一齿落,二毛侵;岩下电,雾中花。”这在我国古诗人,正为“拿手好戏”。
而在近代诗中,此一传统的技巧,亦有了更进的发展,其代表人物,端推那位大才子易顺鼎。易顺鼎在当日是被王闿运称作“仙童”的,他与曾国藩之孙曾广钧齐名,曾广钧则被称作“圣童”。其七言律诗对仗组织之妙,在当时是公认无人可比的。他自己对于对仗,也有一番极夸口的议论,他的《琴志楼摘句诗话》云:
余自信此集(指《四魂集》),为空前绝后、少二寡双之作。……杜诗亦讲巧对,如“子云清自守,今日起为官”,及“大司马”、“总戎貂”之类。况余诗对仗皆用成语,且不喜用僻典,而所用皆人人所知之典,又皆寓慷慨悲歌、嬉笑怒骂于工巧浑成之中,自有诗家以来,要自余始独开此一派矣。
又云:
余尝有一推倒一时豪杰之论云:“无工巧浑成对仗,竟可以不必作诗。盖尘羹土饭、人云亦云之语,虽数十万首亦作不完,何必千手雷同,徒费纸墨乎。”
此语固为极端,但亦确有至理在,此不暇详论之。他本人在《四魂集》中的对仗,多有天才的表现,对于近代诗而言,可为一典型。试举数联如:“城郭人民丁令鹤,楼台冠剑子卿羊。”(丁、子是干支对)“竟同鹏举死冤狱,无怪马迁修谤书。”“李怨牛恩朋党论,桃生羊死贱贫交。”“边墙故迹熊经略,幕府高贤鹿太常。”“中朝旧议封关白,上相新闻使契丹。”“忍耻灭吴求范蠡,写忧适越学梁鸿。”“深州未出牛元翼,浪泊难归马伏波。”等等,其中的人名,对仗都是极智巧的。
陈寅恪为清华学生入学考试,而出“孙行者”的上联,意中要人对以“胡适之”,那是仿了苏轼一联诗的对仗,即:“前身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是犬名,叹为“东坡此联可称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其实,易顺鼎的此种对仗,在其诗中是层出不穷的,比之苏轼是为远过了,苏轼只偶有一二例,比之陆游犹尚不及,所谓“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在易顺鼎之前,是可以那样说的,但易顺鼎出来后,就要超过去了。也因为这个缘故,已故的思想史学者蔡尚思,在其《中国文化史要论》中概论“文学史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于清代之诗人,独推二人,其一即易顺鼎,云“他作诗特长于对仗,就这一点而论,确实是超越古人的”。这意见是不错的。
* * *
最后,对于近代诗成绩的评价,在前人并不乏积极之肯定,有见识的学者,是甚至以为超过宋诗的。如江西诗人欧阳述,在《浩山诗钞自序》中云:“犹记壬寅三月,与文道希(廷式)学士同寓沪上,深夜谈诗,学士举郑公苏龛、沈公子培之句,相与吟味。述因言近贤诗境,似非雍乾诸家所及。”(见《浩山诗钞》,光绪间刻本;按,陈澹然 《彭泽欧阳笠侪墓表》云:“尝谓本朝之诗,极古今之奇变。”亦可证。笠侪,欧阳述字)另一位江西诗人曹震,亦云:“并世诗人,突过乾嘉。”(见《光宣诗坛点将录》)又皖诗人陈诗《上郑海藏先生》云:“海藏与散原,坛坫峙二派。势若决江河,孰能窥其际。……光宣胜嘉道,二公实振旆。”(见《鹤柴诗存》卷四,一九二四年刻本)皆是。后来的学者,如胡先骕也说:“晚清末季,诗学甚为发达,大家名家辈出”;清末之诗,“远迈康雍、乾嘉”(见《四十年来北京之旧诗人》)。这些皆于近代诗有真确的认识。而就中以汪辟疆所言,为尤能探本:
“晚清道咸以后,为世局转变一大关捩。……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在此五十年中,士之怀才遇与不遇者,发诸歌咏,悯时念乱,旨远辞文,如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袁昶、范当世、沈曾植、陈三立诸人之所为者,渊渊乎质有其文,海内承风,蔚为极盛。”
并以之与宋诗作比较云:
宋诗承三唐之后,力破馀地,务为新巧,大家如东坡、临川,亦复时弄狡狯,以求属对之工,使事之巧,如鸭绿鹅黄、青州从事、乌有先生之伦,已肇其端。南宋诸贤,迭相祖述,益趋新巧。近代诸家,虽尝问途宋人,然使事但求雅切,属对只取浑成。……其尤有进于是者:诗歌一道,原本性情,似与学术了不相涉,才高意广与夫习闻西方诗歌界义者,尤乐道之;咸主诗关性情,无资于学。然杜陵一老,卓然为百代所宗,彼固尝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云“熟精《文选》理”。昌黎亦言“馀事作诗人”。是诗固未尝与学术相离也。两宋诗家,承三唐声律极盛之后,独出手眼,别开面貌,其精思健笔,洵足惊人!然尔时作者,惜多不学;……近代诗家,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流风未泯,师承所在,学贵专门,偶出绪馀,从事吟咏,莫不熔铸经史,贯穿百家。故淹通经学,则有巢经、默深;精研许书,则有 、匹园;擅长史地,则有春海、寐叟;通达治理,则有湘乡、南皮;殚精簿录,则有郘亭、东洲。其专为《骚》《选》盛唐,如湘绮、陶堂、白香、越缦、南海、馀杭诸家,亦皆学术湛深,牢笼百氏,诗虽与宋殊途,要足与学相俪,则又两宋诸诗家所未逮也。(见《近代诗派与地域》)
此节所云,特具史家之大眼光,而为诗史的“大判断”,卓识高论,最为可取。其中于近人囿于西诗界义,且亦已有所批驳,故不惮烦而详引之,并以结束本篇云。
作者:王培军(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编辑:于颖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