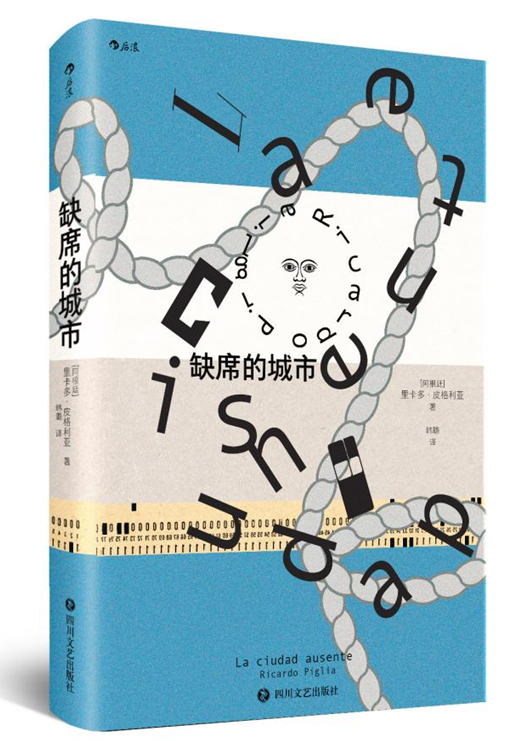
《缺席的城市》
[阿根廷]里卡多·皮格利亚 著
韩璐 译
后浪 |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名记者朱尼尔在收到爆料后,踏上了追查一台神秘机器的旅途。
这台机器拥有一个女人的心智和灵魂,能够输出故事。它是由一个与阿根廷先锋小说家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同名的人物,在心爱的女人去世后创造的,其目的是让爱人在讲述故事中获得永生。
除了个人的爱情回忆,机器还守护着流传在城市里的集体记忆。当她通过重重文本和磁带录音,影射现实、传播真相时,警察也介入进来,试图将机器捣毁。
朱尼尔在城市里四处游荡,在不同的故事中进进退退,试图解开那条总是充满等待和延宕的线索。直到有一天,他来到了世界尽头的的一座小岛上……
——拉美当代文学大师里卡多·皮格利亚代表作中文版初面世。《缺席的城市》是作为其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已被译为多国语言,曾被阿根廷20世纪重要音乐家赫拉尔多·甘迪尼(Gerardo Gandini)改编为同名歌剧。
>>内文选读
我一直喜欢那种有数条并列故事线索的小说。这种情节的交错与我对现实的强烈印象紧密相联。在这个意义上,《缺席的城市》与生活极为相似。有时我会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人在不同的情节之间游走,感受到一天之中,当一个人和朋友、爱人,甚至是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便触发了一种故事的交换,一个多重门一般的系统,打开它便可进入新的情节——这就像一个我们居于其中的语言网络——而叙事的核心品质便是这种流动,一种明显的向另外一条故事线索逃逸的运动。我一直试着描述这种感觉,我相信这就是《缺席的城市》的起源。
通常来说,我们倾向于从一个文本中推断出某种隐藏的社会样貌,想象文本写作的那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与此相反,我在“岛”这一小节中试图做的,是创造一个可能构成《芬尼根守灵夜》的背景的社会。这个社会不是乔伊斯写《守灵夜》时所身处的那个社会,它不指向爱尔兰与英格兰的紧张关系,也不涉及其他一切构成真实文本背景的要素。我想探寻的是:在什么样的想象性背景中,《守灵夜》作为一个文本是有效的?换句话说:在什么样的社会中,《芬尼根的守灵夜》可以被当成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来阅读?答案是:一个语言不断在变化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方法作为一种可能的文学批评的模式一直吸引着我。我认为文学批评应该试图想象文学作品中隐含的、虚构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变成了:《芬尼根守灵夜》中隐藏的现实是什么?答案是:一个人们认为语言就是写在文本中的东西的现实。
《缺席的城市》同样如此。你可以说在《缺席的城市》中,我想象了一个被故事所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真正存在的是被讲述出来的故事,是讲述破碎的阿根廷故事的机器,我要写的就是一部关于这个社会的现实主义小说。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我在“岛”中对《芬尼根守灵夜》的化用与整部《缺席的城市》中应该发生的故事之间的联系。
我感受到自己与某些当代作家,比如托马斯·品钦和唐·德里罗,有一些共通之处,说句玩笑话,我将之称为一种关于妄想症的虚构。在某种程度上,它来源于对其他文本的阅读,比如威廉·巴勒斯、菲利普·迪克,又或者罗伯特·阿尔特。一种关于阴谋的观念普遍见于这些作家的作品,在《缺席的城市》中同样如此。这种观念认为社会是由阴谋所构建的,相应的,也存在反阴谋。这就将问题拉向了与文类的某种关系,拉向了对政治作为阴谋的一种反映。我指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文学;传统政治文学里有私人世界和公共世界之分,
而政治小说与公共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我指的是,政治与文学这两个类别之间的边界消弭后(也许这就是后现代的定义,公共与私有之间对立的消解,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对立的消解),政治在文学中呈现的方式。当所有这些二元对立都消失的时候,阴谋、诡计,就会作为主体把握政治在社会中意味着什么的模式而出现。
私人主体对政治世界的感知几乎就像希腊人对命运或者其神祇的构想:它是一种怪异的操纵运动。这是一些小说家,包括我自己,对政治世界的感知。也就是说,政治借助阴谋这一模式,借助诡计这一叙述,进入当代小说——即使这种阴谋不带有任何明显的政治特征。形式本身构成了小说介入政治的方式。阴谋不一定必须包括政治诡计的要素(虽然它也许包括,比如诺曼·梅勒的小说)才能使阴谋的使用机制变成政治的。它可以是涉及信件邮递的阴谋,可以是有关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的阴谋,也可以是其他任何的编造。小说这种形式本身表明,我们对当今世界政治的感知是虚构的。
需要补充的是,这样的观念已经出现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了。他是第一个运用这种模式的人,因为《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就是建立在一个阴谋之上,《叛徒与英雄的故事》《小径分叉的花园》等其他故事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博尔赫斯,通过建立他的迷你世界,成了第一个谈论平行世界,以及阴谋作为对现实的妄想性政治表征的人。这种对原本不相容的事物之间关系的感知是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会看到疯狂迷恋历史的体,或者因为宇宙而陷入癫狂的主体——又或者,例如在《缺席的城市》中,面对虚假现实而经历谵妄的主体。
最后,我相信一本书的译者总是经历着一种与其作者的奇特关系。这不仅涉及风格、参考、可能的错误,或者翻译可以对文本进行哪些改动。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翻译所涉及的工作,一方面,翻译是一种不寻常的阅读活动,另一方面,它还涉及一种所有权。我一直对翻译与所有权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因为译者事实上改写了整个文本,这个文本既属于又不属于他 / 她。译者总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奇特的境地,因为他 / 她的工作是将一种既属于他 / 她又不属于他 / 她的经验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作家会引用或者直接复制别人的文本,我们所有人都偶尔这样做过——因为一个人会遗忘,或者太喜欢那个文本而不得不这样做——但译者进行的是一项在这两个地方之间画出一条小径的工作。可以说,翻译是一项奇特的挪用活动。
我对文学中的所有权的态度类似于我对社会中的所有权的态度:我反对所有权。我认为翻译中存在一个所有权的游戏。也就是说,翻译对文学常识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提出了质疑,文学中的所有权问题就像社会中的所有权问题一样,事实上极端复杂。语言是一种共同财产;在语言中,没有所谓的私有财产。我们作家总是尝试在语言中放置标记,看看我们是否能阻止其流动。语言中不存在私有财产,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普遍流动的循环。文学中断了那种流动,而这也或许就是文学的本质。
(本文节选自《缺席的城市》英文版译后记,作者塞尔希奥·魏斯曼)

>>作者简介
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1940—2017),阿根廷作家与文学评论家,当代西班牙语文坛最重要的声音之一。
皮格利亚以短篇小说开始他的创作生涯,并凭借首部小说集《入侵》(1967)确立了他作为作家的声誉。他的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人工呼吸》(1980)、《缺席的城市》(1992)、《烈焰焚币》(1997)、《夜间目标》(2010)及《艾达之路》(2013)。此外,他还留有大量散文、评论与剧本。
皮格利亚曾获得西班牙“文学评论奖”(2010)、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2011)、阿根廷作家协会“最高荣誉奖”(2012)和西班牙“福门托文学奖”(2015)等重要奖项。
1973年,皮格利亚曾访问中国,并与郭沫若进行了会面。
作者:塞尔希奥·魏斯曼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