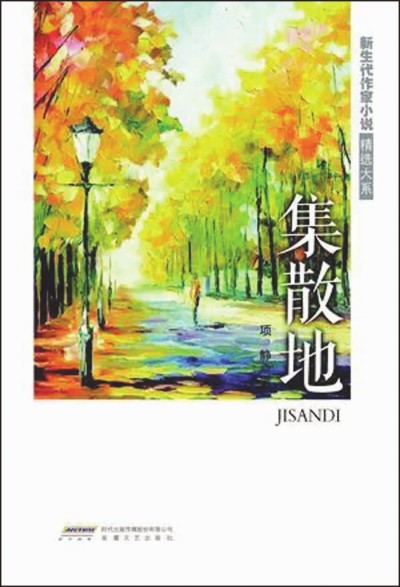
▲《集散地》项静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许多年以后,“我”在深夜的陌生城市收到已经失散许久的少年时代朋友的短信。那个叫作尹小跳的女孩说:23点11分,我经过你所在的城市。这个时候,“我”站在窗前打了一个哈欠,“感到有一些液体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落下去,好像一下子回到集散之地,人们来来往往,不会驻留,它让你情不自禁,无处藏匿。我极其不满意自己这种婆婆妈妈的态度。”但是,叙述者终究没有控制住真情,可能是小声的嘀咕,也可能仅仅是在内心中沉默的呐喊,忍不住嘟哝了 一句:“我——想——念——你——尹小跳——”这是项静《集散地》里题名小说的结尾。
怎么样,这样的情节和语言,有没有村上春树的影迹,像不像塞林格那个霍尔顿的口吻,会不会让你想到夏洛的网? 带着一丝散淡的忧伤和惆怅,却又有着未经损耗的活力和想往。《集散地》最能打动人的是那种关于时间与变迁体验的篇章,因为那些注定会消逝,并且绝不会再回来的东西,其中细微的宿命感本身就有一种永恒性,总是会触发我们关于人生的种种同情与共感。那些事物是最为铭心刻骨的纯真、懵懂、浑噩又葱翠的青春和友爱———人们都会经历,偶尔交集的时刻,然后浮萍一样散开,就像人生本身。如同任何一个有过如此普遍性经验的写作者一样,项静忍不住会让它们在文字中落脚,以免在现实中失散后就灰飞烟灭。所以,在《桑园会》中我们会看到侯孝贤、朱天文般的浮云温柔和世事緜邈,这倒并不是说项静受到《童年往事》或《冬冬的假期》的影响,而更多可能是自然的天机触动,因为尽管具体的时空可能会不同,成长所面临的恒久主题——变化——则是共通的。
但项静更加年轻,她的经历也并没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所以她的记忆便少了一些物哀的意味。项静不是那种喜欢戏剧化的文艺青年,毋宁说她给人一种温婉的书卷气,一个普通青年的表象——当然,这种表象之下也可能隐藏着惊雷与风暴,只是它们会以另外的面目出现。普通青年沉潜在生活的河流之中,并不会有太多飞扬起伏的狗血遭际,即便有旋涡暗礁,也会被日复一日的潮汐冲刷沉积,凝结成岸边沉淀而光滑的石头。《明亮的星》里走出了小镇的少年,即便是在青春记中也不会是青春祭,虽然有怀旧,但那怀旧也是匆匆而过,恍若大野有风,吹过丛林,树叶簌簌作响,旋即止歇,而风已走过,虽然有的人可能永远留在普集镇的夏天里,一切还有余地,一切都才刚刚开始,道路向前铺展开来。“世界什么都没改变……又好像一切都变了”,变与不变之间,是一颗赤子的心。
赤子之心,绝假纯真又倔强无匹,对于80岁的韩尚英也是一样。一路闯关,到最后返璞归真,老儿子意外身亡,她也并没有想得开或者想不开,总归就是“我管不了那些事儿”(《上高山,跐高台》)。这是一个为己的老太太,倒并不显得自私,因为那是一种经过了沧桑之后的坦荡。对于项静的小说而言,这其实构成了一个换喻。“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置换到写作中,我们可以很容易辨别那些最初一念之本心的“为己”写作的诚与真,和那些事先被外在要求束缚的“为人”写作的断裂与隔膜。这倒不是说“为人”写作不真诚,而是说在起心动念的写作原初,一定是从最初一念的切己感受开始的,而后才会有人生、社会、道德和文化诸如此类的踵事增华。
从“为己”开始,是一种天然生发,如同植物种子在特定时节应信发芽,而此后的苗实枝蔓也并没有一定的明确规划。所以《集散地》中的诸多篇什,确实如同集散地上的散碎花朵、杂沓人群。《平行线》中堂兄弟俩的不同人生,隐喻了决绝而又缓慢的乡土变迁;《世上桃园》中旋即隐退在生活中的少年莫名案件,是命运与偶然;《欢乐颂》中日常琐碎和代际差异形成的黑色幽默,不乏情感与伦理形态的转折……题材与人物取向各异,似乎都指向某个不动声色而又不容置疑的社会过程,然而它们又都是含而不露的。年轻的项静很早就获得了洞若观火而又人情练达的文字能力,她笔下的篇章自成一体,混融难分,成为一个个既各自独立又隐约关联的世界。她无法(可能任何人也无法)对那世界进行评判,但赋予了它们一种敞开性,让那些晦暗、含混、黏稠、油腻的人生与故事获得一种清晰如少年般的形式感。难解之谜没有在因果逻辑中取得答案,但混沌因此打开,启示由此产生。
项静更多是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知名,我还记得某次在浦东机场送别一起吃饭,她说到自己最心仪的还是做学术,所以她出的这个小说集确实颇让我吃惊。事实上这些小说显示出了一个与批评文字中的项静堪称截然不同的面目,它们更含混,更犹疑,因而也更丰富。《挑绷头》和《下落不明》讲的都是无因无果的片断,同学罗念莫名其妙地出走了,随之浮现出来的只是一些难以接续的零碎回忆和想象建构;而在蒋小雅生活中偶尔出现的快递员和她情侣一样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消失在人海之中。有意味的是,项静没有把它们结撰成浪漫主义的庸俗情节剧,而是让无疾而终本身成为一种状态,氤染成一种当代感受。这种人生无常的体验也许曾经以抽象的形式贯穿在人类社会的始终,然而此时此地,它们都锚定在当代的嘈杂、匆忙和混乱之中。项静的叙述者以一个冷静而不是温情的面目出现,它尽量隐匿主动的激情,呈示给读者一个放弃了索解欲求的人生情态。
这个人生情态是一种过程中的情态,人生还很漫长,插曲所在多有,浪花不停翻滚,河流自会向前。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仙人掌》和《在烈士陵园下车》的开头都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仙人掌》的情节不过是一个俗套的同学聚会故事,但是它的开头是主人公叶诤的地铁遭遇:一个中年男人晕倒在车厢中,在他苍白的面容、凸起的腰腹和虚弱的身体上,叶诤窥见了让自己不安惶惑的可能性。这个略显惊悚的开头与接下来的繁琐日常形成了结构上的映照,让人怵惕自省而心生悲悯和谅解。而《在烈士陵园下车》中的谢嘉也是公交车上奔赴不可知的未来,“每个人都是时间的奴隶”,意味着此后发生的或者怪异或者平常的情节都不过是曲折人生中的偶然一幕。至于琐碎的龃龉和日常的折冲是否有答案,并不是无人关心,而是无力去寻求。这也许体现了我们时代写作者的一种普遍心态,他们再无信心去在宏观中把握历史的脉象,因而回复到为己的初心和本真,在呈现中触发启示。
项静在这个小说集的创作谈中写道:“每一个地点都不会固定,人来人往,就像旅游集散地这种地方,匆匆忙忙,但谁都有漫长的影子,来处与去处,辑录了他们人生的片段,连缀成篇。而所有这些空间里,都承载着我内心感受到的个人和时间的变化,故事各自独立,看起来没有很大关联,但我知道它们一起拥挤着想要走去的方向。”其实,人们想要去的方向只有在行走中慢慢确定,就像这个小说集中的故事各自独立,每一个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可能并不构成一个秩序井然、条理整饬的建筑,却将自己生长为一株根茎在地下蔓延纵横的藤蔓植物。显然,植物更具有生气,并且包孕了多样的可能性,在枯荣之后还有葳蕤,收获之后仍会再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辑制作:李硕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