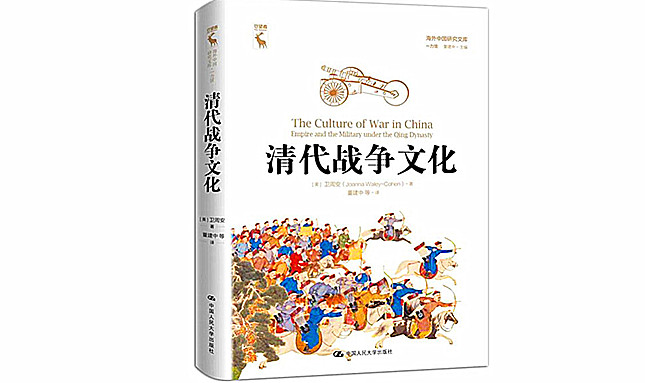
▲《清代战争文化》,[美]卫周安著,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卫周安是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军事与文化史专家,其叙述极有洞察力,展现了军事文化对清廷和公众生活方面的塑造。但卫周安关于尚武精神是清朝文化核心一说值得商榷。无论“重文轻武”还是“重武轻文”,都是王朝基于不同政治环境的产物。
军事胜利及尚武精神被有意推向文化生活中心
在文、武二元范围认识清朝本质,偏重文的一面可能被归为“汉化说”派,偏重武的一面则可能被归入“新清史”派。两派的重要分歧在于如何认识清朝的“尚武精神”。“新清史”代表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所著《清代战争文化》采取迂回策略,从文化史角度探讨“满洲以骑射为本”的尚武精神,挖掘其在文化层面的意义。是书认为“长的18世纪”意味着清朝的漫长征服历程。伴随一系列战争,军事胜利及尚武精神被有意推向文化生活的中心。18世纪盛清帝国宏业展示的正是这种军事征服和文化转变。这一系列微妙变化,是康雍乾三朝扩张的结果,特征则是“吸收并改造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仪式的、思想的、精神的、道德的、有形的、视觉的物质文化”,引导人们“关注并敬重军事成功、尚武精神及最引以为傲的结果——帝国的扩张”。
卫周安将文化领域的这种微妙转变称为“文化的军事化”(militarization of culture)。她认为,这种煞费苦心的文化转变,在建立清帝国宏图大业的过程中,与军事征服同等重要。由于这种视角,本书有别于孟森、罗尔纲、濮德培等人的军事史研究,而更多地将军事置于王朝政治与文化的环境中加以综合考察。
该书第一章《军事文化与清帝国》提出“文化的军事化”这一重要概念。卫周安所言“文化”涵盖思想、艺术、建筑、宗教诸多方面,“军事化”则指军事对文化生活广泛而全面的渗透。她认为,“文化的军事化”与军事实力密切相关,涉及政府文化与风格转变,影响政治环境,甚至更新“军事”的定义。比如,土尔扈特人回归即是无战争的军事胜利。“文化的军事化”还促成军事主题进入官方赞助的文艺、建筑、景观等方方面面,最终,私人的文学作品也弥漫着帝国军事开拓的遗风。
此后的几章,分主题讨论清帝国的这波文化运动。
《纪念性的战争》着重从纪念碑、绘画、建筑与纸本文献探讨乾隆“十全武功”,认为这些纪念形式和纪念文献自具生命力。通过对比北京和承德的纪念碑,卫周安指出清代对战争纪念存在多层次的规划,从而证明尚武是更高级文化的标志。皇帝的提倡影响民众对军事的普遍认知,可能导致19世纪地方社会的军事化。
《宗教、战争与帝国建设》关注第二次金川战役中宗教的作用,认为这是清朝巩固某类宗教群体对皇帝忠诚所致,符合“一种连续不断的宗教战争模式”。
《军礼和清帝国》分析清代各种军礼如大阅、命将、郊劳、献俘与受俘、凯旋等象征性礼仪活动,认为军礼的文本和戏剧化的礼仪传播效果,推动“文化的军事化”目标的实现。
《帝国的空间变化》认为,在文化转变计划的推动下,清朝一整套军事文化的意义得以进入政治生活、实体景观和物质文化中,从而使人们对武功和皇权更加敬畏。卫周安认为,各种“观念空间”和实体景观已不可避免打上军事印记,如承德行宫将各地景观建造为类似“世界之窗”那样的微缩版帝国,“促进了帝国内部空间的转变,旨在成为清朝军事力量的永久提示物。”
对清朝“中心与边缘”的认识偏差
纵观全书,卫周安特别强调,尚武精神是整个文化运动的基础。
卫周安认为,满人不同于以往王朝重文轻武的倾向,更偏爱内亚模式,重视军事力量。对清帝而言,弘扬尚武精神有助于避免明朝灭亡的覆辙。在此意义上,卫周安提出尚武精神在清朝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是欧立德所谓的“满洲之道”。这种倾向使卫周安对清朝的“中心与边缘”产生了认识偏差:“清朝在它权势的鼎盛时期,无论在地理还是在文化上,都不再把中国视为帝国的中心,而只是一个更为广阔疆域的组成部分——当然是极为重要的部分。”
换言之,在卫周安看来,帝国的中心在内亚,而非传统中国。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也是“新清史”的重要见解,却无法解释江南及整个运河流域在清朝政权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漕运、盐政还是治河等工程,都是清朝行政最为关心的首要内容,是日常施政当然的中心。不能因江南和运河流域的重要逐步日常化,而瓦解这些地区的中心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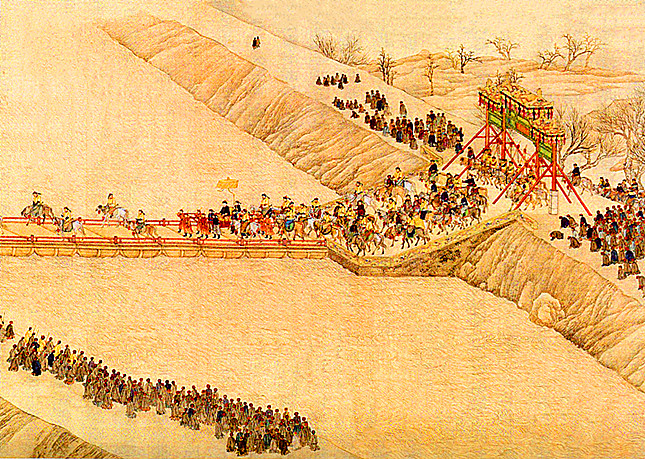
▲乾隆皇帝南巡图(局部)
内亚和边疆交锋的表面化和事件化,凸显和放大这些事务的重要性,但热点地区未必就是帝国的中心。正如军事征服及“文化的军事化”仅仅是清帝国宏业的一部分,康雍乾的边疆事务也并非帝国事务的全部。与之相比,江南地区的漕盐改革与黄河治理,毫无疑问是帝国更重要的支柱,毕竟涉及帝国的经济命脉。张勉治《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揭示,清帝国以巡幸模式在江南推行政治合法性建构,正反映江南之于帝国的重要意义。
与军事征服西北边疆相比,清朝对帝国中心——江南只是采取了不一样的统治模式。有趣的是,在当代关于清代的研究中,“新清史”对内亚和边疆研究方兴未艾之际,江南和大运河研究也如火如荼,这恰好反映了不同学者对清朝中心看法的差异。
卫周安关于尚武精神是清朝文化核心一说更值得商榷。她认为,“从历史上看此前各朝多是重文轻武”。但这并非中国历史的实际。以向来被视作“右文”之极的宋朝而言,近年对宋代文武关系的研究也不再支持简单的“重文轻武”结论。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提出,宋朝并非只重视文教而不重视军事。无论“重文轻武”还是“重武轻文”,都是王朝基于不同政治环境的产物,并非满洲的民族特性。由此,“新清史”一派学者可能过于拔高“尚武精神”在讨论清王朝性质上的作用,而“汉化说”一派在此纠缠则是不必要的误会。
在论述乾隆有意规划各类纪念物时,卫周安过于强调乾隆自觉的历史意识,不恰当地投射了当代观念。乾隆与其祖父康熙一样,具有英雄主义人格,但未必有意使用一系列历史和记忆操控技术去左右战争记忆。比如,对于战争纪念碑多语种呈现及图像表达,可能只是旧有传统的复苏。卫周安特别强调,《平定西域战图》等图画文本,并非“新的文化基础”。马雅贞《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经研究发现,那些战勋图像在“明代却是官员间盛行的视觉文化之一环,清帝王透过转化汉人精英的视觉表述遂行其文化霸权,到了乾隆朝逐步形成以战争图像为核心的武勋展示,最终确立了展现满洲武功霸权的体系”。
清代有其特殊性,但其接续明朝的“近传统”一面也不应被忽视。需指出的是,本书在诸多方面强调清朝的军事胜利,往往以明朝军事失败作映衬,这一定程度遮蔽了明清两朝内在的连续性。
过于着眼清帝国扩张与军事征服
通读全书,卫周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令人印象深刻。她认为,18世纪清帝国的军事行动不仅奠定帝国疆域,其组织动员的方式与塑造战争记忆的模式也深刻地影响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和社会走向。她进而提醒人们注意清朝这种军事文化遗产对此后百年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意义。
清朝中前期的武功之盛,与近代史的关联真的那么密切?基于乾隆朝军事武功造就的军事文化遗产来论断清帝国并非孱弱,而是征服性质的帝国,恰恰人为扭曲了清代中前期与晚清的连续性。乾隆取得“十全武功”之际,为何不再军事扩张?在为现代中国寻找历史源头时,1800年以来清朝一系列战争遗产难道应当被忽视?我们固然不应以1840年以来清朝在战争上的孱弱表现来认识整个王朝,然而单纯将清朝视作一个征服王朝,恰恰忽视了这一时期清朝在战争上的作为。
审视清代中前期军事文化遗产时,本书也过于着眼帝国扩张与军事征服,并将目光主要锁定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而未对康熙平定台湾、乾隆晚年处理川陕白莲教起义等战事作处理。对东南地区战事的关注,令人留意到,清代的军事征服多因国家生存空间而引发,并非满洲尚武精神的特性使然。否则,为什么乾隆即位初期就慨叹“我国家承平日久,武备渐弛”,“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致生疏矣”。鸦片战争时期,坚持主战的汉族精英而非满洲勇士。另外,19世纪地方社会的军事化,与其说是受清代尚武精神的影响,不如说是18世纪末以来连绵起伏的地方叛乱不断锤炼民众所致。
卫周安的研究还有一令人遗憾处,即引文中几乎没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果说清史研究是世界性学问,那么中国学者的成果就不应被忽视。“新清史”论著对材料和论点的片面性选择,并不会增强其说服力。卫周安致力于为“新清史”辩护,使其视野存在遮蔽情况。与之相对应的是,马雅贞《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立场先行的误区。该书“跳脱‘汉化说’与‘新清史’的框架,从皇清文化霸权的角度,重新反思满族得以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不同机制”。在围绕“新清史”争议越发激烈的当下,马雅贞此书揭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即跳脱旧有对立的框架进行对话和言说。对中国学者而言,欲在“新清史”争论中占据有利位置,除去取径新的言说外,还应寻求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解放,如此,方能在诠释清代历史上占据主动,而不致在研究话题上受人牵引。
作者:尧育飞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张裕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