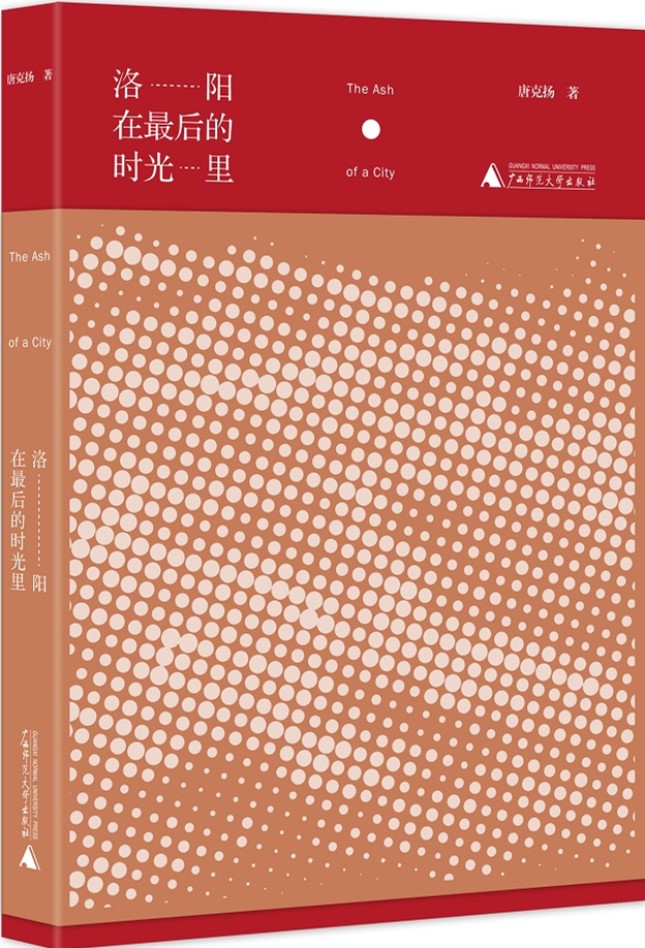
▲《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唐克扬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们在大地上规划和修建起伟大的城市和建筑。城市中的分隔、边界和那些希望上通天界的高塔佛寺,世俗的努力无一不代表着人类精神上的愿望与希冀。城市的生活空间,真实地展示出一个时代中人们不同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对于时间、空间和永恒的理解。
在本书中,这座数度毁于兵灾战火的城市被还原和重生,街巷相通,人声鼎沸,北魏洛阳这座中国古代最辉煌的都市之一的最后时光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纸上。
深入洛阳城,自然没法不谈洛城人。我们心中不约而同想到的洛城人,多半还是洛河上“凌波微步”“翩若惊鸿”的美艳女子。沉于洛水的窈娘,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旖旎动人。特别的,千古传诵中的“洛神”是洛阳专属的代言人,在曹植的笔下,洛水女神宓妃和他的意中人甄氏是一体两面的。
但 “美人”并不一定专指女性,仗剑嬉游的“君子”也常有令人倾倒的风姿。曹植在《名都篇》里这样写道:“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
曹植笔下的妖女和少年同是洛阳的人情与风景,他们斗鸡走马的鲜丽生活,既洋溢着让人艳羡的贵家气息,又富于难以抵御的通俗魅力。最迷人莫过于“掷果潘安”这样的传奇故事:一旦潘安出现在路上,全城的少女仿佛都撵在了美少年的身后,她们大胆的热情澎湃荡漾,似乎是漫山的春色无处安放,于是少女们纷纷将鲜果扔到潘安的车中,令他每次都可以满载而归。
可是洛城人的故事绝不会仅仅是如此美妙,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就太低估复杂的人性本身了——那样,我们也就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疑惑:这城市末日戏剧的舞台已经搭好,但谁才是推波助澜的演员?谁又是山呼海啸般的看客?

▲千古传诵的洛神是洛阳专属的代言人
嬉笑和喧闹中“官民杂处”
洛阳城中住的不都是罗马共和国意义上的“市民”,相反,大多数洛阳“城民”共享——“官民杂处”——的社区并不能提示他们人生权益,甚至人身自由的巨大差异。相当一部分洛城人,其实是工有所专,服务于北魏上层贵族的“部民”,也就是“专役户”。更差一点的,是过着悲惨生活的 “刑徒”和“奴隶”,自古皆然。不自由的,甚至也还包括那些挥锄劳作于洛阳城外、平时住在城里的“城民—部民—农民”。平日里这批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战时则成为军事有生力量的来源。城市首先是他们的过夜容身之处,其次才是消费娱乐之所。
“城民”之中还包含特殊的政治人群,比如商之“顽民”的后裔,这些人在洛阳的沦落在于他们不太美妙的社会品级。从周公的时代开始,在那时还不大的洛阳城中,就已经住着一批“异见者”的后代,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同时也带来了坚决不肯服从新诰命的商代遗民,那也就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所写到的,被历代轻视和虐待的商之“蠢殷”。这批执拗的遗民的居处,自然“城隍偪狭,卑陋之所”而已,直到鲜卑人入据了洛阳,他们依旧是在这里居住的朝廷官员轻看的对象,以至于大家纷纷搬家,去往更“高尚”的体面人社区了,只剩下烧制瓦器的工匠满不在乎,照住不误。
有贱民区和贫民窟,便有相应的“高尚社区”。“高尚”首先受惠于政治上的优势,洛城,首先必须是高贵洛城人的舞台。洛阳内城以西,张方沟以东,南近洛水,北达邙山,东西宽二里,南北长15里的一块地方,集合了30个属于高贵人的里坊,总名叫作“寿丘里”,这是皇族簇集的住地,老百姓统称它们为“王子坊”——“王子坊”,到底是 30个“超级街区”的物理总合,或只是对这样的住区等级的统称,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今天流传下来的只有在其中发生的故事。在王子坊中,河间王元琛素以富丽豪侈出名,他经常和高阳王元雍较着劲儿,看谁更加奢华,两人的竞争追步西晋时洛阳人石崇、王恺斗富的前事。元琛所建造的“文柏堂”仿自皇宫太极宫里的徽音殿,他在其中置造了黄金做的水罐和玉石砌的水井,并用五色金丝搓成井绳;河间王府中还蓄养了300个歌妓舞女,都是全国的上选美人。可就这样,他还是比不上元雍,那家伙富可敌国,第宅园苑和帝王家的不相上下,家中养有僮仆六千、乐伎五百,“出则仪卫满路,归则歌吹连夜”,一顿饭就吃掉几万钱。
“高尚社区”的定义主要是因为门第上的原因,而在古代城市中,社会地位的“高尚”既可能意味着“品”,也可能关于“流”——若要细究,前者显示了政治等级的“高低”,后者则是约定俗成的社会身份的“贵贱”。那会儿,尽管洛阳城中已经出现了大批贸易致富的商人,这些阶级夹缝中的得利者却还不太得志,有钱并不见得“入流”。
最后,便是《洛阳伽蓝记》中浓墨重书的佛寺了,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事物,它是以上诸种城市元素的总合之地。有势力的佛寺常常独霸一整个里坊,是洛阳城中最别致的“住区”——如果皇宫的“居民”是“王家”贵胄,佛寺的“居民”则由“僧户”充任,他们都不编入赋税人口,成为帝国社会结构中无法测度的黑洞。虽然同样不免于奴役、流品、政治这些俗套,佛寺和以上几个社区不同,并不算是洛阳城市中清晰界定的一部分,尤其它的“社会成分”最为混杂,是流动性最大的一种,因为僧人可能来自以上的任何等级。
我们将以上这些笼统地称为“洛城人”。“洛城人”,或者就是洛阳广义的“城市居民”,纵然我们已经解释了他们之间显著的差异,谁敢说这些人之间便毫无相同之处?高贵和下贱,顽皮抑或端庄,普遍人性总在看不见的深处彼此勾连。一方面,政治或等级上的差异使得这些人群在社会空间里彼此暌隔;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洛城人共享的城市公共生活,在分歧和孤立之中潜滋暗长,这种
新的时代风尚,就正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掷果潘安”那般,它的情节不被既有的规则设定,却是由嬉笑和喧闹之中破土而出。

▲洛阳的山集雄险秀丽于一身
“繁 荣 ”兼 “混乱”的最后时光
在《幸运的套鞋》中,童话作家安徒生提到一种“魔法套鞋”,可以令你时空穿越。假如,一个人可以穿着这样的套鞋,来到洛阳宽达百步的铜驼街上,极目四顾,你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片农村与城市混杂、蛮荒和文明交织的奇异风景中。路超宽,堪比我们今天的 “世纪大道”,却不甚体面,没有什么光洁的路砖或是文石,倒是满地的黄土,不管刮了风下了雨都够瞧的。由此有了陆机意味深长的道德训诫:“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
在洛阳,一个普通人会首先去哪儿呢?在佛寺传入中国之前,受到严格管制的城市,在功能单一的居住区外主要的公共空间大概只能是“市场”,“城”正对应着“市”,这是坊墙内的世界春光乍泄之处,我们可以邂逅各种洛城人的地方——我们常把古代城市的市场繁荣比拟于今天的城市生活,但洛阳城市的“城”非今天的“市域”,城市的“市”也未必是自由经济里社会交流的象征,这种表面繁荣的生活并非更高级文明形态的雏形。在此意义上,洛阳既是华丽都会,又带着几分土气。
考古学家们对北魏洛阳城坊制度是否严格地遵循了 “方三百步”的标准还有争议,毫无疑问,
这里一定有着各种各样的 “例外”,使得那只是字面上齐整的制度最终显得混乱不堪:有的建筑物独占一个或数个里坊,如有北魏国寺之尊的永宁寺,明河青槐使人宛如置身上苑;有的里坊中却没准罕见人烟,可能遍地都是荒地和野树林,王侯邸苑也未见得就是风流遍地。不过,至少肯定的一点是,有里坊必有围墙,有管制的权力也必有破坏的欲望,有板起的面孔也便有诙谐的调笑,有自命高贵,便也有金枝玉叶肝脑涂地的一天。
“繁荣”兼“混乱”是城市舞台上喜剧和悲剧的合体——“拈花着尘”。
永嘉之乱后,北方本来是南方流亡氏族所不齿的人文沦丧之地,但到了北魏,人物风流却似乎一点也不逊于南朝,以至于江左来人也不禁要叹服于河洛的 “正朔”。上文说的洛阳上商里,就是瓦工才好意思住的不良社区,却有一位周杰伦式的弄潮人物——将军郭文远,满不在乎地住在里内;另有一位陇西人李元谦爱好运用双声语——现代汉语多有双声语,但当时却是一种罕见的文学巨匠才能掌握的技巧。有一次李从郭文远的宅邸前经过,看到门庭典丽,就说:“是谁第宅?过佳!”——“是谁”“第宅”“过佳”都是双声。郭文远的婢女春风闻声从门内走出来说:“郭冠军家。”李元谦说:“凡婢双声!”春风说:“儜奴慢骂!”答来问去,在当时语音中都是两字声母相同,寥寥数语,居然都是“双声”。
一个寻常婢女,也能和文学巨匠在语言才能上相匹敌,可见北朝人文之盛。但是,这同时也不妨碍流氓和武夫们大行其道,那真是一个人情滥汜的年代……无论历史的宿命最终是如何使人悲恸,在故事的高潮,悲喜剧总是混杂在一处的。即使在太平年月,盗寇、马贼、小偷小摸,屡禁不绝,小聪明大才智有了各自的用武之地——华丽的文明之盾也为它自身的粉碎准备了合适的矛。洛阳的名字,除了活在上个春天的记忆中,也记录在盗墓专用工具“洛阳铲”的近代命名里。那些当代“土夫子”们,在继续沿用这种半圆柱形的掘土铁铲开掘至今不绝的北朝遗产时,或许也会偶然回忆起那个年代的技术“进步”。在将军家婢勤学双声的同一时刻,也有道士綦母怀文刻苦钻研灌钢技术,在南方制成“宿铁刀”,可一下劈断30片金属甲片,锋利无比——在洛阳动乱的最后年月,此类发明大概是乱上添乱。
洛阳人刘白堕专事酿酒,他酿的“鹤筋酒”芳香醇美,烈日下曝晒十天也不会变质走味,人喝了就会“醉而经日不醒”。
“醉而经日不醒”——这异乎寻常而至忘情的繁盛不是没有原因。最终,在新的舞台上,无序累积的财富和欲望也燃起了毁灭的熊熊大火。
作者:唐克扬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周怡倩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