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随着张翎新作《劳燕》发表、戴小华新作《忽如归》出版,海外华裔写作者成为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汤亭亭的名字虽然逾越了“华裔”的标签,跻身英美文学当代大家行列,但她也可能是华裔作家中引发最多争议的一位。
本文提示我们换个视角看待她的写作:在那个矛盾尖锐的文化战场上,她尝试打破一些人对华裔的刻板印象,试图借助孔子的遗产,思考美国主流文化的伤痕。
——编者
汤亭亭的名字在美国逾越了华裔作家的狭隘标签,已进入美国文学的经典,当美国高校教师推荐必须阅读的当代文学作家时,汤亭亭和爱丽丝·门罗,菲利普·罗斯,塞林格,托尼·莫里森等一并在列。然而,自汤亭亭于1976年出版《女勇士》起,有关她作品的争议就鲜少终止过。
中国读者也许只读一读内容概要,就可能仓促作结:《女勇士》是在贩卖中国的“奇观”。全书首章《没有名字的女人》写因出轨而被乡人逼迫、投井死去的姑姑,第二章则是叙事者“我”为帮姑姑报仇,赴白虎山学艺,最终发现不过是南柯一梦,之后的章节转到美国:辛苦操持洗衣店的华裔移民,来加州寻夫却最终发疯的小姨等等,如今都仿佛沦为充斥着成见的中国移民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汤亭亭遭遇了之后所有少数族裔作家都遭遇过的质询:你通过渲染“异国情调”,把母国的文化变作西方的傀儡。
有关汤亭亭争议的最高点发生在一次公开座谈中,同样有着亚裔身份的剧作家、批评家赵健秀指责汤亭亭篡改花木兰的故事。《女勇士》的第二章《白虎山学艺》很大程度上是花木兰故事的改写,叙事者是个7岁的小女孩,借由仙鸟的殷勤探看,结识一对武艺非凡的老夫妇,老夫妇对她说:“你能忍受跟随我们生活15年吗? 我们可以训练你成为真正的女勇士!”叙事者选择留下,未给双亲捎只言片语,实在思念家人时只能借助一瓢葫芦窥得双亲的相貌,15年后,她出落成武林高手,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率领一班军队将侵略家乡的敌人杀得片甲不留,事成后退回女装,嫁人生子,深藏功与名。令赵健秀尤其不满的是,故事中汤亭亭将岳母刺字的情节嫁接到花木兰的故事上,15年后,叙事者回到家乡,决定替父征战的前夜,她的父亲在她背上刻下“复仇”字样,他解释说:倘若你死了,暴尸荒野,人们也可以在你的尸体上看到你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赵健秀认定这是在虚假表现中国文化。多年后,面对谭恩美因《喜福会》走红,赵健秀也把类似的苛责投向了谭恩美——你笔下的中国是虚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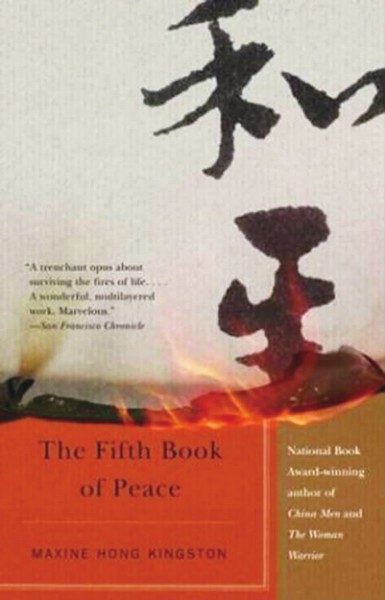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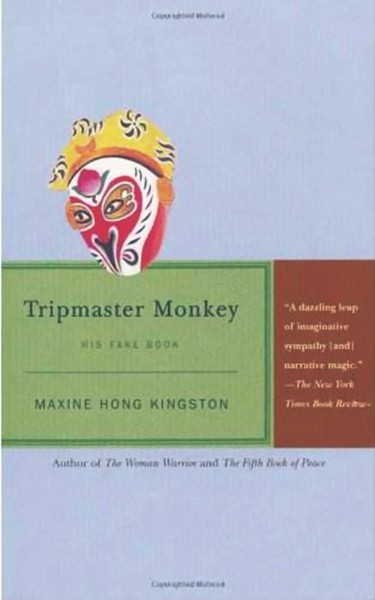
耶鲁大学文学教授艾米·亨格福德在《1945年后的美国文学》课堂里专就这一批评作出回应:“这就好比有人对后现代作家约翰·巴斯说,‘等等,你篡改了奥德赛的故事! 你在作伪!’”在对文学传统采取捍卫态度的读者眼中,传统的“真实”和“纯粹”都影响着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改写即玷污,这或许也是不少中国读者翻开海外华裔文学时连连摇头的原因,他们会叹息:一派胡言。
且不论传统是否应当保持开放的态度,让后世的改写与诠释不断丰富其内涵,我以为更重要的是,看待美国华裔作家,应当保持头脑的清醒:他们所面对的并非是中国的传统,而是美国的主流文化。
汤亭亭曾经很明确地表示:“和所有美国作家一样,我的志愿是写一部能够进入美国主流文化视野的长篇小说。”所谓的美国主流文化视野,长期由白人男性掌控着话语权。在这个意义上,1976年作为华裔作家开篇之作的《女勇士》恰恰是试图创造“原型”,而非固化既有的写作类型。
《女勇士》非常强调话语的重要性,全书交织着两个叙事声音,一是叙事者,二是叙事者的母亲,后者对前者强调:“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故事,你不许告诉其他人。”母亲所讲的就是姑姑投井的故事,她说:“我们说你爸爸只有兄弟,没有姊妹,仿佛让家族蒙羞的她从未来到这世上一般。”可见,《女勇士》的叙事是力图打破禁忌的“话语”,当叙事者选择言说,通过“讲述”,在“话语”中,她重新赋予姑姑生命,让其存在。类似的,在《白虎山学艺》中,故事开场,母亲讲述的就是两百多年前鹤拳的创始人,以及花木兰。这个故事中叙事者的声音不是打破禁忌,而是追随这些传说开启幻想,让自己在梦境中复制这些女勇士的人生履历。汤亭亭对自己的写作有这样的期许——运用想象创造“真实”。这些勇于言说的中国女性形象对中国读者而言稀松平常,但在1970年代的美国却是晴天霹雳。因在那之前,美国文学视野中的华裔女性类型不外乎两种,一是温柔寡言的瓷娃娃,二是心怀叵测的蛇蝎美人,“花木兰”是她为华裔女性正名的“原型”,而非类型。汤亭亭迫切反击的是美国白人男性营造的狭隘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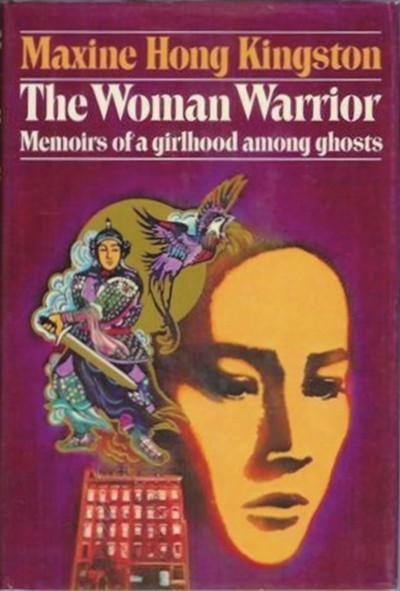
又如,汤亭亭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表面看是运用西游记的故事模版,但实际挑战着美国清教徒长期把持的话语权。她在一次访谈中谈道:“我想让华裔美国人也有一个充分的踏足这片土地的理由。清教徒总说他们来到这里追求自由,然后我就在想,在主流视野中什么是华裔最初来美国的理由? 很遗憾,是为了金矿。”这个刻板印象影响深远,时至今日,美国主流社会仍有人将华裔以及华人视作“过来赚大钱”的类型。于是,汤亭亭决定要给华裔重新寻找一个理由,幸运的是,她在故纸堆中找到,最早一批在旧金山上岸的华裔移民是一百人左右的皮影戏剧团, “他们在世界各地行走——传递孙行者的精神”。当时采访者提醒她,这种孙行者精神迥异于清教徒的苦行传统,汤亭亭回应:“现在我们交融在一起了——苦行的和世俗的,我们可以看看接下来的美国文化会发生什么改变。
后来,当汤亭亭诠释孔子时,她的立场是孔子对于疗补美国主流文化何以可能。美国的文化历史充斥着暴力冲突,汤亭亭曾有一兄弟失踪于越南战场,这段私人经历更让汤亭亭在一个矛盾尖锐的文化场域中,时刻思索非暴力的和平路径。她认为孔子给予她启示:孔子降临于乱世,但他重建秩序、社群、和平以及和谐。他用非暴力的方式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和睦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在《第五和平书》 中,这些中国文化传统为她提供思考美国主流文化疮疤的新视角。
中国学者研究海外华裔文学时常常会感慨,中国形象被扭曲,中华文明遭误解,西方人眼中没有真实的中国。但诚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言:“(中国)永远不会客观地存在,它只是在我们的诸多解释方式当中的一个游移的参照点。”对美国华裔作家而言,中国将是一个永远的镜像,以便打量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