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萨遗址博物馆的彩釉浮雕
在2019年5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联展”的展览中,伊朗15件文物第一次借调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展览实物的方式展现了伊朗的文明历史,同时展出的还有中国和日本的丝绸之路相关文物,中国观众也有了亲密接触亚洲文明和异域文化的机会。2020年冬春之交,我们前往伊朗进行了一次为期5周的环伊朗考察,在伊朗文化遗产旅游部和德黑兰大学师友帮助下,先后考察了17个世界文化遗产和近百个考古遗址及文博机构,走在这些古代遗址上,睹物思人,也回想起一些学界往事。
无论学界还是民间,我们常常以波斯称呼伊朗,伊朗足球被称为“波斯铁骑”、伊朗地毯被称为“波斯地毯”,还有波斯猫、波斯音乐,波斯一词好像就是带着异域风情,让人浮想联翩。实际上,波斯是指以现代伊朗为中心建立的古代国家,一般是阿契美尼德、帕提亚、萨珊三个古代王朝的总称,伊朗国名的由来则是现代的一次更改国名。
我们对于波斯考古美术和宗教文化的认识也是从中国的民国政府时期开始,但当时由于交通道路隔绝,两国忙于各自民族解放事务,也都在“全盘西化”和“托古改制”的思潮中踌躇,并没有太多直接交集。
作为文化复兴和民族精神再发现的重要一环,恺加王朝(1796—1925)的纳赛尔·丁·沙阿见证了伊朗考古研究的开端,法国考古学成了伊朗学习的重要对象。伊朗自身的考古学开启也是在法国Marcel-Auguste Dieulafoy与Jane Dieulafoy夫妇组织的苏萨发掘调查开始,陆续在这里发现了阿契美尼德之前的埃兰文化等,Roman Girshman在二战后的继续发掘,明确了公元前3000年之后的文化地层,苏萨也成为了伊朗考古的标准地层遗迹。
民国时期,尽管两国之间还未正式建交,但已经有了一些关于伊朗文化的译介,我们可以从江绍原的翻译事例来窥探。从1932年2月3日开始,《世界日报》连载江绍原博士翻译的《古波斯宗教》[Dr. Edvard Lehmann (1862—1930),原著收录于Lehrbuch der Religionsgeschichte(1897,Freiburg)节选翻译]一书,里面介绍了波斯的宗教文化历史,这也是当时世界各国的宗教学通用教材。曾经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狂飙突进的江绍原在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以比较宗教学研究为己任,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任教,也与鲁迅等人交好。
在序言中,江绍原还提到:“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第四册古代中国于伊斯兰之交通,关于我国文籍所载波斯宗教情形及祆教在华的出现和消减,我现在无暇详考。张所云陈圆庵《火祆教入中国考》专书,尚未见。”
对于中国古籍文献中涉及波斯宗教的研究,陈垣除《火祆教入中国考》,也陆续写出《摩尼教入华考》《回回教入华史略》等专文,推动了对于波斯宗教文化的认识。但受困于时代限制,当时国内学人很难走进丝绸之路上的国家进行实地考证。
1935年驻日本公使蒋作宾给民国政府发来电报信息,称波斯在3月21日通告全世界,已经改名伊朗:“本国国名将由波斯改为伊朗,以希腊文Persia系由Pars而来,即本国南部之旧省会也,若以此而代国名,似欠合理,且自昔迄今,本国即以伊朗自称。”(北京市档案馆J1-1-144)当时外交部长汪兆铭迅速通电给全国各级政府改名之事,伊朗的国名从此走进中国。
这时期的伊朗在经历了1925年的政变后,新成立的巴列维王朝(1925—1979)继续推进西化政策。1935年,伊朗政府也委托法国学者主持设计并建立了德黑兰考古博物馆,以考古发掘物为基础进行科学馆藏陈列,正式展出了伊朗各地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以考古发现构筑了伊朗的通史陈列。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展览的文物也来自这里,我们到来时这里的馆长Dr. Jebrael Nokandeh已经对中国很熟悉,在这座仿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拉克泰西封宫殿建筑中,馆长给我们讲述了很多他在中国的见闻,看到的受伊朗古代文化影响的文物古迹,对于中国的认识似乎在重新开始。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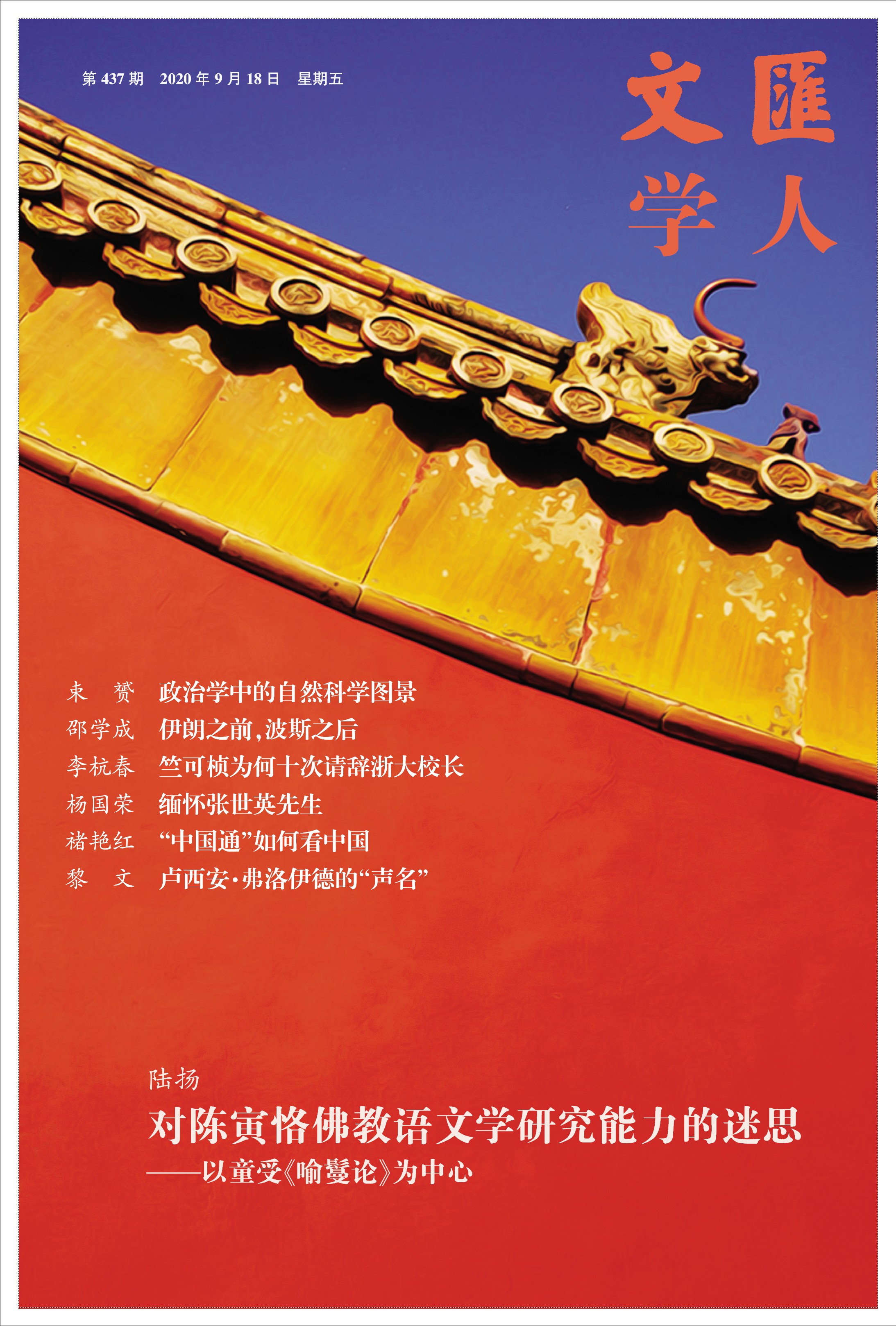
作者:邵学成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