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在《弃猫》的结尾部分归纳道:“换言之,我们只不过是落在广袤大地上无数雨滴中无名的一滴。虽为固有,却可替换。然而,一滴雨水,有一滴雨水的思维,有一滴雨水的历史,有将那历史继承下去的职责。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即使那滴雨水将被大地轻易地吸收,失去个体的轮廓,被某种集合性的东西置换而消失。不,反而应该这样说,正因为它将被某种集合性的东西所置换。”村上明确表示:自己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个体,但有继承历史的职责。而这一点,经过四十年的写作实践,已经清晰地内化为村上身为作家的使命。村上对此抱有清晰的认识。在近期的两次欧洲之行中,他也有意识地追寻历史,正视“世界的黑暗”。
2019年5月,村上受邀访问了波兰。村上在游记《波兰》(Skyward,JAL 2019年9月)中写了华沙数十年不遇的春寒冷雨,以及扑面而来的绿意,还在遗迹中追溯了历史。“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在帕德格勒泽(Podgorze)的高墙内度过了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高墙内的犹太人被逐批地全都送进了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集中营,大多数在那里失去了生命。他们被运走前集合的广场至今尚存,名为Plac Bohaterów Gatta。”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游记登载于日本航空的机内杂志上。村上在波兰的所见所感,借助迅疾的交通工具,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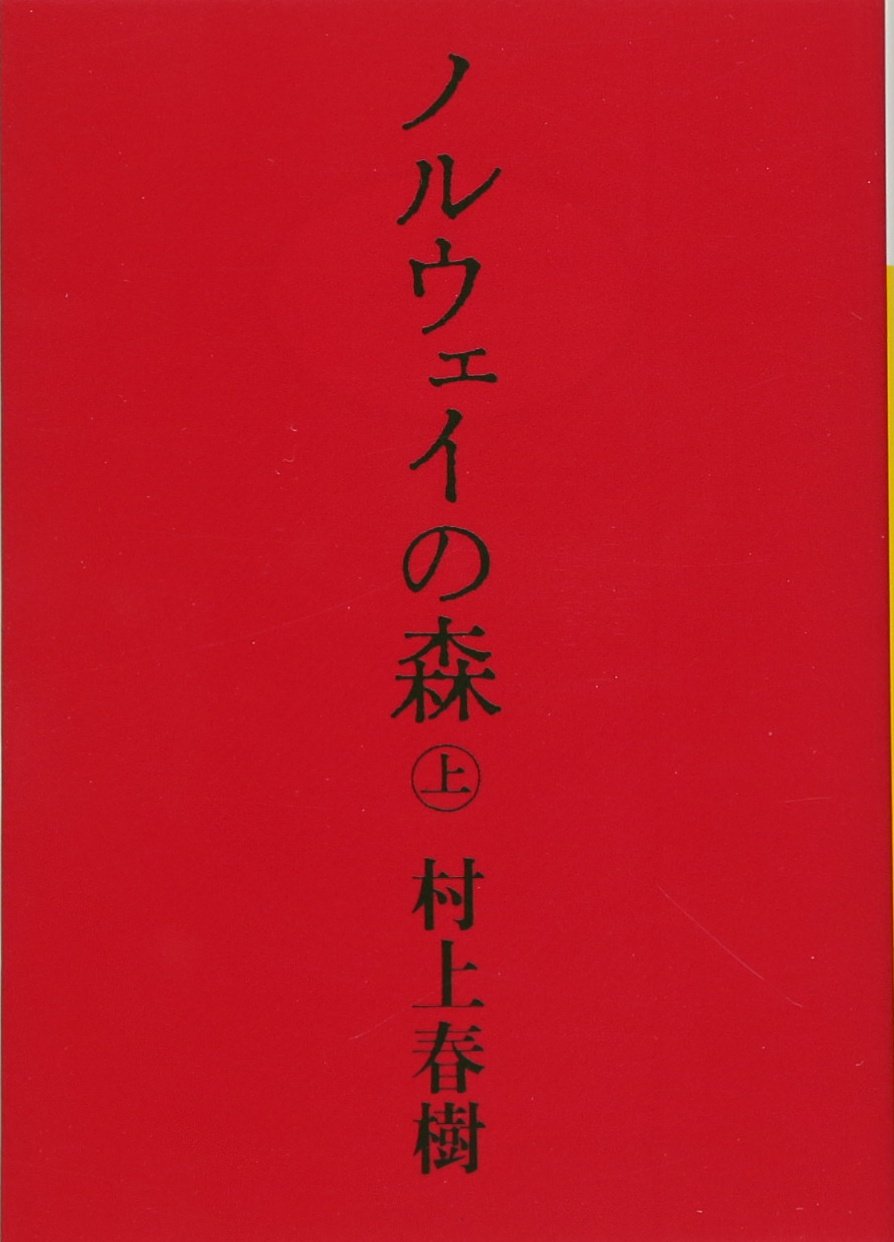
2019年7月,村上受邀去德国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在游记《处处皆是狂想 überall Wahn 拜罗伊特日记》(《文艺春秋》2019年10月号)中,他详细记录了访德期间的观剧感受。7月26日,村上在瓦格纳节日剧场观看了歌剧《罗恩格林》,次日观看了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在《纽伦堡的名歌手》开演之前,他在纪念品商店购买了两件T恤,其中一件胸前印着歌剧中的台词“Wahn! Wahn! überall Wahn!(狂想!狂想!处处皆是狂想!)”有别于《罗恩格林》相对传统的演出,《纽伦堡的名歌手》做好“招致普通观众反感”的心理准备,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村上认为瓦格纳作品之所以能保持其生命力,原因之一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积极采用新的演出方式及手法,并“继承社会、文化的责任”。新版《纽伦堡的名歌手》的舞台场景在传统歌剧中的16世纪的纽伦堡、作为剧中剧的19世纪后半叶理查德·瓦格纳的书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行军事审判的纽伦堡之间切换。歌剧的演出十分精彩,“然而听众无法仅仅沉醉于歌曲之中,因为舞台忽然转为纽伦堡审判的法庭,再次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代。审判官背后挂着法、英、美、苏四国的巨大国旗,舞台的角落里站着美军宪兵。而歌手必须站在证人席上演唱。”显然,《纽伦堡的名歌手》中关于战争的再创作,继承了“社会、文化的责任”,给村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村上在《长篇访谈 犹如黑暗之中的灯笼》(《文学界》2019年9月号)中与访谈者汤川丰、小山铁郎进行过一段对话。
村上 从主人公在居住地挖出骑士团长开始,故事急转直下,那是一种把过去拉出来,使之复苏的故事。
——您说过,骑士团长或许是“历史性的联系”“来自过去的信使”。
村上 不管怎样深挖洞穴,加以隐藏,该出来时还会出来。我们背负着历史而生活,不管怎样隐藏,历史终将显露出来。我认为,历史是我们背负的,集体性的记忆。
——您是二战结束后不久,1949年(昭和24年)出生的吧。
村上 在那个时代,因为国家的逻辑而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人杀人的鲜活记忆还残留在空气之中。我现在仍然强烈地持有战争并非虚构的意识。我们以为是坚固的地面,其实或许只是柔然的泥土。
村上讲述的“历史是我们背负的,集体性的记忆”,恰如其分地点明了自《奇鸟行状录》到近作《刺杀骑士团长》,贯穿其中并越来越明晰的作家的职责。村上在这篇访谈中强调说,“善恶的观念,在地上是泾渭分明的。可是下到无意识的世界,其界限就越来越模糊。越过某条界限,变得无法分辨。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就算身处那样黑漆漆的暗处,还是必须像保护洞穴中的灯笼一样,坚守人的自然具备的方向性。”这句话呼应了村上的获奖演说,进一步阐明了他身为作家的职责:以文学之光,照亮存在于世界各处的黑暗。
作者:邹波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