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先生新近出版的《回归语文学》一书,收录了近些年他关于语文学的九篇文章,对西方关于“回归语文学”的讨论进行了综述评议,结合作者对藏传佛教文献的研究分享了语文学的经验体会,提出了几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引发了热烈的赞同和讨论。这里不揣谫陋,结合中国古典文献学,从中西比较的角度,也简单谈几点初步的理解。
(1)
《回归语文学》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引人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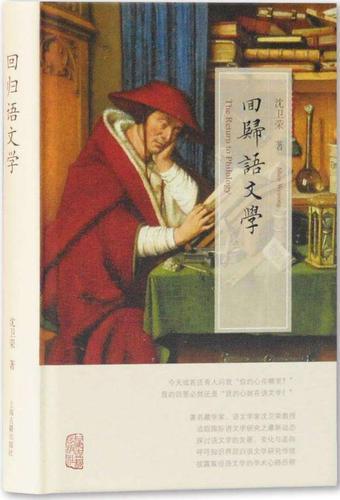
比如前言提到,德国语文学大家恩斯特·施泰因克尔纳(Ernst Steinkellner)在2008年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开幕式上的报告《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有关方法论的几点意见》:“出人意料的是,Steinkellner先生没有多谈语文学和他所从事的专业研究的关系,却大谈了一通语文学方法对于实现人类和平、和谐和幸福的意义。”

德国语文学大家恩斯特·施泰因克尔纳
比如第二章说道:“语文学和哲学(或者思想、理论)本来是人类智识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不可或缺。然而自现代人文科学于19世纪末形成以来,语文学和理论就成了一对天生的冤家,二者之间似乎有着解不开的瑜亮情结。“
《文汇学人》2019年8月2日所刊李婵娜《为什么必须回归语文学》,是一篇书评。文末说道:“期盼在该书的启发下,未来的中国研究,可以继承中国学术固有的‘朴学’之传统,兼之以语文学之方法和精神。”
施泰因克尔纳为何要在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大谈“语文学方法对于实现人类和平、和谐和幸福的意义”?语文学和理论如何“就成了一对天生的冤家”?中国的朴学传统与西方的语文学路径有何异同?“语文学的精神”究竟是什么?
(2)
什么是语文学?简单说来,语文学是穿过时空隔阂了解他者的一种方法。
比如西方人要了解中国,他们可以从自身的世界观出发,从其对外国、对东方的一般认识出发,通过思考,来达成自己的了解。这条路直捷好走,但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他们的了解往往肤浅隔膜,甚至不通。
另外有一条路相对迂曲难行:从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开始,学习中国文化,跟中国人相处,学习像中国人那样说话、行事、思考问题,长期周旋,最终达成自己的了解。对于这些几乎听不出口音的外国人,我们有一个称呼叫“中国通”。我们觉得,他们的了解,才是真了解。这条路,就是语文学之路。
穿过空间隔阂如此,穿过时间隔阂亦如此。东西方是不同的世界,古代和现代也是不同的世界。通过学习古代的语言文字以达成对古代的了解,就是语文学。西方所谓语文学,本来指的就是这个。穿过空间隔阂去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的所谓语文学路径,是近现代的引申用法。
语文学,英语是philology,源自古希腊语,由“爱”(philo)和“语文”(logos)构成。可资比较者,哲学,philosophy,由“爱”(philo)和“智慧”(sophia)构成。
就穿过时空隔阂了解他者而言,“爱语文”和“爱智慧”是两条不同的路径。
关于爱智慧这条路径,《吕氏春秋·察今》有说:“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
“近”和“今”,这藉以知“远”、藉以知“古”的东西,其实就是以观察者生活经验为中心的知识作为基础概括归纳出的统括性、一般性的认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理论”。
以近知远,以今知古,由所见推想所不见,其实是从一般到特殊,就是理论的具体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己度人,以今例古。
(3)
中国和西方都有十分悠久的语文学传统,只不过在称名上纷然杂出,需略加疏解。
语文学在中国传统学问系统中或称“小学”。小学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教人识文断字,所以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统称“小学”。语文学在西方学术史上或称“文法学”。这里的“文法”不是现代汉语所谓“语法”,而是囊括了文字、词汇、音韵和语法所有关于古典语文的知识。中世纪欧洲有所谓“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教授古典语文即拉丁文,此名至今英国仍在沿用。教育机构与学问门类同名互指,东西对照,相映成趣。
语文学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相当于文献学。“文献学”一词是近代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之时为对译philology(语文学)一词而新造的词语。其中“文献”二字来自中国典籍。《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文”是书面文本,“献”是口头记述。徵文考献,以明古事,正是philology的要旨。杰罗姆·麦根《现代校勘学批判》提到,“全面语文学”(philologia perennis)是“古代学”(Alterthumswissenschaft, science of antiquity)的另一个名字(《西方校勘学论著选》,248页),亦作如是观。
5世纪初,古罗马作家马尔提亚努斯·凯佩拉(Martianus Capella)撰写了题为《墨丘利与菲洛勒吉娅的婚礼》(De nuptiis Mercurii et Philologiae)的寓言体学术论著。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Hermes),是信息和交流之神。“阐释学”(Hermeneutics)的语源就是“赫尔墨斯”(Hermes)。菲洛勒吉娅即philology,“语文学”。在两者的婚礼上,文法、修辞、逻辑、算术、音乐、几何和天文,亦即所谓“自由七艺”,作为伴娘出场。
揆其寓意:要想对古代文献进行正确阐释,首先需要熟悉作者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同时还要尽可能了解作者所知晓的以七艺为代表的所有知识。
这大致相当于所谓张之洞《书目答问》所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不过张之洞这句话,在强调语文学路径的同时,还隐含着另外一重意思:从理论入手的“以今知古”式路径值得怀疑。

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是信息和交流之神。图为卢浮宫所藏意大利雕塑家博洛尼亚的著名青铜雕塑——飞翔的墨丘利
(4)
关于典籍阐释,在中国学术史和西方学术史上,都曾有过理论与语文学的对立。语文学是从研究对象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入手,着眼于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体贴入微地理解研究对象的具体表述。理论则是从研究者的知识体系出发,将其一般性的认识适用于特殊的研究对象,从而达成理解。
中国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理论与语文学的斗争。
今文经学用“大一统”、“天人合一”以及阴阳五行等理论来解释经文文本中所谓“微言大义”,其实质是用当前理论对古代文本进行过度阐释。
古文经学因为其文本所用文字古奥,所以首先要“重训诂”,从经典文本语言文字在古代的本来含义出发来解释经文,也就是语文学的方法。
与中国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差可比拟的是,西方学术史上有所谓寓意阐释(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和字面义阐释(literal interpretation)的对立。
寓意阐释,亦见于在对西方古典文本的解释,但最典型的,集中表现在对《圣经》文本的解释中。在《圣经》解释的历史上,寓意解经曾盛行一时。解经者在经文字面意义之外,根据后世“预表论”等神学理论,阐发、构建其深层的寓意。这“寓意”与中国今文经学所谓“微言大义”差可比拟。
用理论阐发出来的“经义”,在中国和西方往往都发挥着指导生活的现实功用。汉代董仲舒主张以儒家经义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称作“经义决狱”。基督教以《圣经》作为指导信徒生活的最高准则,也曾致力于阐释经文字面意义之外的神学意义,以扩大生活指导的覆盖面。
对于古代文本的解读诠释,中国和西方都曾上演过“回归语文学”的故事。
《圣经》文本有些地方存在寓意,可以从寓意角度加以阐释。历史上寓意解经的问题是无限扩大适用范围,从某种理论出发,生搬硬套,牵强附会。随着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寓意解经已经淡出,字面义阐释恢复了主导地位。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讨论明清之际的学术转向:不再从“宋代新儒学力图建立的涵盖全部人类经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古典,而是通过“训诂考证”“还原古典原义”(21页)。所转向的这个philology(语文学),清初亦称“汉学”(江藩《汉学师承记》)。从宋学到汉学,显而易见,在朴学家看来,这个“语文学转向”(turn)是一种“回归”(return)。
(5)
1983年,研究近现代文学的美国文学批评家保罗·德曼(1919-1983)也喊出了“回归语文学”的响亮口号,影响颇广。
面对近现代文本,没有时空隔阂,一般说来没有“通训诂”的必要,也就没有多少语文学的用武之地,应该是文学理论的一统天下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文学批评需要根据在人类经验和历史的宏大背景下形成的关于文学的总体认识,来评鉴具体作品的优劣得失。这关于文学的总体认识,是形形色色的理论,比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
理论是一副眼镜,能让批评者从文本中看出特别的意义。但这眼镜是有色的,批评者在文本中所看到的东西,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来自文本,何种程度上来自眼镜,终究难免让人有所犹疑。
有鉴于此,耶鲁大学解构主义学派的保罗·德曼撰有一篇颇为著名的文章,题为《对理论的抵抗》。这个题目后来成为德曼相关论文集的书名。书中有一篇题曰《回归语文学》:在宣布抵抗的同时,指出了突围的方向。


萨义德(上)和德曼(下)都主张“回归语文学”,但是他们对“语文学”的理解并不一致。如果说德曼的“回归语文学”,是对文学理论的抵抗,那么萨义德的“回归语文学”,可以说是对东方主义中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抵抗。说到根本上,这意识形态也是理论。
德曼认为,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应该从历史学和美学出发,而是应该从语言学出发;研究者首先要讨论的,不是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而是这意义和价值具体是如何从文本中产生的、又是如何被接受的。只有做到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can be said to come into being)。
德曼提出的这个从语言学出发的理论,与此前的理论有本质不同。用德曼在《回归语文学》一文中的话来说:“此番走向理论,是回归语文学。”(the turn to theory is a return to philology)只有从理论与语文学相对立的格局出发,才能准确理解这一句的吊诡之处。而这“回归语文学”的“理论”,骨子里仍然是“对理论的抵抗”。
德曼所回归的“语文学”其实是语言学,准确来讲,是语法学和修辞学。不过为了点题,德曼宁愿用古意盎然的“三科”(trivium)——即“七艺”中的文法、逻辑、修辞——来概括,同时将逻辑归入文法,故名三而实二。语法(包括词义)分析相对简单;构成难点的,是所谓“修辞解读”。 德曼说:“修辞解读,对于它们所鼓吹的解读,同样抱持着回避和抵抗的态度。这种对理论的抵抗无可克服,因为这理论本身就是抵抗。”
德曼是文学理论家,始终都是。其所谓“语文学”,与传统语文学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其“回归语文学”的主张,仍然闪耀着语文学精神的光芒。
(6)
德曼《回归语文学》发表后二十年,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发表了同题论文。
爱德华·萨义德,美国阿拉伯裔文学理论家,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因《东方主义》(1978)一书而蜚声学界。所谓“东方主义”(或译“东方学”),是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对北非、中东和亚洲等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和认知。在萨义德看来,这些研究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东方学的著作都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
2003年,在萨义德罹患癌症去世之前,完成了《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其中核心篇目之一就是《回归语文学》。从书名不难看出,萨义德关于“回归语文学”的讨论与政治密切相关,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一脉相承。
萨义德和德曼都主张“回归语文学”,但是他们对“语文学”的理解并不一致。萨义德对德曼将文本从其生成历史中剥离出来仅从语言学上加以分析的做法进行了批判,认为“语文学”是“对生活于历史之中的人的言语和修辞进行仔细、耐心的考察,念兹在兹,终身以之”。
如果说德曼的“回归语文学”,是对文学理论的抵抗,那么萨义德的“回归语文学”,可以说是对东方主义中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抵抗。说到根本上,这意识形态也是理论。
人类学对于各种文化的研究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聚焦于各种文化的相同点;另一个是相对主义(Relativism),聚焦于各种文化的不同点。
研究其他文化,如果从普遍主义出发,就是将研究者的一般性认识适用于特殊对象,也就是通过理论来了解他者。而这理论,必然是以自身文化作为标准和中心,藉以想象和概括其他文化。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乃基于华夏中心论;萨义德所揭示的当代西方的“东方主义”,乃基于欧洲中心论。二者虽有中西古今之异,但其内在逻辑无疑是一样的。
如果从相对主义出发,首先是学习该其他文化的语言文字,通过语文学来掌握对方知识体系的方方面面,最终达成全面的了解。简单来说,相对主义的宗旨是:“认真地将他者当作他者,而不是自我的一个异域风情的、低劣的,或者未达标准的版本。”(Foley, W.A.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p.175)埃米尔·卡齐姆(Emere Kazim)去年发表了《萨义德的哲学遗产:相对主义和积极抵抗》(The Philosophical Legacy of Said: Relativism and Positive Resistance, Maydan Politics & Society, Dec. 4. 2018)一文,这个题目反映了“萨义德主义”(Saidism)的关键词。尽管卡齐姆的态度不无保留 ,但是众多学者从相对主义的角度解读萨义德却是不争的事实。
德曼所做的,是举着解构主义旗帜的文学批评;萨义德所做的,是举着相对主义旗帜的文化批评,其间的差异显而易见。然而他们都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发表题为“回归语文学”的文章。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与语文学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就像许多直奔主题而又不及细说的绝笔文章一样,这两篇同题文章留下了不小的讨论空间,吸引着许多人撰文讨论。我们认为,他们之所以可以共用一个题目,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对理论的抵抗,都是对先入之见的警惕,坚持从语言文字出发,对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进行深入细致的体认。
(7)
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2008年北京举办的国际藏学研讨会开幕式上,施泰因克尔纳做了题为《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的主题演讲,他没有讲文本考证,而是“大谈语文学方法对于实现人类和平、和谐和幸福的意义”。乍一看,这颇令人意外;但细一想,这不仅合情合理,甚至可以说极为应景切题。
德曼的“语文学”和萨义德的“语文学”畛域攸分。施泰因克尔纳显然是和萨义德站在一起的,其语文学路径的上空,飘扬着相对主义的旗帜。
藏学文献固然有许多是古代文本,但在西方学者看来,它们首先是来自其他文化的文本。欧洲无疑是当前具有较高威望的优势文化,作者自觉地排斥欧洲中心主义,抵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从语言文字出发对藏学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体认,就是认真地将西藏当作西藏,而不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异域风情的、低劣的,或者未达标准的版本,从而达成对东方的真正理解。这当然可以说具有“实现人类和平、和谐和幸福的意义”。尤其是发言地点是在北京,听众主要是东方学者,西方学者从这个角度揭示语文学的意义,可谓即景生情,着手成春。
(8)
理论聚焦于共性,语文学聚集于个性。两者互相对立,而又彼此相联。
西方近代学术史上,理论家与语文学家曾经互嘲互谑,其核心梗,是将学问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契合度和适用性,比作男女之间的浪漫约会。理论从普遍主义出发,聚焦于共性,适用面广,但契合度低,所以被谑为“约会多多,却无衣可穿”(lots of dates, but nothing to wear)。语文学从相对主义出发,聚焦于个性,契合度高,但适用面窄。极端一点来讲,语文学家的知识学问往往都是围绕着特定研究对象的,让其转而他适,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被谑为“严妆盛服,却无处可去”(all dressed up, but nowhere to go)(Sheldon Pollock, “Future Philology? The Fate of a Soft Science in a Hard World”, Critical Inquiry, Vol.35, No.4, 2009, p.947)。
在具体交流和认知的过程中,理论和语文学两种方法彼此相联。按照西方阐释学的说法,自我对他者的认识,都是从自我与他者的相同之处开始,从以己度人开始。随着阐释活动的深入,或者说阐释循环的扩大,不断发现并修正自己不正确的先入之见,与此同时,不断增加自己想象力和同情理解的能力。
理论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局限和问题,特别是其中的预设立场和意识形态,值得警惕。所谓对理论的抵抗,着眼点即在于此。
(9)
“语文学”一语涵盖范围也比较广,包括古籍文本校释学、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等等,不一而足。也就是说,传统语文学后来分化为多个现代学科。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现代人文学科被遗忘了的源头:语文学》(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2014)开篇引用了那句著名的格言“狐狸知道许多事情,刺猬知道一件大事”,用其中的“一”和“多”来引出语文学与现代人文学科之间的一源多流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特纳并没有论及狐狸所知和刺猬所知的本质不同。

狐狸和刺猬这个比喻源出古希腊阿尔齐洛科斯,因以赛亚·伯林(上)的引用阐发而广为人知
狐狸和刺猬这个比喻源出古希腊阿尔齐洛科斯(Archilochus),因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引用阐发而广为人知。伯林认为,作家和思想家可以分为具有深刻差异的两类。一类是刺猬型:在他们看来,万事万物,共理条贯,可以执一以应万,故而“知道一件大事”即可。另一类是狐狸型:在他们看来,事物各有其理,往往彼此龃龉,需要逐一把握,因而“知道许多事情”。对于这两类,伯林是有倾向的,他更倾向于狐狸。人们常举的典型,马克思是刺猬,孔夫子是狐狸。
按照伯林的阐发,从普遍主义出发,聚焦于共性的理论家,是刺猬;从相对主义出发,聚焦于个性的语文学家,是狐狸。
卡尔·莱尔斯《古典语文学家十诫》第四诫是“不可妄称方法之名”,如今看来,这多少有点“抵抗理论”的意味。
我曾译介西方校勘学,于是有人向我当面笑言挑战,说请举出一个例子,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校勘方法解决不了,只有西方校勘学方法可以解决。还真不知该从何说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真正的语文学家或者说文献学家,都强调与研究对象的熟悉无间。这需要天长月久的功夫,而不是什么锦囊方法。
比勒尔《文法学家的技艺》:“如果说古代整理者在对校方法上有所欠缺,但他们却熟悉作者的语言,这一点,即使是当代最伟大的学者也无法望其项背;用A·E·豪斯曼的话来说:‘他们用自己的骨髓来理解作者,因为他们与作者有着相同的骨髓。’”(《西方校勘学论著选》,113页注)
要熟悉古代语言文字,熟悉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学者常说“寝馈于斯”“浸淫其间”,这与萨义德所理解的语文学:“念兹在兹,终身以之”(a lifelong attentiveness)正可相照。
唯有如此的投入和专注,才能抵达陈寅恪所说的“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中国的朴学与西方的语文学在细处容或不同,但在总体精神上是一致的。
尼采曾游走于“爱语文”和“爱智慧”两途。早年从事语文学,曾因语文学家偏狭和迂阔而痛心疾首(《我们语文学家》)。后来致力于哲学,1886年为其《曙光》一书迟到的前言(1881年第一版没有前言,1886年第二版才补上)略有所辩,对自己的语文学出身倒有一番十分准确的评述,特别是拈出的一个“慢”字,尤为恰切。在目前人文社科项目大干快上、计日程功的火热形势下,尼采的这一番话倒不失为一剂清凉散:
语文学是这样一门令人肃然起敬的技艺,它要求从事者首先要做到——走到一边,从容不迫,变得静默和缓慢——这是一门施之于语言文字的金匠般的从容技艺:这门手艺必须慢慢从事,细细完成,不慢,不能成其事。故而现在语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它具有最高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在当前这样一个“干活儿”的时代:不得体不合理地慌张,如此急切地要立即“将事做完”——对书也是如此,无论是新还是旧。而语文学本身,却不是如此匆忙地要“将事做完”。它教人如何读好,也就是说,从容地,深入地,专注地,审慎地,心有所思,胸无窒碍,用灵活的指和眼。
吴金华先生常说,干我们这一行,就是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此言虽浅,深意在焉。
作者:苏杰(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
编辑:于颖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