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了行业和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标志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重要历史节点。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如今,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如何留住工业文明的历史乡愁?如何加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记者就此专访了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教授。 ——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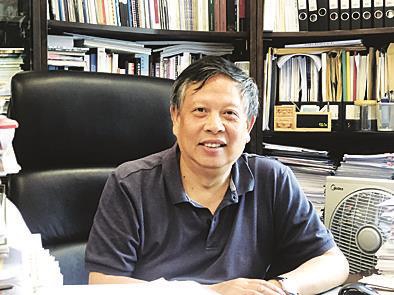
“最小干预原则”在工业遗产保护中不一定总是成立
文汇报:早在19世纪末期,英国就出现了 “工业考古学”。1978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在瑞典成立。工业遗产的价值是如何被认识的?
伍江:工业文化遗产的历史离我们很近,许多厂房仍在使用中,人们很难看到它的历史价值。直到20世纪末的欧洲,大量重要的工业基地被荒废,迫切需要转型,许多工厂用地因此被卖出去,进行房地产开发。这时人们才发现,如果照这种势头,工业遗产的消失速度非常快。今天,距离我们更远的农业文明,甚至狩猎采集文明,都能找到遗迹。工业文明如果它的物质载体消失了,以后的人根本无法想象。于是,全球范围内开始有学者展开工业文化遗产的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全球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ICCH),后来还有20世纪遗产保护研究会,把工业看作是20世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成为全球共识。
文汇报:《世界遗产公约》在定义“文化遗产”时,提到了历史、科学、艺术三大价值,这对于工业文化遗产也同样适用吗?
伍江: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世界文化遗产的三大价值在大部分工业遗产里很难完全“对号入座”。首先,工业遗产的科学价值需要专门研究。比如说,工业文明中有各种不同的工业生产方式,怎么确定哪个是最重要的代表?是最大的,最早的,还是最美观的,最有名的?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历史价值也难以判断,如果说第一个“××厂”还比较容易找到,但第二个、第三个要不要保护?此外,工业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也很难被广泛接受,因为它的建造几乎都是以实用为目的,缺乏非功利的审美考量。除了少部分艺术家或许能够欣赏,一般的人会觉得那些大烟囱那么丑,为什么要留着?
文汇报:工业遗产也不是冰冷的钢铁和砖石,如何唤醒其活的灵魂?
伍江:若是将原先适用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直接套用到工业遗产上,将会带来巨大的冲突。文化遗产保护要“原汁原味”,文物价值是碰不得的。但在工业遗产的问题上,几乎没有人会说工业遗产必须原封不动保留。
工业遗产与一般的世界文化遗产最大区别就是,体量大、占的资源多。比如德国鲁尔工业区打造成工业公园,但这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如果一切都要原封不动的保护,这意味着整个地球的空间资源都没办法进行再生产。针对大部分工业遗产,学界提出将它重新激活,保留躯壳,赋予它新的价值,这可能是最好的保护方式。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那些争论不休的原则,在这里可以放弃一部分,大胆去做。比如,“最小干预原则”在工业遗产中就不一定总是成立。像“一大会址”里面,可能一个茶杯都非常重要。但对于工厂来说,只要空间结构特征和生产线里标志性的东西还在,就可以了。因此,在尽可能地保护工业遗产,以及重要的工业文化信息的基础上,你完全可以根据现在需要的功能,开创性地使用它。
“转型”不能随心所欲,要看是不是城市想要的
文汇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纷纷兴起了工业遗产的“艺术转型”。旧厂房为何会与艺术家结缘?
伍江:世界范围内那么多荒废的工厂,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土地资源完全交给房地产业,最有可能的就是推翻重建。但问题是,我们不希望它们完全消失,那么房地产开发的这套机制就不宜全部引入。由于租金低,这些荒废的工厂吸引了许多艺术家的到来——因为他们要空间,又付不起高昂的租金。
最早,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纽约曼哈顿SOHO区曾经是美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但随着20世纪纽约的金融化、现代化,工厂外迁使得这片区域闲置。艺术家喜欢这里地段好、建筑空间大。他们把这些工业建筑稍加改造后当作自己的艺术工作室和生活场所。开始没有人管、不收租金。但随着经济回温,许多原厂主有机会可以把这些厂房卖掉,他们得把这些“非法占据”的艺术家给赶走。为此,全纽约的艺术家就要保护这些工业遗产。当然,这个“保护”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低成本的使用,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历史。当时,他们的诉求得到了正面的回应。因为这些艺术家的存在确实是有利于工业文化遗产的再利用。所以,一个传统的工业生产空间就很自然地转化为现代创意产业的空间,工业厂房既是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也是新兴产业的承载体,两者就合二为一了。
文汇报:工业遗产的蝶变,证明它们可以是城市的文化富矿。唤醒“沉睡”的资源,同样的故事在中国是怎么上演的?
伍江: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的上海,大量的工业用地转化为商业用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但一些项目在开发过程中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并就此搁浅。最后,也是以很低的价钱暂时外租作为临时用途,这时大量的艺术家开始进驻,除了价格便宜外,他们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美国艺术家都喜欢在厂房,为什么我不可以呢?原身为上海春明粗纺厂的M50创意园就是这样兴起的。
文汇报:上海春明粗纺厂从本世纪初开始向艺术创意园区转型。而从2003年到2008年,您时任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能否为我们介绍下当时这些工业建筑改造的具体规划情况?
伍江:我03年进入市规划局,直接参与这一讨论。我们当时就提出,这个事情本质上是不合法的,因为土地功能转换必须经过“招拍挂”。但这样的话,哪里还有什么创意产业?哪里还有什么艺术家?他们根本做不起。所以当时打了一个“擦边球”,我们提出“三不”:不改变土地的规划性质,它还是工业用地;不改变土地上的房屋结构;不改变房子的权属关系。但是鼓励重新利用,把新的功能引进来。到今天为止,这还是有争议的,现在你开画廊做艺术产业,大家还能接受,但开咖啡馆开饭店,大家就好像很难接受。
其实,工业遗产的保护本身就意味着它不能“随心所欲”,把土地看作是一张白纸来进行房地产开发,它有许多附加要求,这些都与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是冲突的。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再来思考在这些旧厂房中生长出来的文化产业、创意产业,乃至于餐饮行业,到底是不是这座城市想要的。如果是想要的,那就说明是我们现在的政策有问题,应该调整政策。这是我和当时上海大部分决策者的观点。也正因为这样,上海在工业遗产再利用上的实践,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05年前后,上海已经有了100个左右的创意产业园区,其中85%以上是旧工业厂房的再利用。也有新造的,但都不成功,艺术家不愿意进去,反而是旧厂房改造的都成功了。

黄浦江 潘思同(1904-1980)1962年作
油罐或变剧场或成住宅,关键是要留住“乡愁”
文汇报:从政策方向来看,《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支持利用国家工业遗产资源,开发工业旅游项目,建设工业文化产业园区、特色小镇(街区)、创新创业基地等。上海在工业遗产建筑再利用方面利用率较高,但也有学者认为,利用类型过于单一化。对此,您怎么看?
伍江:确实,你很难想象上海所有的工厂全部都变成美术馆。还是要开动脑筋,把各种各样的新功能加进去。我个人认为什么样的新功能都可以加进去,但前提是你要认识到这里是上海历史上重要的工业发展的记忆,必须留住。在这个前提下,就需要寻找既可以保护它,又能够跟你植入的新功能相容的交点,才有可能让它活在当下,活在未来。比如,我们的油罐可以变成一个剧场,事实上国外的油罐变成住宅的也有。
最近我去青岛考察四方机车厂,它曾经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造火车的地方,现在也是主要的高铁基地。旧址上都是100年前的厂房,怎么办?他们有了一个很好的方案,打算在旧建筑之间造一些跟工厂的功能转型直接相关的新建筑。比如说,有些原来的厂房,被改造成高铁的研究所和展示厅。还有一部分经过改造成了服务于附近社区的公共设施,比如小学、中学、幼儿园,还有菜场等等。与此类似,在上海,我们现在也在讨论,能不能最大可能地把当年工厂的那些建筑、生产的工艺特点,最大程度的保留下来,让后人还能够感受到当年这里的样子,比如当年的上海第一钢铁厂是什么样子。同时又把新的开发融进来,里面不乏有大楼有办公,有新的文化功能,我认为这可能成为上海一个新的亮点。
文汇报:对工业遗产的利用不只是卖情怀、卖文化,您所要强调的是,在赋予工业遗存当代价值的同时,也要保留当时的社区记忆,让人们望得见乡愁。
伍江:是的。其实所谓的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保护,不仅仅是我们学术界讨论的事情,它事关每一个人。当时我在市规划局的时候,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建议信,有很多专业的建筑师、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投诉,说哪哪被破坏了。但令我触动很大的是一位杨树浦电厂的工人,他说你们不能把工厂的大烟囱拆掉,拆了我们的记忆就没了。他说我已经退休了,烟囱现在也不用了,但是它是我们所有杨树浦电厂人的一个念想。所以,专业学者讨论一栋建筑的价值是什么,从理论上讲大烟囱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就是记忆。就像在家里面,如果去世的老人的东西都没有了,也就谈不上记忆了。虽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着,但你总是要留下点什么,给自己一些念想。
作者:本报首席记者 杨逸淇 记者 陈瑜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陈瑜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