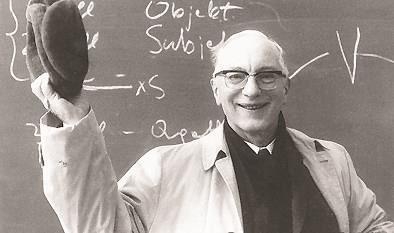
▲埃里克·沃格林(1901—1985)
雅斯贝斯的历史哲学赋予超验价值更为重要的地位,并以超验价值的形成与制度化作为其比较文明研究的基础。和雅斯贝斯一样,沃格林深受韦伯的影响。沃格林理论的出发点也与韦伯颇为相似。不过,韦伯所津津乐道的新教理性主义在沃格林看来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灵知主义。
韦伯关于儒教与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论无疑构成其宗教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韦伯的理论可能有诸多视角,其中一个颇为有趣的视角是将韦伯和受他影响的几位著名德裔思想家的观点放在一起比较。这种比较或可对我们理解韦伯理论的价值与局限有所启迪。
强调“紧张状态”
中文学界在讨论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时,较多关注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争论儒家文化是否也包含某种功能趋同的伦理。
不过,为了全面理解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特别是理解韦伯对传统中国文化所包含的经济伦理的分析,最好的方法是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他在十多年后写作的《儒教与道教》以及《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阅读。按照韦伯自己的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集中讨论的是经由对世界的伦理态度所驱动的职业伦理问题,而《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则是从更广阔的角度比较不同世界性宗教的经济伦理。
《儒教与道教》作为《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韦伯成熟时期的宗教社会学理念。韦伯首先以“社会学基础”为标题颇为全面地分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结构,然后剖析了儒教与道教的基本伦理倾向。最后,他以比较方式专章分析“儒教与清教”。
在这一章中,韦伯阐释了他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核心理念:即如何处理超验价值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展示了不同宗教理性化程度的差异。他将之划分为三种类型:适应世界型,逃避世界型,以及克服世界型。
按照韦伯的分析,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不包含任何超验价值。“在中国从未出现过与‘现世’的紧张对峙,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超世的、提出伦理要求的上帝做过伦理的预言。”“在儒教的伦理中,看不到存在于自然与神之间、伦理要求与人的缺点之间、罪恶意识与救赎需要之间、尘世的行为与彼世报答之间、宗教义务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任何紧张感。”正因为儒教“如此彻底地消除了此世与个人的超世规定之间所存在的悲观主义紧张性”,韦伯才断言儒教“将与此一世界的紧张性降至绝对的最低点”。在这个意义上,儒教的宗旨是“适应外部世界,适应‘世界’的条件”,而不是按照某种超验价值去改造世界。
与儒教形成最鲜明对比的是清教。按照韦伯的观点,基督教本身包含的超验价值在新教改革后得到强化。“禁欲主义的基督新教通过种种迹象表明,它已达到了最后阶段。从它所显示的大多数特点看来,它将巫术完全彻底地摈除。就连在已纯化的圣礼与象征仪式里,巫术也原则上被根除了。”惟其如此,“清教伦理在对待尘世事物的态度方面,与儒教的伦理形成强烈的对照。如果说儒教对世上万物采取一种随和态度的话,那么清教伦理则与‘世界’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任何一种以其理性的(伦理的)要求而与世界相对立的宗教,都会在某一点上与世界的非理性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清教与儒教的对比构成评价儒教以及广泛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基础。由于儒教中不包含超验价值,缺乏超验价值与此世的紧张性,儒教影响下的中国文化展示出独特的伦理取向。
首先,根据韦伯的分析,儒教没有原罪的观念,儒教徒的人生目标是“此世的福、禄、寿与死后的声名不朽”。儒教徒“就像真正的古希腊人一样,他们没有超越尘世寄托的伦理,没有介于超俗世上帝所托使命与尘世肉体之间的紧张性,没有追求死后天堂的取向,也没有恶根性的观念,凡能遵从诫命者——这是一般人能力所能及的——就能免于罪过”。其次,儒教缺少超验价值,对现世的态度是适应世界,“适应外部世界,适应‘世界’的条件”。

▲“挑战”西方中心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韦伯的影响,卡尔·雅斯贝斯的历史哲学赋予超验价值更为重要的地位,并以超验价值的形成与制度化作为其比较文明研究的基础。所不同的是,雅斯贝斯并不像韦伯那样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他试图突破将耶稣基督降临作为世界历史轴心的传统基督教理念,而将轴心时期扩展到中国、印度等文明。
雅斯贝斯历史哲学的最重要贡献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阐释了“轴心时期文明”的概念。他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个阶段称为“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希腊等文明出现了伟大的哲学家或先知,从而突破并超越了原始文化,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这些民族因此便成为“轴心民族”。“正是这些民族,他们在与自身过去的连续性中完成突变,在此突变中仿佛再生并通过它建立人的精神本质及其真正的历史: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犹太人、希腊人。”
根据雅斯贝斯的分析,轴心时代革命是人类历史中的决定性时刻。在轴心时代革命之后便形成几个大的“轴心民族”,其文明一直延续至今。而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则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千上万的古老高度文化随着轴心时代而终止,轴心时代同化它们,接受它们,让它们沉没,是同一民族承受新事物也好,是其他民族也罢。”
雅斯贝斯在阐释轴心时期文明的特征时,强调精神突破的重要性。他多次使用超验(transcendence)这一词汇描述轴心时期发生的最大变化。艾森斯塔德对雅斯贝斯的这一理论内涵有清晰的理解。他在分析轴心时期文明的概念时,将轴心时期文明精要地概括为,“在超验秩序和现世秩序之间的基本紧张开始显现,并被概念化与制度化”。
雅斯贝斯关于轴心时期文明的概念尽管引发了不少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自雅斯贝斯以来,关于轴心时期文明的概念一直是比较历史研究和比较宗教研究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一些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和比较文化研究学者试图利用、拓展这一概念作为比较文化研究中的理论框架。在此,我们可以举出著名汉学家史华慈关于轴心时期文明的创造性研究,艾森斯塔德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对轴心时期文明的研究,以及罗伯特·贝拉的研究。
雅斯贝斯关于轴心时期文明的概念被不少人描述为挑战西方中心主义、倡导多元文化理念的代表。其实,尽管雅斯贝斯承认若干文明实现了轴心时期文明革命,但是,在这些实现了轴心时期革命的文明之间,还是有等级的区分。正如有的学者注意到的那样,“虽然雅斯贝斯拒绝‘欧洲的傲慢’,但他还是用一个统一的理性尺度来评价所有的文化与社会。……在这样的‘轴心突破’思想指导下的历史分析或文明分析,必然会更多地在意它们的分析对象是否达致突破,而不会太在意个
别传统的特殊性。……今天的人们已经不能接受这种通过牺牲多样性而得来的普遍性,不能接受那种没有多样传统的抽象的人类”。
“存在的飞跃”与彻底分离
在西方关于比较文明研究的学者中,当代著名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的理论似乎较好地平衡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和雅斯贝斯一样,沃格林深受韦伯的影响。沃格林理论的出发点也与韦伯颇为相似。他不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理解人性,而是从精神的角度理解人性。按照沃格林的说法,人有两种存在方式,其一是自然的存在(natural being),其二是实存的存在(existential being)。在自然存在状态下,人的存在方式和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并无二异:我生、我长、我死,自然存在的人并不理解人生的意义,不理解个人之存在与一个更大的存在链条之间的关系。从自然的存在向实存的存在转化的关键环节是政治共同体的构建。通过政治共同体,个体的存在和一个更大的存在体联系在一起,从而将有限的生命与超越有限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以此赋予个人存在更长久的意义。
在沃格林看来,一个政治社会的秩序在两方面有赖于具有超验性质的真理:一方面,政治社会的公共秩序被视为旨在维护和增进该社会所代表的超验真理,超验真理于是成为该社会从事政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另一方面,公共秩序本身的建立和维护有必要从超验真理获取支持,超验真理于是成为该社会的政治活动可资利用的一种手段。
按照沃格林的分析,人类社会早期的帝国,即近东和远东的帝国所代表的超验真理实质上是一种“宇宙论的真理”,那时的帝国也可以被称为“宇宙论帝国”。宇宙论帝国的特征是超验真理和帝国秩序之间融为一体,用沃格林的术语来表述的话,二者呈现出“紧致(compact)”状态,没有任何意义的分殊(differentiation)。或者,为了更好地理解沃格林的观念,如果我们把沃格林的术语换成韦伯和雅斯贝斯的术语的话,在宇宙论帝国时期,尚未出现超验价值和现世秩序之间的明显分离与对立。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宇宙论帝国的真理观受到挑战。这种挑战的发生代表了“存在的飞跃 (leap in being)”。按照沃格林的解释,“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长达五百年的过程,更确切地说,大约相当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300年这段时期;它在多个文明中同时发生,却并没有明显的互相影响。在中国,是孔子、老子和诸子百家时代;在印度,是奥义书和佛陀时代;在波斯,是琐罗亚斯德教时代;在以色列,是先知时代;在希腊,是悲剧和哲学家们的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这段时期,也就是赫拉克利特、佛陀、孔子同时在世之时,或许可视为这一旷日持久的过程中的一个特别典型的阶段”。
我们很容易看出,就基本逻辑而言,沃格林的理论与韦伯及雅斯贝斯有相同之处。事实上,沃格林在著作中曾引述雅斯贝斯关于轴心时期文明的理论。沃格林也像韦伯及雅斯贝斯那样,将超越价值和现实世界之间紧张关系的程度作为区分不同文明的标尺,而且明确地将超验价值与现实秩序的分离作为大的文明“突破”的标志。
尽管沃格林像雅斯贝斯一样,注意到在不同地域出现过“存在的飞跃”,但他强调只有在西方文明中,超验价值与现实秩序的分离达到最典型、最彻底的程度。
这种分离首先体现在希腊哲学中。按照沃格林的观点,柏拉图的哲学代表了从哲学角度“突破”宇宙论秩序的最完美形式。沃格林称柏拉图式的哲学是一种“人类学的原理”,这个原理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是用来解释社会的一个普遍原理;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社会批判的工具。”柏拉图所发现的批判性原理目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原理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为人们揭示灵魂的真正秩序,也就是揭示上帝的尺度。按照沃格林的描述,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具有超验价值特质的“灵魂的真正秩序”与具有宇宙论特质的灵魂的实际秩序既同处于现实存在之中,又构成强烈的张力。超验价值不可能改变所有人的灵魂,使理想政体得以在城邦建立,但超验价值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与引导功能,引导“将人心向上帝敞开”。
与哲学方式相并列的是以宗教的方式实现从宇宙论秩序的突破。这种宗教的突破首先出现在以色列。在《以色列与启示》中,沃格林详细考察了近东早期的宇宙论秩序以及以色列的突破。沃格林高度评价以色列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神的选择使以色列能够一跃而与超越的存在实现更完美的和谐。这个历史结果打破了文明进程的模式。随着以色列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代理人,此代理与其他民族不同,它既不是一个文明,也不是处于一个文明中的民族。……如果没有以色列就没有历史,而只有宇宙论形式的社会无休止重复。”
在希腊哲学与犹太教结合的基础上发展出基督教。基督教的兴起标志着第一个世界性宗教的出现。在基督教教义中,神的秩序和人的秩序发生了分离。奥古斯丁所谓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张力奠定了基督教政治秩序结构的基础。
至此为止,沃格林的分析似乎是韦伯学说的进一步展开,但是,在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节点上,沃格林与韦伯分道扬镳了。在韦伯那里,新教伦理代表了典型的西方现代理性主义。新教伦理的最大特征是,一方面,新教摆脱了巫术的超验价值;另一方面,超验价值和现实世界构成强烈的紧张关系。在沃格林看来,这也折射出基督教文明的现代危机。沃格林的基本观点是,超验价值与现实世界的分殊是“存在的飞跃”的核心内涵。无论是柏拉图的哲学还是犹太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教义,在本质上都有一个超验价值与现实世界的分殊与张力。超验价值只能作为现实秩序的导引,而不可能作为现实秩序的蓝图或目标。任何教义,如果企图在现实世界实现超验价值所描绘的秩序目标,就是以另一种方式追求一种“紧致性的结构”,即重新返回宇宙论秩序。
如果我们将沃格林的理论和韦伯的理论作一番简单对比,那么,可以看出,韦伯所津津乐道的新教理性主义在沃格林看来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灵知主义。企图按照超验价值的指引改造现实世界,最终将导致极端现代性危机。韦伯和沃格林都认定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不包含强烈的超验价值,因而缺乏超验价值与现实世界的紧张,按照沃格林的逻辑,这恰恰是防止走入极端主义等现代性歧途的精神基础。■
作者: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编辑:范菁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