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尔·史密斯(NeilSmith,1954—2012),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与地理学教授
士绅化的推进,与其说是通过勇敢的拓荒者的行动,不如说是通过资本的集体所有者的行动。士绅化完全是一个国际现象。在它的语言中,对前沿意象的青睐是显而易见的:城市拓荒者、城市自耕农和城市牛仔成了城市前沿新的民间英雄。
1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93年发表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958年版)这篇具有典范意义的论文,他提出:
美国的发展所展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线条的前进,而是一个在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向原始状况的回归,并在那个区域有新的发展。美国社会的发展就这样在边疆持续不断地开始着……在这一进程中,边疆是移民浪潮的前沿,是野蛮和文明的会合处……荒野被越来越多持续增长的文明线条所渗入。
在特纳看来,开拓边疆,压制荒野与野蛮,其目的是在桀骜的、不合作的自然界中开辟出可居住的空间。这不仅是单纯的空间扩张和物理世界的逐步驯化。开发边疆当然能够达成这些目的,但对特纳来说,它也是定义美国民族性格独特性的核心体验。随着身强力壮的拓荒者每次将边疆向外推进,不仅新的土地被纳入美国版图,而且新的血液也被注入美国理想的血脉中。每一波西进的浪潮,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将人性的冲击波传回到东部。
到了20世纪后期,有关荒野和边疆的意象已经不大适用于西部的平原、山脉和森林(西部的文明程度已经相当可观),反而更适用于美国东部的城市。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郊区化的兴起,美国城市开始被视为“城市荒野”;城市过去是——如今大多数也仍然是——滋生疾病和混乱、犯罪和腐败、毒品和危险的温床。事实上,这些担忧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由关注城市的“凋敝”和“没落”、内城的“社会弊病”、城市社会的“病理现象”的城市理论家们表达过,简言之,“城市不再是天堂”。城市被描绘为荒野,或者是更糟糕的描述——“丛林”。比起新闻媒体或社科著述的描绘,这一点在好莱坞的“城市丛林”类型电影中表现得更加形象,比如《金刚》《西区故事》《梦断勇士》和《布朗克斯的阿帕奇要塞》这些电影的主题。正如罗伯特·博勒加德(1993)所说,这种“有关没落的话语”主宰了有关城市的讨论。
反城市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核心主题。与当初的荒野经验类似,过去的30年间,人们对城市的印象也经历了从恐惧到浪漫主义的转向,以及从荒野到前沿的城市意象的发展。17世纪的科顿·马瑟和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对森林充满恐惧,将其视为难以穿越的邪恶、危险的荒野、原始之地。但随着森林不断被驯化,及其在日益资本化的人类劳动者手中不断发生变化,特纳较为温和的边疆意象逐渐取代了马瑟的邪恶森林论调。这种乐观主义和扩张的期待与折射出自信与征服感的“前沿”相关联。因此,在20世纪的美国城市中,城市荒野的意象——意味着绝望地放弃——到20世纪60年代(尽管到处都是暴动)已经开始被城市前沿的意象取代。这种转变可以部分追溯到“城市更新”的讨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独户式住宅和公寓街区的改造逐渐形成,“城市更新”继承者的象征意味而得到强化。在士绅化(gentrifcation)的语言中,对前沿意象的青睐是显而易见的:城市拓荒者、城市自耕农和城市牛仔成了城市前沿新的民间英雄。在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杂志甚至谈到了“城市侦察员”,他们的工作是去考察高档街区的周边,探察地块是否适合投资,同时还要报告当地居民的友好程度。不那么乐观的评论员则控诉新出现的“城市好汉”与内城的毒品文化有关联。
正如特纳虽然认识到美洲原住民的存在,却将他们看作野蛮荒野的一部分,当代的城市前沿意象也把当下的内城人口视作自己周围环境的自然元素。因此,“城市拓荒者”的术语和“拓荒者”的最初概念一样,显得傲慢自负,因为它暗示着一个还没有社会化的城市;同美洲原住民一样,城市工人阶级并没有被认为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只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特纳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清楚,他把边疆称为“野蛮和文明的会合处”,虽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士绅化前沿的论述很少说得那么明确,但是对待内城人口的方式大致相同。
这种相似之处还有很多。对特纳来说,地理上边界线的向西推进与锻造“民族精神”有关。同样的精神期望也在将士绅化看作城市复兴前沿的一片拥护声中得以表达;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新的城市拓荒者被寄予厚望,期待他们能够如当年的前辈那样对萎靡不振的民族精神做出贡献:带领国家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把旧世界的问题都抛在后面。借用一份联邦文件上的话,士绅化的历史使命涉及“在心理上重新体验过去所取得的成功,因为近年来让人失望的事件不断上演,如越南战争、水门事件、能源危机、环境污染、通货膨胀、高利率等”(历史文物保护咨询委员会,1980)。从这里,我们将会看到,从失败的自由主义走到20世纪90年代的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仅是很短的一段路程。目前还没有人会真的认为,我们应该把詹姆斯·劳斯(他负责开发了巴尔的摩内港、纽约南街海港及波士顿的法纽尔厅这类风格特异的市中心旅游购物街)视作士绅化的约翰·韦恩,但只要这些项目成为许多城市中心进行士绅化改造的标准,这种说法仍将是相当符合城市前沿话语的。最后,重要的结论是,无论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部,还是在20世纪末的内城,前沿话语使征服的过程变得合理化、合法化了。
特纳对西部历史研究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他所设立的爱国者历史标准也很难让人忽视。然而,新一代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已经开始重写边疆的历史。帕特里夏·尼尔森·利默里克在自己对西部好莱坞历史的拨乱反正中察觉到近现代城市对前沿母题的再次挪用:
如果好莱坞想抓住西部历史的真实情绪,它的电影将是关于房地产的。约翰·韦恩将既不是枪手,也不是警长,而是测量师、投机商或者打索赔官司的律师。决斗将出现在土地办公室或法庭;武器是契约和诉讼,而不是左轮手枪。
现在,这在很多方面看上去似乎是对士绅化过程的一种高度民族主义的表达。事实上,士绅化完全是一个国际现象,广泛出现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的城市,以及日本、南非和巴西的一些城市。在布拉格或悉尼,或者说多伦多,关于前沿的语言并不像在美国那样自动成为士绅化的意识形态润滑剂,而这种适用于世纪末城市的前沿神话看上去很明显是美国的造物。毫无疑问的是,虽然前沿神话更加明显地表现在美国,但是最初的前沿体验并不是单纯的美国商品。首先,它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西西里岛的潜在移民对新世界的想象,而这种想象与已经居住在堪萨斯城或旧金山的德国或中国移民对新大陆的体验一样是真切的。其次,其他的欧洲殖民前哨站,如澳大利亚或肯尼亚内陆、加拿大的“西北前沿”,或印度和巴基斯坦,虽然阶级构成、种族结构和地形地貌全然不同,却享有同样功效的前沿灵药,这使它们保持了相同的意识形态。最后,前沿母题不管怎么说,都是在非美国(non-US)的情况下出现的。
2
或许最显著的是于伦敦涌现出的前沿,即著名的“前线”。整个20世纪80年代,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在经历了警察和加勒比黑人、南亚裔、白人青年之间的对峙骚乱后,好几个街区都出现了一条地盘线。这些“前线”,比如肯辛顿和切尔西的“万圣路”,或是诺丁山或布里克斯顿的类似地区,在70年代是一起形成的抵御警察袭扰的阵地,同时也是警方建立的战略性“滩头阵地”。到了80年代,它们也很快成为去士绅化的前线。原伦敦警察总长肯尼斯·纽曼爵士在80年代初推出了这项前线策略,并在一次面向欧洲大西洋右翼组织发表的演讲中解释了推出的目的。他在演讲中引述道,“多族群社区不断发展”导致了“被剥夺的下层阶级”,他预计到了“犯罪和混乱”的出现,标明了包括上述前线区域在内的伦敦11处“象征性地点”,需要在那里采取特别的战术。对于每个地点,他认为“都有一个应急计划,警方能够迅速占领该地区并加以控制”。
前沿母题一直是伦敦日常生活文化泡沫中的一部分。同在美国各地一样,对某些人来说,“城市牛仔”带有一些鬼魅的风格。“是啊,如日中天般遍布伦敦,”罗伯特·耶茨说,“狂野西部的狂热分子都戴上自己的牛仔帽,上好马鞍,以为伦敦塔桥就是美国得州。”(1992)在哥本哈根,“狂野西部”酒吧开在一个高档社区里;在1993年5月因为丹麦投票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引发的骚乱中,有6名抗议者在那里被警方枪击。从悉尼到布达佩斯,“狂野西部”式的各种酒吧和其他前沿符号不时地描述并点缀着城市社区的士绅化。当然,这个母题经常会有一个鲜明的本地外号,就好像伦敦的帝国主题,士绅化者成了“新拉吉”,而“西北前沿”则呈现出全新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在这个说法里,士绅化的国际性得到了更加直接的承认。
与每种思想意识一样,把士绅化看作新的城市前沿有其真实基础,也有其偏颇之处——如果不算是扭曲的话。前沿代表着能够唤起回忆的经济、地理和历史发展的组合,然而从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来说,将这种命运寄托在社会的个体主义身上仍然只是神话。特纳的边界线向西推进,与其说是依靠个体的拓荒者、自耕农、衣衫褴褛的个人主义者,不如说是靠银行、铁路、国家和其他集体的资本资源。在此期间,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在大陆上的地域扩张来实现的。
今天,经济增长和地理扩张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这将效能赋予了前沿的意象,但是这种联系的形式是非常不同的。如今的经济扩张不再纯粹是通过绝对的地域扩张进行,而是涉及已开发空间的内部分化。在城市尺度,这就是城市士绅化与城市郊区化对比的重要性。总体上的空间扩张与细部的士绅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发展不平衡的例子。与真正的城市前沿相似,士绅化的推进,与其说是通过勇敢的拓荒者的行动,不如说是通过资本的集体所有者的行动。城市拓荒者勇敢地前行之处,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小规模的和实力雄厚的放贷人、零售企业和国家一般早已前往了。
在所谓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和国际资本都面临各自的涵盖在士绅化前沿之内的全球性“前沿”。不同空间尺度与城市国家化和国际化扩张发展的向心性之间的联系,在城市企业区支持者热情洋溢的语言中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所谓城市企业区是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创的一个想法,也是20世纪90年代城市私有化策略的核心。斯图尔特·巴特勒(为极右翼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工作的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认为,在这一对城市弊病的诊断中,把内城转换成前沿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意象不仅仅是方便的意识形态表达。如同19世纪的西部,20世纪末的新城市前沿的建设是经济再征服的地域性政治策略:
也可以这样说,今天许多城市区域面对的问题至少有一部分在于我们没有把特纳解释过的机制(即本地的不断开发和创新观念)应用到内城“前沿”上去……企业区拥护者的目的是提供一个环境,使前沿化的过程可以由城市本身来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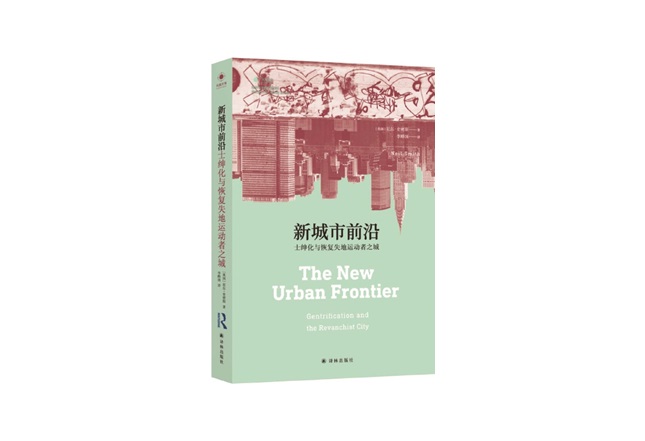
▲(尼尔·史密斯著李晔国译《新城市前沿》,译林出版社,2018年6月)
3
回想起来,我想我第一次感受到士绅化,是1972年我在爱丁堡玫瑰街的一家保险公司做暑期实习时。每天早上,我从达尔基斯坐79路巴士,然后走半条玫瑰街到达办公室。玫瑰街是气势恢宏的王子大街后面的一条后街,长期以来都是著名的酒吧街,密布了夜总会和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酒吧,以及很多更加昏暗肮脏的、人们常常光临的地方(用美国人的说法,就是小酒吧),甚至还有几家妓院(虽然传闻它们在70年代初就已经撤到多瑙河街去了)。这是爱丁堡酒吧聚集的地方。我的办公室下面新开了一家叫“骏马奔腾”的酒吧,它没有俗气的装饰,也没有因时间久远而撒落一地的木屑。这是一家全新的酒吧,提供用沙拉佐餐的相当开胃的午餐,这在当时大多数的苏格兰酒吧里都还是一个新事物。几天后,我开始注意到其他的一些酒吧也被“现代化”了;出现了几家新的餐厅——当然对我来说,价格太贵了,要不然我去餐厅的次数要多得多。因为许多楼上的房间也在装修,狭窄的玫瑰街总是堵满了施工车辆。
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只是当我在费城那几年作为一名地理学本科生接触了一些城市理论后,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模式,更是一个戏剧性模式。我所了解的所有城市相关理论(当然,当时实际上没几个)都告诉我说,这种“士绅化”是不应该发生的。然而,在费城和爱丁堡,它又确实发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在20世纪7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我有很多相似的经历。我听到并爱上了兰迪·纽曼的歌曲《大河燃烧》,并视之为尖刻的环境抗议,但在1977年我到克利夫兰的时候,凯霍加河畔“平跟鞋”酒吧里的场景已经开始吸引雅皮士、像我这样的学生、号称“地狱天使”的飞车党和下晚班的码头工人。我想我看到了不祥之兆。我同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克利夫兰的朋友打赌说,这座城市将在十年内显著地士绅化,虽然她从未付过赌资,但是她不得不在还远未到十年的时候就承认自己输了。
本书中的论文涉及各种士绅化的经验,但它们更多是发生在美国。事实上,有四分之三的章节,特别是结尾部分对去士绅化的政治和文化观点的讨论,都是基于我自己在纽约的生活经验和研究。这显然会引起人们对这些论点在其他语境下适用性的怀疑。虽然我接受劝诫,认为不同的国家、地区、城市,甚至街区的环境,都会有全然不同的士绅化经验,但是我也坚持在这些不同中,大多数士绅化经验会有相互共鸣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从纽约的经验中学到很多,而且纽约的情况能够大量地激发别处的共鸣。当卢·里德演唱《和你相约在汤普金斯广场》(收录在他的专辑《纽约》中)时,他让围绕着这座下东区公园进行的暴力抗争,立刻成为许多人能够识别的新兴“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国际符号。
(本文节选自《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前言,标题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作者:尼尔·史密斯
翻译:李晔国
编辑:范菁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