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华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群,尤其熟悉下层农民生活。一生著述十余种,均与中国有关,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其中,《中国人的素质》初版于1894年,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国民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先后被译为法、德、日等多国文字,影响深广。该书对百余年前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留日学生构成强烈震撼。

▲埃德蒙·詹姆斯,1904年至1920年间担任伊利诺伊大学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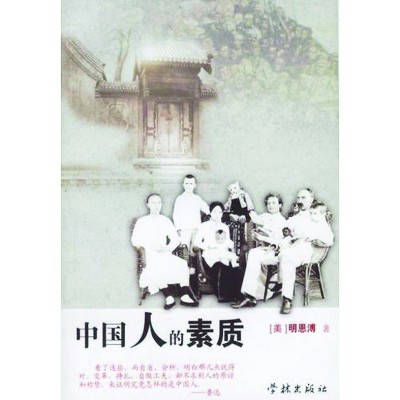
伊利诺伊大学与中国展开的交流互动反映了当时中美关系中的很多议题——从美国教育的理想主义与全球化憧憬到国际关系与种族主义。探究伊利诺伊大学发展对华关系的最初构想和目标,以及迄今为止的实现情况,有助于揭示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美国与东亚地区的关系中,曾经扮演了怎样矛盾而暧昧的特殊角色。
美国有一所高校名为“中国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新闻网站“高等教育界”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称为“中国大学伊利诺伊分校”。她之所以赋予其如此醒目的别号,是为了凸显这所州立旗舰大学中国留学生大规模增长的现状。新世纪以来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群体迅速膨胀,现已占据美国高校国际生源的最大份额,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正好同步见证了这个趋势。其本科生中的中国学生从2000年时的37名暴增为2014年的2898名;再加上1973名研究生,该校拥有近5000名中国学生,成为全美高等教育机构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大学。(Elizabeth Redden,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at Illinois,” Inside Higher Ed ,7 January 20 5)
“中国大学伊利诺伊分校”的称号,除上述作者本意之外,还可以衍生出另一层含义,唤起谙熟于这所大学对华交流史的人们的某些悠久记忆。这段历史始于1908年到1909年间,当时全球的政治格局尚处于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掌控之下,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相对而言微不足道。伊利诺伊大学与中国展开的交流互动反映了当时中美关系中的很多议题——从美国教育的理想主义与全球化憧憬到国际关系与种族主义。本文致力于探究伊利诺伊大学发展对华关系的最初构想和目标,以及迄今为止的实现情况。这段历史揭示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美国与东亚地区的关系中,曾经扮演了怎样矛盾而暧昧的特殊角色。

▲容闳,广东香山南屏人,最早获得西方大学正式学位的中国人。

▲1872年,香港,首批留美幼童合影。这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批幼童原计划留学15年,但9年后就被中途召回。
一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帝国主义的打击和满清王朝的乱局导致中国此后陷入连串危机之中。不到半个世纪,中国又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欧洲诸强蜂起瓜分中国,让曾经立于世界之巅的“中华帝国”跌落谷底,沦为帝国主义列强利益争夺的牺牲品。西方列强按照财富和权力重新制订国际规则,当此遽变之下,坚持传统价值以维系自身的文化属性,还是学习现代技术来提高国家的安全保障,这二者之间如何取舍平衡,成为中国思想先驱和知识精英们不断讨论的议题。这些思想交锋常常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而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早期的现代化追求终于成为中国的主流话语,其标志便是张之洞在1898年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这种具有现代性的“体用观”,既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优越性,又不动摇中国文化传统的唯一性。虽然关于何为中国“本质”的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上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辩题,但暂将其搁置不论,自从中国开始向西方重点学习机械、技术以及商业方面的先进知识,中美之间的文化关系便发生了改变。
到了1899年,随着美西战争告捷进而取得对菲律宾的统治权,美国跻身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第一梯队。只不过由于其外交和军事力量集中于拉丁美洲,它在亚洲的存在感和影响力还十分有限。正当诸强竞相争夺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之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海(John Hay,1838—1905)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旨在确保所有国家在华享受平等的投资和贸易机会,无论是否已经获得本国的势力范围(例如,日本在中国东北,英国在华中地区)。对当时尚未如英、日一般拥有势力范围的美国而言,获得国际社会对该政策的认可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帝国主义列强的默许(特别是来自日本的,因其“公认”的在太平洋地区的强大影响力),则在美国的政客、传教士、商人和教师群体中激起与中国深入发展商贸及其他双边关系的强烈需求。正是基于这种国际背景,伊利诺伊大学开始在亚太地区建立关联并无形中影响了中美关系。
20世纪初,伊利诺伊大学在富于开创精神的校长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 James,1855—1925,1904—1920在任)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一所国家级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初时,詹姆斯踌躇满志地来到厄巴纳—香槟市,力图将伊利诺伊大学建设成为跻身美国高等教育联盟、与哈佛大学并驾齐驱的公立大学。与此同时,他也希望通过教育来扩大美国在全世界的文化影响力。[詹姆斯校长对伊利诺伊大学的贡献,详见Winston Solberg著 “President Edmund J. James and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04—1920: Redeeming the Promise of the Morrill Land Grant Act,” (未出版手稿)] 实际上,詹姆斯在担任校长仅仅两年之后,1906年,就与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在华传教士和舆论领袖共同上书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82—1945),力主部分退还美国政府依据1901年与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所获得的“庚子赔款”,并用于帮助中国政府发展现代(美式)教育。
为什么偏偏是1906年呢?原本罗斯福政府的太平洋战略更重视支持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壮大,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只能叨陪末座。然而,爆发于1905年海内外华人圈的“抵制美货运动”,使罗斯福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的亚洲政策。在此之前,经过二十余年排外情绪的酝酿,美国国会于1882年颁布了《排华法案》,不仅十年之内禁止中国劳工入境,更剥夺了中国移民获得美国公民的权利,甚至在1904年还将该法案无限期延长。尽管来自中国的学者、商人和官员在表面上得到豁免,但实际上一旦入境便难逃美方工作人员的持续侮辱与骚扰。受此影响,中国各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组织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全国性运动,以拒买美货的方式来宣泄国人对美国种族歧视政策和排华行径的愤慨。鉴于中方对美国种族主义的强烈反感,罗斯福总统将这场反美运动视为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信号,并开始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全新途径。(见Peter Kwong and Dusanka Miscevic, 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5, chapters 7 and 11;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a, chapters 1-3)
就在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Arthur H. Smith,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其关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初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到白宫敦促美国政府返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教育事业的同时,埃德蒙·詹姆斯校长也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封与亚瑟·史密斯不谋而合的信函。这封信集中表达了“改造”中国的信念,被史密斯收录在其颇受读者欢迎的著作《今日中国与美国》(China and America Today, 1907)中,经常被人引用。教育在“门户开放”时期的中美关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正如埃德蒙·詹姆斯曾写到的,就在于教育的力量能掌控中国下一代人的心智和思维:
哪个国家舍得付出一定的成本来投入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教育事业,它必将获得道德、知识和商业领域内的巨大回报。……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如果美国能在35年前发现这一
点,留住那批中国留学生,并使之继续增殖,那么今天美国就能通过引导中国领袖的思想和决策来更行之有效地影响中国的发展。(引自 Qian Ning, Chinese Students Encounter America, T.K. Chu, tran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0, xvi-xvii. Arthur Smith 原本摘录James的信件于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于1923年首次出版. Arthur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13-16)
詹姆斯校长因此建议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重点发展教育。这个观点在当时可谓极具前瞻性。 到数十年之后,众多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的学者才提出一个国家如何通过教育、电影、 音乐等“软实力”去影响另一个国家的。
埃德蒙·詹姆斯在信中提到的“那批中国留学生”和“35年前”,是指通常学者称为第一次的中国“留美潮”。1847年,在一位美国传教士的资助下,容闳(1828—1912)成为首位赴美留学的中国人。七年后,他带着耶鲁大学的学士学位荣归故里,由此萌生了引领更多中国年轻人赴美留学的梦想。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1811—1872)希望中国涌现更多的工程师和商人来推动社会变革,在他的支持下,容闳从1872年到1876年之间先后组织了120名中国男孩来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学习。然而到了1881年,随着美国国内反华情绪的高涨,清政府改弦易辙召回全部留美学生,这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官派留美计划的夭折。(见 Qian Ning, Chinese Students Encounter America, pp. Ix-xv; Liel Leibovitz and Matthew Miller, Fortunate Sons ,New York: W.W. Norton, 2011; Edward J.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而至1908年,美国国会授权豁免了部分“庚子赔款”,中国政府遂于1909年以其款项设立“庚子赔款奖学金”来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此后又在北京建立了留美预备性质的清华学堂(1928年更名为清华大学)。这也拉开了第二次“留美潮”的序幕。
1908年,埃德蒙·詹姆斯邀请时任清政府驻美公使的伍廷芳担任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邀请中国人做演讲嘉宾在当时可谓破天荒。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此举亦并非偶然。晚清名宿伍廷芳(1842—1922)是一名曾在英国伦敦接受过法律教育的律师,也曾是一个深度参与“抵制美货运动”的民族主义者,更在1907年至1910年间担任清政府驻美公使。这位中国外交家于1908年6月来到厄巴纳—香槟市,似乎非常享受校长一家的殷勤款待和美国中部简朴的生活方式。或许为了表明他对伊利诺伊大学作为中国学生赴美学习优良基地的热忱肯定,他与当时在校的五名中国大学生和预备生(包括胡诒谷和杜伟岑等)合影留念,这张照片现存于伊利诺伊大学档案馆。此次访问后不久,伍廷芳就致书埃德蒙·詹姆斯,打算推荐两名学生来学习法律,并详细询问了招生政策和学费情况。詹姆斯校长马上答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函,着重强调了伊利诺伊大学相对低廉的学费和生活成本。他还提到了“庚子赔款奖学金”,并向伍廷芳表明自己“热切期盼通过您……来传达我对每一个希望来伊利诺伊大学求学的中国学生的诚挚欢迎”。此外,他还表示“希望您能寄一份官派留学生的名单和地址,以及他们具体的留学计划”。
然而,事实证明,伊利诺伊大学并未从“庚子赔款奖学金”这项最负盛名的中国政府奖学金中获益太多。根据官方记录,从1909年到1911年,180名中国官派留美学生中绝大部分都就读于常青藤盟校,真正来到伊利诺伊的只有区区18人。(第一次庚子赔款留学生列表, https://Zh.m.wikipedia.org ,accessed 14 March 2017)但是毋庸置疑,为了实现创建研究型大学的梦想,培养出能对中美关系作出积极贡献的中国青年才俊,埃德蒙·詹姆斯多年间实施的一系列招生方案和发展战略,在当时都极具开创性。举例来说,在吸引中国生源方面,他就通过自己熟悉的各种美国在华传教士团体得以和中国一些不太知名的省级预备学校建立起联系。而他对中国留学生的这种热情支持就曾经给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两位负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分别是校长张鸿烈(1918年获得政治教育硕士学位)和钟朋先(音译,1918获得畜牧学学士),二人都曾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并在1920年代选送了三名毕业生来到伊利诺伊大学。(Carol Huang, “The Soft Power of U.S Students and the Foundation of a Chinese America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in Urbana-Champaign,”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01, p. 49)
大概正是通过伍廷芳的努力,伊利诺伊大学以其低廉的学费和生活成本在中国逐渐打开局面。《东方杂志》作为晚清至民国时期极具影响力的上海刊物,就曾登载文章比较过美国不同大学的留学成本。而这样的宣传尤其能有效地吸引自费留学生,他们可是占据了第二批中国留美学生总数的半壁江山。同时,詹姆斯校长对中国的危急处境和中美关系的深切关注,对中国留学生群体生活水平和学术事业的不懈推动,也使伊利诺伊大学在中国青年中倍受青睐。例如,1913年在密歇根州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学生联盟”(一个全美华人学生组织)大会上,来自伊利诺伊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大放异彩”,詹姆斯随后便向该组织申请承办下届大会,顺利获得批准。在他的督导下,这次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使伊利诺伊大学收获了来自中国留美学生群体前所未有的瞩目。为了表达对詹姆斯校长的敬意,联盟授予其“荣誉会员”的称号(其他获此殊荣的知名人士中还包括哲学家约翰·杜威),并恳请他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提供舆论支持。
许多曾经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的华籍留学生后来都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举例来说,1913年毕业于农学院的竺可桢,五年后又获得哈佛大学的气象学博士学位,归国后终生活跃于专业教学、科研领域,赢得“中国气象学之父”的称号;1915年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的陶行知,随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1920年代即成为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领军人物,同时又是1930到1940年代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积极倡导者。
但另一方面,伊利诺伊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也面临着所有在美中国留学生都要面对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随处可见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这些留学生表面上获得学校的
“热烈欢迎”,实际上却常常受到质疑,甚至被惯于调侃东方主义的恶趣味所讽刺讥诮,即便这些还算不上彻头彻尾的敌意。比如,发表于1910年《校友季刊》“伊利诺伊大学中国留学生”专栏的一份报告竟然这样写道:
早些时候,还从未听说过有人想过招收中国学生。在那个年代,中国完全是个恐怖的代名词,其国民是“野人蛮族”,其前景黯如地狱。想象一下我校的某位先驱……在和中国人见面时……尽管对方也能履行真正的美式礼仪,发自内心而又热情适度,但中国学生的手实在是又小又细,手指修长,一触生凉,甚至可以说是一击即碎……这种握手可不像罗斯福与塔夫脱那样。( “Chinese Students at Illinois” The Alumni Quarterly 1 no.4 ,October 1910 : 363.)
另外陈六琯(土木工程学硕士,1924)的遭遇也很能说明问题。他以二战时期担任重庆附近一座大型机场建设的总工程师而闻名于世,而这座用于供美军“空中堡垒”巨型轰炸机起降的机场,完全是在缺乏现代科技含量的情况下,由征募而来的数万名农民一手一脚所建造。就连1941年曾到访重庆的美国文豪海明威在目睹了建设现场之后,都盛赞这样一项伟大工程的总设计师无愧于中国英雄主义代言人的称号。但就是这位杰出人物,学生时代每次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中心就餐时,都会遭到白人学生的冷遇。事实上,即便迟至1945年,厄巴那—香槟地区依然有超过92℅的房东不愿意把房子出租给外国留学生。(Huang, “The Soft Power of U.S. Students and Foundation of a Chinese America Intellectual Community in Urbana-Champaign,” pp.190-91 and 303-305; Ernest Hemingway, By-Line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Articles and Dispatches of Four Decades ,New York, Scribner, 1998)
不过,重重困难并未阻挡留学的脚步,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伊利诺伊大学人数最多的留学生群体,其余则多来自日本、巴西、菲律宾和印度。随着在校学生日益国际化,为了帮助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更好地适应美国的学术环境,詹姆斯校长于1913年建立了“外国学生办事处”(1919年升格为“外国留学生院”),这也被视做他为伊利诺伊大学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他坚持安排一位对外国文化有过亲身体验的的教职人员(而非行政人员)来担任办事处的主管。一位以外语教学法知名的拉丁语教授詹姆斯·西摩成为首席人选。为了彰显这个位置的重要性,詹姆斯校长甚至还给西摩教授增加了300美元的薪酬(后来增幅提高到700美元)。作为一名本身就博学敬业的学者,再加上詹姆斯校长的大力支持,西摩教授放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比如开设语言扩展课程,提供一对一的语言教学服务,以及建立遍布全城的寄宿家庭制度。另外,他还花费了大量时间与各国留学生交流他们在适应美国生活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从而使“外国学生办事处”(几乎等同于“中国学生俱乐部”)成为一个让中国留学生倍感亲切的温馨家园。该办事处的成功也促使美国其他高校在接下来的几年内陆续建立了类似机构,以便为广大留学生提供建议和帮助。而西摩本人则在1921年接受了中国毕业生的邀请,用两年时间赴华游历,并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组织了类似的英语培训课程。

▲张鸿烈,河南固始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留学,1918年获得政治教育硕士学位,次年回国,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长。

▲1908年,伍廷芳在芝加哥。

▲留美预备性质的“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正式开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二
埃德蒙·詹姆斯校长通过这些创新举措来招收和培养中国学生,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同时伊利诺伊大学也在1910到1920年代成为那些渴望探索西方文化精神的中国学生的留学圣地。而继任者大卫·金利(David Kinley 1920—1930在任)此前曾经担任过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生院院长和副校长,对学校一直以来发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工作重点了如指掌,因此也在最大程度上沿袭了前任校长的开创性政策。虽然他本身并未获得新的建树,但他始终密切关注中国毕业生在国内的职业发展状况,并成为首位访华的美国大学校长。1930年,金利卸任后随即展开亚洲之行,涉足若干个中国城市,并在返美后向新任校长哈里·蔡斯(Harry Chase,1930—1933在任)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介绍他对刚刚访问过的几所中国顶尖学府的考察心得以及对中国教育发展现状的由衷看法。尽管伊利诺伊大学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但这份材料直到今天仍是校方领导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唯一一份官方报告。如果说埃德蒙·詹姆斯以一种颇具传教士精神的理想主义,寄希望于美国能在中国的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大卫·金利则在其报告中呈现出有所保留的乐观态度。当时的中国既饱受西方列强的操控,又被日本不断在满洲增兵所侵扰,广大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存在着强烈的反帝倾向和民族情绪,而金利对中美关系的清醒认识就植根于访华期间的这些亲身体验。
此次访问应该是由一些素有威望的中国校友安排打理的。实际上,从1910年代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一直活跃着一个名为“伊利诺伊大学校友会”的民间组织,并在诸多核心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以及重庆(抗日战争期间)等设有分部。不少校友会成员都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中美关系增进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王景春(1882—1956)便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1909年他受伍廷芳选荐来到伊利诺伊大学求学并获得铁路工程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又在大卫·金利的指导下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留学生在美国很难得到助学金和实习机会,时任校长的詹姆斯和导师金利都曾动用私人关系帮他筹措,包括在学校讲授一门《东方文化》的课程,以及在芝加哥火车站进行一次实习。而王景春学成归国的年代,中国的铁路系统不仅规模小,并且由于长期被西方诸列强和日本侵略者所分别管控,难免显得七零八落、各自为营。为了国家的整体发展与经济现代化,王景春誓要夺回中国铁路主权,并对整个铁路交通系统进行重组和翻修。正直的人格品性和深厚的专业学养为他赢得了“中国施政三杰之一”的美誉。他与导师金利多年保持联系,在全力推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与其师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设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中国教育代表团承担着管理全部在美中国留学生的重任,而他在数年间都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Carol Huang, 《王景春,中国第一位铁路管理博士》,《中国时报》“文学专栏” 5 December 2001:1; Stacey Bieler, “Wang Jingchun,”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校友则是被称为中国“棉纱大王”的穆藕初(1876—1943)。他生于上海一个从事棉花业的小商人家庭,1909年赴美留学时已年届33岁,五年后收获伊利诺伊大学农学学士学位,此后又在德克萨斯州农工学院取得棉花科硕士学位。怀揣建立现代纺织工业的梦想,他甫一回国便尝试开设了三家棉纺厂,将此前在美国学到的关于棉籽和棉纺业科学管理的知识投入实际应用,而这两者都需要进行大量的本土化实践,为此他也和其他棉花种植与生产方面的同行分享自己的经验成果。另外,他还发起建立了位于上海的华商纱布交易所和中华劝工银行,以加强棉纺织市场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可惜,他的棉纺事业因1930年代日本的加速入侵而备受打击。纵观其整个职业生涯,穆藕初都算得上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忠实校友,不仅一直和大卫·金利保持联系,还自毕业之初就加入了校友会,并慷慨解囊予以资助。同时,他也致力于推动校友会在中国的发展,多年担任留美归国学生联合会主席。(Moh Hsing Yueh, Alumni Biographical File, 1913-1936, RS 2614,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ign-Urbana, IL; Mu Jiaxiu et al. (eds.), 《穆藕初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以王景春和穆藕初为代表的伊利诺伊大学校友会成员,在大卫·金利访华期间给予了热情招待。二人不仅为其举办了数场盛大的宴会,更全程陪伴,贯穿始终。或许是通过近距离的交流,大卫·金利才惊讶地发现,归国留学生们如果不能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全盘顺应国内的社会环境,他们在伊利诺伊大学学到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就无法毫无保留、直接有效地服务于所谓“社会需求”。而更让他感到诧异的则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立场:
一个国家花费人力物力来帮助另一个国家发展进步,虽然开始能收获掌声和谢意,但假以时日便仍被那些曾经饱受惠泽的国民视为帝国主义,好像时刻要从他们身上掠夺财富。……(这种敌对情绪)并未因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访华人士的友善态度和杰出贡献而有所减轻。……总是有人假定我们就是带着优越感去教导中国人要“用我们的方式”立身行事。(David Kinley Report to President H.W. Chase, “Some Cursory Observations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Sund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China and Japan,” 8 June 1932, President Harry W. Chase Subject File, 1930-1933, RS 47/5/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 )
这段评价饱含同情与无奈,却也提出了美国教育对20年代中国的影响甚为有限的疑问。
三
大卫·金利提交了一份清醒严肃的报告。此时恰逢美国“大萧条”爆发期间,伊利诺伊大学随之紧缩财政,接踵而来的还有美国外交政策和公众态度日益深重的孤立主义倾向,再加上学校高层对中国(及亚洲)失去兴趣,以及一些其他方面的紧迫问题,伊利诺伊大学就再没有为建立与亚太地区的联系而实施新的举措或启动新的计划。1930年以后,伊利诺伊大学中国学生的人数逐渐减少,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由于中国政府又开始向美国输送大批留学生才得以恢复增长。但这种情形并未持续太久,1949年后,这一波留学潮便戛然而止。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在冷战背景下形成了长期敌对的状态。在此期间,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成为留美华裔学生的主要输送地,其中部分学生来到伊利诺伊大学。与前面两批中国留学生一样,大部分来自台湾地区的学子都选择攻读理工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只有少数人另辟蹊径学习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其中较知名者如曾经摘取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李安(戏剧学学士,1980)。
到了1978年,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复苏,在经历了近30年的隔绝之后,第三次留美潮应运而生。最先来到美国的多为访问学者,直到1981年至1983年期间,终于有不少公费和自费留学生赴美攻读研究生。伊利诺伊大学不属于全美第一梯队的精英学府,因此一开始并非中国学生的首选。当时,大多数美国顶级研究型高校都对重新获得与中国学术界开展文化交流的机会表现积极,竞相争取最优秀的中国生源,但两国之间的校际交换项目还是进展缓慢。而伊利诺伊大学以其与亚太地区的历史渊源,在中国赢得了开路先锋的美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的无机材料专家严东生(1918—2016),曾在1949年获得伊利诺伊大学陶瓷学博士学位。他在给时任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的斯坦利·依肯贝瑞(Stanley Ikenberry, 1979—1995在任)的信中写道:
伊利诺伊大学因其在诸多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杰出贡献而(在中国)久负盛名,校方也一直善于增进各类学术团体和科学家群体之间的互动与友谊。……我自己也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友,1949年我取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那里工作到1950年。如果能由我负责接待从母校来访的代表团,那对我来说必将是莫大的“荣幸”。(Yan Dongsheng Letter to President Stanley Ikenberry, 12 August 1983, Administrative Subject File, 1932-2005 RS 7/1/7-30, ibid)
严东生于1983年给斯坦利·依肯贝瑞校长写了这封信,正式邀请他率伊利诺伊大学代表团访问中国。
依肯贝瑞校长接受了邀请,但他没有像大卫·金利校长那样留下文字资料,所以我们无法获知他在中国的见闻和感触。无论如何,1983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允许自费留学,伊利诺伊大学以其出色的科学和工程专业,吸引了很多中国学生的目光。如同之前的两代留学生,这一批中国学生也几乎全是研究生,他们大多经济拮据,只能想方设法节衣缩食,以便能寄钱回国贴补家用。2000年以后,随着大批中国学生远赴海外就读本科,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改观。在美国,尤其是2007年到2008年之后,中国留学生的数量突飞猛进,这也体现了国内中等收入群体的日渐壮大。到了2013年至2014年,中国留学生达到28万人,占美国高校外国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本科生人数大幅增长,几乎占中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之多。有鉴于此,批评界纷纷谴责美国高等教育将中国学生当成了主要的消费者。事实上,在一个教学和科研面临财政危机的时代,支付全额学费的中国本科生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很多大学,使它们得以继续保持教育平等观念和学术竞争力。但是,在这些受惠于中国学生的高校中,用来帮助中国学生适应不同教育文化理念的相关服务和设施却寥寥无几。(案例请见,Bethany Allen-Ebrahimian,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300000 and Counting,” Foreign Affairs)
伊利诺伊大学拥有近5000名中国学生,在全美高校中名列前茅,因此成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发展态势的晴雨表,常年占据此类新闻的媒体头条。尽管如此,在与中国开展学术交流乃至建立长期联络方面,它反倒是显得踌躇不前。举例来说,某私人基金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资助一个人文社会科学交流项目,每年在十到十二所中国高校中选定若干学者来伊利诺伊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科研工作,近期却决定予以中止。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校方高层对是否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加强合作,越来越犹疑不决,特别是曾经有一个原定召开于南京大学的所有参加过交流项目的学者的研讨会,原本已筹备多时,却因伊利诺伊大学校方在最后一刻取消而前功尽弃,这样的变故更让该基金会心生疑窦,最终不得不偃旗息鼓。而另一方面,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也面临着多重挑战: 如美国高校不断深化的财政危机,美国政治文化的二分对立和种族矛盾,以及自身在校园内外的“被种族化”(racialization) 处境,无不令许多中国学生不知所措。
早在1912年,埃德蒙·詹姆斯校长曾与美国总统塔夫脱和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共同担任“美国中华协会”名誉副主席。他获此殊荣之下的满腔豪情不禁跃然纸上:
我们伊利诺伊大学拥有多名中国学生,足足四五十人之多。他们都能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来充实自己。其中不少毕业生回国后都为社会、为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Edmund James Letter to Major Louis Livingston Seaman,4 November 1912, President Edmund Jame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04-1919 RS 2/5/3-3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s)
20世纪初,埃德蒙·詹姆斯校长及其继任者大卫·金利校长都以其先见之明和独出心裁探索了以美国教育培养中国学生的方式方法,他们开设的英语课程和外国学生办事处都曾有效地帮助中国学生适应全新的文化环境,而这样的良苦用心也为伊利诺伊大学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赢得盛誉。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已经从当初那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一方面在数量上早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在现实中面临的重重困境却又一如既往。毋庸置疑,埃德蒙·詹姆斯和大卫·金利两位校长为了使伊利诺伊大学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完成了太多创举,特别是开创了将教育作为一种“软实力”来影响两国关系的经典案例,既具有筚路蓝缕的先锋意义,同时又凸显出难以规避的局限性。重新梳理这段遮蔽已久的历史,可以在中美关系史、中美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留学史等多个维度上,发现伊利诺伊大学特有的示范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研究。
作者: 傅葆石(作者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翻译/万若嘉 王羽)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