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湛舸小说集《莫须有》近日由世纪文景出版,本书围绕南宋“莫须有”冤案,以岳云、赵构、秦桧、岳雷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进入同一段历史。作者将史料化为充满感性力量的叙事,在既定的历史框架下再现了不同人物面对多重抉择与后果时的复杂心理。书中包含六篇视角各异但互有联系的小说,其核心人物是死于23岁的岳飞之子岳云。在少年的目光中,脸谱化的英雄还魂为尘世中人,注定被碾碎的蝼蚁展现出浓墨重彩的生命情境。

《莫须有》
倪湛舸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较之小说写作者,倪湛舸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学者、诗人。她自称写小说这事儿,在她的世界里,起因是“中邪”。《莫须有》的写作早在十余年前开始,《断云微度》《衰草连天》两章的雏形《微云衰草》最先写成,而后《蓬窗睡起》的一部分发表在2008年的《小说界》。直至2021年,经过数次修改,《莫须有》全书方才完稿。
倪湛舸曾反复阅读《说岳全传》,她发现钱彩把历史放置在一个神话框架里,历史人物是神话人物转世后的化身,他们的经历不过是某个浩大秩序里的微小环节。钱彩把岳飞呈现为佛前大鹏金翅鸟的转世,岳云是跟随他下凡的雷部正神。然而,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已成为祛魅的、有历史而无神话的世界,通俗小说所努力覆盖并消解的岳飞父子的悲剧,终究还是无法被覆盖并消解的。倪湛舸说:“为此,我感到痛苦。出于这种痛苦,我想要想象历史中的而非神话里的岳云,想要作为另一个无可奈何的普通人去心疼他,去体谅他浮沉于世的痛苦,想要从早已封闭的史料里打捞出曾经鲜活的生命,想要告慰被伤害的少年和与他共同受难的人:千年后,我们仍然没有忘记,少年心永不悔改。”
关于岳云的历史记载不多,在《说岳全传》等作品中,他的形象并不复杂:一个骁勇善战的少年将领。倪湛舸想要冒险尝试的,是参考寥寥无几的史料,将岳云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文学人物。“为了重塑岳云,我倒是想要借用《说岳》里的那股神仙下凡的‘神气’,把‘神气’重新阐释成脱俗出尘之气,写出岳云生逢乱世的创伤、直面虚无的洞彻以及为自己也为他人寻求救赎的挣扎。所谓的少年心,不是神仙俯瞰人间炼狱的淡然,而是小人物烈火灼身时的看穿和看不穿,看穿的是权力和欲望,看不穿更放不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依赖与交付,比如父子、同袍甚至陌生人之间的情义。”
《莫须有》中也有赵构、秦桧的叙述。凭借这些多元的叙述视角,作者试图超越“莫须有”作为岳飞个体悲剧的解读,进入更宏阔的历史与社会关系,从宋、金之间的复杂互动与两国之间、君臣之间乃至官僚阶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时时变动的消长关系来看待这一事件。他们的故事令读者看到,在古代的君臣秩序之下,岳飞的性格决定了他几乎有着难以避免的失败结局。
倪湛舸凭借出色语言掌控力和深厚的学识,将当代人的通俗浅近的语言和古典的情境与趣味糅合在一起,既有军中少年的洒脱、放荡不羁的口吻,也有面对虚妄世事又知其不可为之的英雄之苍凉与壮美。
作家李修文是《莫须有》最初的读者之一,他在十余年前就读过这本书最早完成的篇章。李修文对这部作品不吝盛赞:“多年以来,我一直是这部小说的追随者,它清简利落,又幽玄悲怆,寓波诡云谲于残山剩水,寄江山兴亡于一己之身。天地不仁,藕断丝连,生也生他不得,死也死他不得,树倒猢狲散,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一一多少生与死的电光石火,多少中国人的一场大梦,尽在这哀矜与慈悲互织的《莫须有》之中。我深信,它是我们时代最迷人的小说之一。”
作家赵松则认为:“岳飞的故事早被评书打成了铁,可倪湛舸偏偏能另起炉灶把它化掉,让尘归尘、土归土,把脸谱化的悲剧英雄还魂为尘世中人。她能始终含住那口最初活泼渐次低迴沉郁的气,让它升起、贯通,再滑落心底,最后化作一泓深冬清水——生命旺盛,难免徒劳,英雄也是玩偶,不朽盛名,抵不了悲哀半分。”
此外,《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的作者、宋史学者虞云国也是它的读者。历史写作者刘勃欣赏它的“功力深厚而无学究气,诗情洋溢而无头巾气,精雕细琢却又有土地中生长出来般的诚挚”。漫画家早稻读完了全书,为倪湛舸富有灵气的文字所触动,为其创作了封面插画。
据悉,《莫须有》是文景原创文学书系“文景·潮生”在2022年推出的首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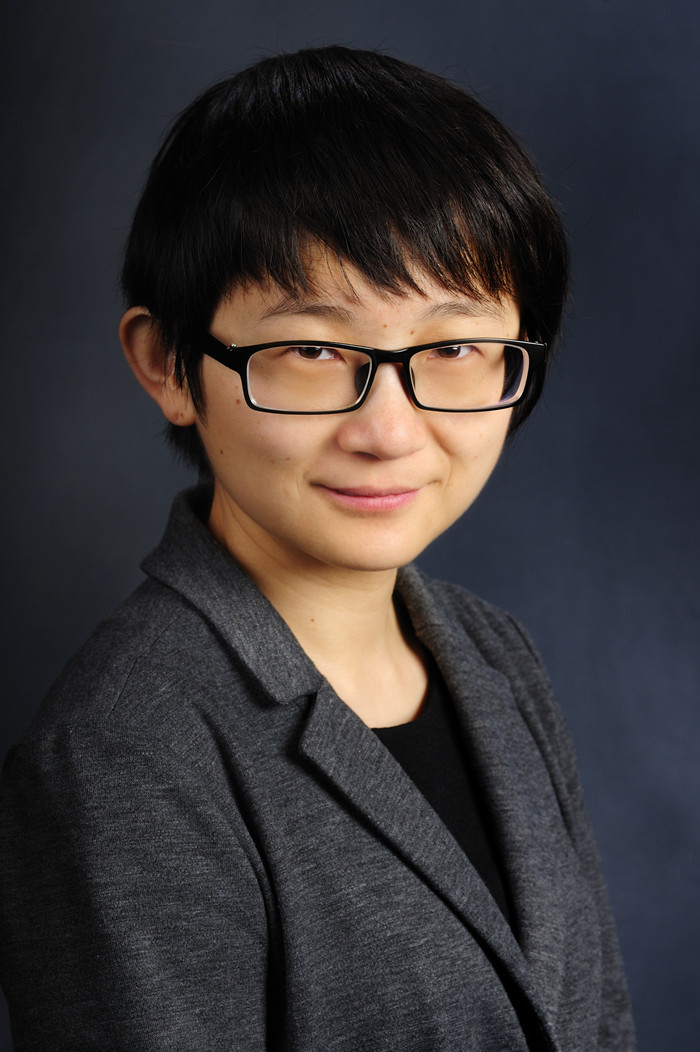
▲《莫须有》作者倪湛舸
>>内文选摘:
我记得你们
退兵后,父亲又带我去临安,见了官家便极力请辞官职, 官家不许,还要加封我,正好借口强留我在临安养伤。父亲匆匆回了鄂州的军营,小勺带着孩子过来,弟弟也跟着,倒是一家子送上门来给朝廷做人质要挟父亲。张敌万托弟弟带来那本《正蒙》,说他看到这书就浑身不自在,正好扔给我以绝后患。我把那书随手甩在一旁,拉着弟弟教他划拳:“读个屁书啊,我们兄弟俩时来运转,从此也要过衙内的悠闲日子!”弟弟还没习惯新家,成天缩着脖子哭丧个脸:“临安的冬天真冷。”“等等吧,一眨眼就开春了!”
果然,雪下了又停,停了又下,雪渐渐变成了雨,雨里先是夹着雪,再扭扭捏捏地缠着风,终于痛快淋漓地往下泼水,浇醒了蛰伏已久的大魔头。开春了,到处都是蠢蠢欲动的草,草从墙角的砖缝里钻出来,在野地里推开去年的落叶露出头,遍地的草不动声色地染青远山,把整个世界都捏在掌心。绍兴十一年的春天,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后一个春天, 一岁一枯荣的草,也不知道见过了多少我这般的蝼蚁,明白自己微不足道,我并不羡慕这恒常的春草,我只是怕它。
初春时兀术贼心不死又来进犯,父亲配合着张俊和韩世忠把他赶了回去,官家见局势已趋安定,赶紧把三大将都召回临安,削了他们的兵权都攥在自己手里,遂了长久以来的心愿。父亲得了个枢密副使的虚职,也不争,也不闹,默默地升了这官,一腔愤然说不出口,只能成日披襟作雍容状, 与他一同明升实降的韩世忠还学文士的样子包头巾,两人面对面坐着喝茶,倒像是一对落第书生。我特意跑去枢密院观摩,想笑又不敢笑,刚要开溜就被韩世忠一眼瞅见:“哟,云哥儿来了啊。”父亲看见我就烦:“这个祸害!我后悔把他拴在身边!”我再傻都还是听懂了他的气话,他后悔害我也陷在这摊浑水里与之沉浮。
我从鄂州搬来不久,家里懒得张罗什么,就凑合着过, 父亲来了之后吩咐我们继续节俭着,什么都别添置,反正很快就要离开临安找个地方种田去,他觉得庐山脚下不错,打算把继母和那边的弟弟们也都从鄂州接过去。弟弟高兴得眼睛发亮,我却提不起精神附和父亲的美梦,他早就对官家死了心,以为过些时日辞了官就能脱身,我却觉得看似软唧唧的官家实在可怕,讲和收兵权这些难事他居然都做成了,他就算没本事,狗屎运却充足得很,谁知道他还在暗地里谋划些啥,想想就心惊。做了鬼的我回头才明白,原来他为了巩固到手的兵权得翦除任何可能的威胁,张俊是饭桶,韩世忠在他先前落难时曾经救过驾,那可不是只剩父亲任他宰割,更何况父亲要报的那个国跟他的国南辕北辙,这可是他眼里的不忠!
还没做鬼的我上有老下有小,白天得满脸堆笑,天色一黑,心底便有浑水往上涌,憋在胸口,连透气都辛苦。小勺忙着带孩子,没空理我,我也不敢多见他们,只能窝在书房读书写字,有时候彻夜秉烛,父亲见家里蜡下得特别快,问我怎么突然变得好学,是不是在门上磕了脑袋把那些个歪七扭八的筋给磕正了。我捡起那卷被我随手甩开的《正蒙》答:“张载就在我这般年纪弃兵从文,我倒是真想学他。”父亲点头:“有些真学问也好,就怕学成了朝里的那群乌鸦文官。”“阿爹尽管放心,我从军从得稀里糊涂,读书也不懂什么经世致用,无非是心里翻腾,想求个片刻安宁。” 话虽如此, 心里若真是静不下来,别说睡不着觉,就连书都读不进,只能半夜偷偷牵马出去,在西湖边一路狂奔,奔到山穷水尽,指间纠结着被汗水浸透的马鬃,冲如磐的夜色无声呼告:“我记得你们,你们可记得我?”
我记得你们,死去的孤魂和活着的流民。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