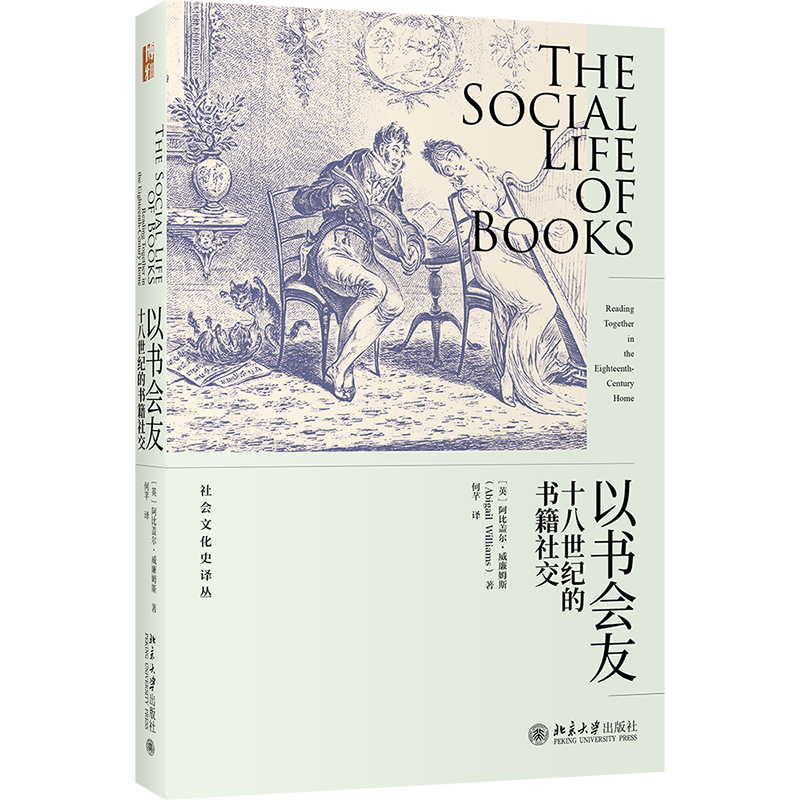
《以书会友:十八世纪的书籍社交》
[英] 阿比盖尔·威廉姆斯 著
何芊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18世纪的英国,由于印刷业的蓬勃发展,书籍成为自我提升、家庭娱乐和邻里社交的重要工具。本书聚焦18世纪英国中产阶层的阅读生活,关注他们如何获取并阅读书籍,阅读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以及大众阅读偏好与书籍出版甚至文学体裁发展间的互动。重现了18世纪的阅读场景,进而使我们窥见当时的社会心态与文化风尚。
>>精彩试读
家中装点
1802年4月15日,多萝茜和威廉·华兹华斯兄妹俩在湖区的一次随意闲行,成就了文学史上最意义非凡的一次散步。那是狂风大作的一天,他们穿越了阿尔斯沃特湖附近的山丘,强风呼啸,水雾缥缈,山泉掩映在树篱之中。途经高巴罗公园时,他们先是看到了几株水仙花,继续走着,又发现了一大丛,沿湖簇生,郁郁葱葱,随湖岸蔓延,与乡道同宽。多萝茜的日记里写道:
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水仙花,它们怒放在爬满青苔的石块之间,有的花冠耷拉在石头上,仿佛是靠在枕上小憩,其余的都在摇曳、摆动和起舞,如同是迎着湖风发出了真诚的笑声,它们看上去如此欢快奔放,光彩夺目而又千姿百态。
兄妹两人继续散步,他们在一家酒馆饱餐了一顿火腿和马铃薯。按照多萝茜的叙述,晚餐之后,“我下楼看到威廉正坐在炉火旁。他起身走到窗前堆放的藏书前,拿出了恩菲尔德的《演说者》、一部文选以及康格里夫某出戏剧的散卷。我们喝了一杯热朗姆酒加水——我们把盏言欢,并为玛丽祝祷。”

当天还有很多值得说道之处。多萝茜的日记原文比这里摘录的内容更详尽,为理解“我如行云独自游”提供了基础,这是华兹华斯两年后写下的传世之作,水仙花被描绘成了在郁郁独行中令诗人欢愉的伴侣。这或许是英国文学中最有名的一首抒情诗,它展现了浪漫派诗人对幻想与自然的讴歌。然而,除了学术界的小圈子,多萝茜的日记并不为大众所知。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诗与日记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活动。通过描写水仙花,华兹华斯强调的是一种唯我的感受:沉溺幻想时的孤寂、专注与沉默,以及“闪现于心眼的”画面。但这首诗背后的多萝茜日记却记录了散步与偶遇水仙花之间相得益彰的乐趣,日记的结尾更是家庭内部共同的娱乐活动。在漫长的外出结束后,兄妹两人坐在酒馆的炉火边,从书架上随便抽出几本畅销的诗集和戏剧,一边啜饮朗姆酒一边朗读。多萝茜在日记里写到自己时常对着兄长朗读,这就是一个关于共同分享的故事。

尚·欧诺列·福拉哥纳尔 ,《读书少女》,1776
诗歌与文学是个人的自我表达方式,阅读则成为个人灵感之来源以及对自我心灵的探索,威廉·华兹华斯与其他浪漫主义作家有力地塑造了这种对文学作品的看法。在他们之前与之后的数个世纪中,诗人、艺术家和哲人们通过强调文艺创作与知识生产中独处的重要性,一直“在描写着自身的孤独”,一位历史学家如是评价。然而,共同阅读与文学活动在我们的文化史中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如果多看几行多萝茜·华兹华斯当天的日记,我们能从她描述的散步与阅读中了解到什么?他们的经历究竟是共同的还是私人的?相伴读书与个人阅读是否一样?这些问题不断回响在交际阅读的历史中。多萝茜的描述显然说明,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会受到阅读时实际场景的影响——在这里,康格里夫戏剧“散卷”的价值更多在于它如何被阅读。难忘的一日外出之后,喝着朗姆酒,有亲人相伴,如此阅读场景比书卷本身的内容更有意义。我们看到了出其不意、令人意外的选择:华兹华斯从酒馆书架上随手取下的一本书就契合当晚的主题——这并非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意在增进学识的安排。读了什么并没有如何去读那么重要。这个故事也展现了汇编文集的重要性:多萝茜提到了另一本书,威廉·恩菲尔德的《演说者》就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本文集。这本书收录了不少诗歌与散文,旨在提升青年人的道德水平和社交技能,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本书里有不少朗朗上口、值得一读的节选篇章,常被用来消磨午后与晚间的家庭时光。多萝茜的共同阅读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文学体验,其中地点、同伴、食物、酒水与易得性都发挥着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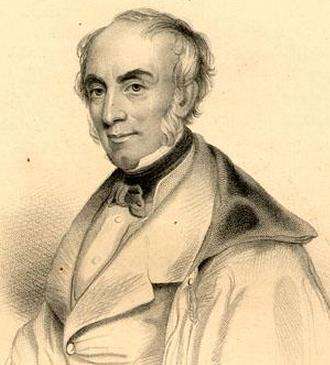
威廉·华兹华斯
交际阅读的历史把书籍重新放回到生活与家庭中,使我们得以完整地理解文学。其中,理发、乘坐马车以及口吃儿童都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能够看到,读者的希望、选择、限制以及顾虑如何影响了三个世纪之前书籍的意义。某些现实与文化的情境——有限的灯光、原始的眼科医学、增多的空闲时间以及显摆教养的欲望——都影响着书籍被使用的方式。交际阅读也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18世纪文学史的诸多特点。有时,相伴而读是一种预防手段——尤其针对当时刚流行起来的散文小说,大众普遍认为,这种文体代表了危险的兴奋。随着小说这种文学载体逐渐兴起,围绕它的争论一直很激烈,小说的诱惑性也始终是争议的内容之一。奥古斯特·贝尔纳·达杰希的名画《读〈哀绿绮思与阿伯拉书信集〉的女士》就有力地唤起了人们对小说魅惑力的印象。事实上,画中女士可能无法代表18世纪小说的一般读者。根据书籍史学者最近的研究,体面的中年男性更有可能是当时小说的主要受众。但我们却可以看到,在这幅画作中,女士流露出道德松弛的神态,很可能是未受管束地阅读小说所致。交际阅读能够纠正这一点,它让家长得以重新掌控家庭内部的阅读生活,引导年少无知的家庭成员选择更恰当的文学载体。

Auguste Bernard d’Agesci, Lady Reading the Letters of Heloise and Abelard, c. 1780
《读〈哀绿绮思与阿伯拉书信集〉的女士》 (1780)
书籍会被大声朗读,将这一点纳入考量,我们就能开始了解书籍史中的口述形态。分享式阅读无论在书籍的物质形态上,还是书籍的接受史上,均有所体现。印刷尺寸、书籍版式以及文风类型都要按照是否便于表演的标准来考量。字体大、摘录短、片段式的结构、充满格言警句的段落,都是为了让文本变得更轻便,更适合在有人做伴时朗读。关注出版物的表演与口述性质,这让我们得以从新角度理解18世纪读者如何看待当时的文学作品;也迫使我们从观众而非读者的角度来理解文本,就像卓越的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说,文本乃是“见不如闻”。伊丽莎白·汉密尔顿是一位年轻姑娘,她出身于18世纪80年代斯特灵郡一个缙绅家庭。在她看来,最好的散文应当是那种“无须耗尽气力就能贯读下去”的文章,她说出了当时的主流看法。读者的选择很可能为句式结构和演讲方式之间的关联所左右,但以往对18世纪文学史的研究常常忽略这一点。口述形态也会带来不小的影响,感伤文学的畅销也与此有关。哈丽雅特·马蒂诺曾提过,朗读使文字有了全新的魔力:“我记得母亲和姐姐从奥佩夫人家回来时浮肿的眼袋与脆弱的心情,她们在那儿听女主人激情澎湃地朗读了一个晚上的《脾气》。她们看到印刷版后,简直难以相信这是同一个故事。”这些要素有助于我们理解18世纪文学中的某些反常现象。詹姆斯·麦克弗森的莪相诗(Ossian poetry)引发了不可复制的轰动,这是否应当归功于深沉的吟诵与激昂的朗读?感伤小说的风行,是否就因为它充当了18世纪社交场合中令人潸然泪下的焦点?
本书将带你探索一个少为人知的世界,它将带你进入中等阶层和下层士绅家庭,了解他们日常如何使用书籍,如何在家中相伴朗读。虽然教室、教堂、酒馆、咖啡馆以及大学都能提供朗读之所,但是家庭却尤为不同。家,既是公共场所又是私人宅邸,既拥有私密感又呈现了社交性。这是一处既可闲暇又能工作的地点:既能助你遁世,又能为入世做准备。重新审视家庭阅读的繁喧世界让我们了解,书籍如何通过多种方式将人们联结在一起。考察家庭空间的阅读生活,我们就能体会,虔敬、自抑、自修、无礼与社会交往之间的错综杂糅如何塑造了18世纪社会。人们享受的文学形式多种多样,除了我们熟知的传统书籍,还有从手札到“滔滔集”这类很多我们现已不太了解,但却流行一时的形式。除了虚构作品,人们也会选择一些非虚构的著作,尤其是历史和宗教类作品在家中大声朗读,不过教导人们如何在家阅读的指南书,仍主要以文学作品作示例。人们从中学习如何提高朗诵技巧,如何在为大家朗诵时利用肢体语言传递情绪。人们抄录并分享最爱的诗篇,朗读流行小说里的对白,朗诵戏剧里感人或滑稽的片段,他们还相互借阅布道书册,读后一同讨论。他们使用在整个村子或家族中都传阅过的破书残卷,也会购买一些新近可得,供家庭使用的汇编文集。他们会在书房里放置沙发,或是在壁炉周围摆上书架,这些布置都令读书成为了交往环境中的享受。
>>作者简介
阿比盖尔·威廉姆斯(Abigail Williams),历史学者,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教授。著有《诗歌与辉格派文学文化的创造,1681-1714》。
作者:阿比盖尔·威廉姆斯
图源:网络资料图片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