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继《流溪》后,小说家林棹第二部长篇小说《潮汐图》首发于《收获》2021年第五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故事从19世纪的广州开始,一只雌性巨蛙出现于珠江水上人家,它从船底时代过渡到了鱼盆时代。因苏格兰博物学者H的诱捕,它被关进了广州十三行,从此知道了画,体会了“身处画中”;接着阴差阳错地,来到澳门,重遇H,被当作明星宠物与珍稀物种住进了好景花园;鸦片战争前夕,H破产而自溺,好景花园如大梦般消失。一个下大雪的冬天,巨蛙逃出动物园,来到一个湾镇,度过了最后的十年。
这部颇具魔幻色彩的小说,拓宽了怎样的文学书写可能性?朵云书院旗舰店分享会上,文学评论家黄德海与刘欣玥、《收获》编辑朱婧熠对谈时指出,《潮汐图》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小说,它目之所及的是现代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读者不必把小说仅仅理解为‘历史小说’,也不要因为这部有粤语方言的融入,就简单贴上‘方言小说’标签。我们今天依然面临着语言的转变,我们也只是潮汐图的一部分,或者说,水一直流到了现在。”

合上林棹新作《潮汐图》的时候,我在潮涌般的快乐中品尝到了一丝隐秘的羡艳。快乐自是不必说,羡艳则源自作者庞大充沛的想象力,和对语言近乎野蛮的直觉。
还记得初次阅读林棹,是她的处女作《流溪》。作为成长在岭南的女性,在翻开《流溪》的第一个瞬间就可以轻易地和另一个岭南少女相认,然后追随她逡巡在亚热带的密林、季风与潮湿里。如果说《流溪》是岭南的今生,那么《潮汐图》大概是岭南的前世。
这是一个由虚构生物巨蛙讲述的故事。巨蛙说,“我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是生吞。”巨蛙通过生吞水中之物岸边之物认识了珠江、贫贱和汉字。于是,故事的语言风格亦犹如生吞。巨蛙不是作家,她不需要懂得何谓剪裁,何谓详略得当,不需要区分故事的主干或细节。她生吞下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所有,无需咀嚼,不经消化,然后宛如产卵一般泻于纸面:无论贵或贱、生或死、甚至有机或无机的一切,挤挤挨挨,黏腻密集得让人既恐惧又好奇。巨蛙不是人,她不做“万物的尺度”,因此她生吞之后模糊了一切事物的边界。她口中的颜料水彩“吃棉纸”,“自由地吃过去、吃开去”“吃出老榕须格局”;她腹中的滚滚浓烟“发围,挺起孕肚”。
我们常说雕塑和舞蹈是空间的艺术,因为身体和物质材料会占据一定体积的空间;而音乐、小说和电影是时间的艺术,因为它们都是线性排列的,占据一定长度的时间。因此舞蹈完全可以脱离音乐而存在,而我们偏爱为电影配上音乐,热衷把小说改编成影视。然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潮汐图》是一部拒绝被影视化的小说。它的画面感当然很强,任何人看完描写鸬鹚胜的鸬鹚捕鱼的段落,都会赞叹其“历历在目”“栩栩如生”;观影经验丰富的读者甚至马上就可以想象出如何运镜如何剪辑,以还原出海皮自然史又或者是好景花园。
但,这样的影像便不是巨蛙生吞下的世界了。林棹通过巨蛙的口腹赋予了语言一种空间感,或者说,《潮汐图》更像是一件巨大的装置艺术而非一部小说;不是读者在阅读文字,而是语言笼罩、吸附、包裹甚至圈禁了走进装置的读者。因此,如果有人害怕或拒绝,也在情理之中。用一个更浅显的比喻:《潮汐图》是一座语言的博物馆,字眼、词汇、句子和段落既是陈列之物又是建筑材料。再换句话说,在此处,语言本身就是意义、价值和美。也正因如此,小说在这里回归了其作为文学的本质。

那么,这是一部所谓“形式大于内容”的、炫技的小说吗?并非如此。巨蛙作为叙事者带来的不仅仅是生猛饱满的语言风格,同时带来的也是奇特的叙事视角。我们当然会想起卡夫卡和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由于格里高尔拥有曾经为人的记忆,甲虫提供了一种虽然陌生化但依然属于人类的视角。巨蛙诞生之初是尚未定型的动物,是通灵的怪兽,后来是被豢养的宠物,是被圈禁的珍奇,最终是孤绝的生物;虽然终生与人同行,但不曾有一日为人。因此,异类的视角——去人类中心化的视角在巨蛙身上获得了可能。
在异类之眼的透视下,19世纪欧陆博物学的蓬勃繁盛暴露出了狰狞残酷的爪牙:“帝国人把人捆起像木料,推入舱底塞满”,但“他们还为植物定做专用船舱哩”。这是发达对落后的殖民,在这里,巨蛙当然是“反殖民的和反讽的”。如此说来,巨蛙意味着原始的野性、返古的冲动?似乎也并非如此。巨蛙是兽,但巨蛙也是灵;巨蛙不是人,但巨蛙与人类共享了语言、情感和记忆。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可以,弗兰肯斯坦造出的生物会怎样讲述自己的故事。两百年后,林棹自如地扩张了玛丽·雪莱的野心,巨蛙开口说话,于是我们得以再次探寻文明与野蛮的辩证。
故事中时常会出现第二人称代词“你”。“你”既是故事中参观巨蛙19世纪男女,也是书页前阅读故事的21世纪的我们。这是巨蛙与人类的对望与对话。巨蛙一边表演野蛮一边观看人类,洞察了赏玩野蛮正是文明最大的傲慢。然而,巨蛙依然是文明的学徒:冯喜给她讲古,H带她游历,茉莉·钟斯教她握笔,陌生的小女孩赐她圣祝。人类予以巨蛙知识和情感的滋养,巨蛙得以拥有自己的“成长史”,得以永恒葆有并封存最初的芫女和舢舨。随着故事的行进,小说的句子和段落越来越长,那是因为巨蛙逐渐拥有了“大忧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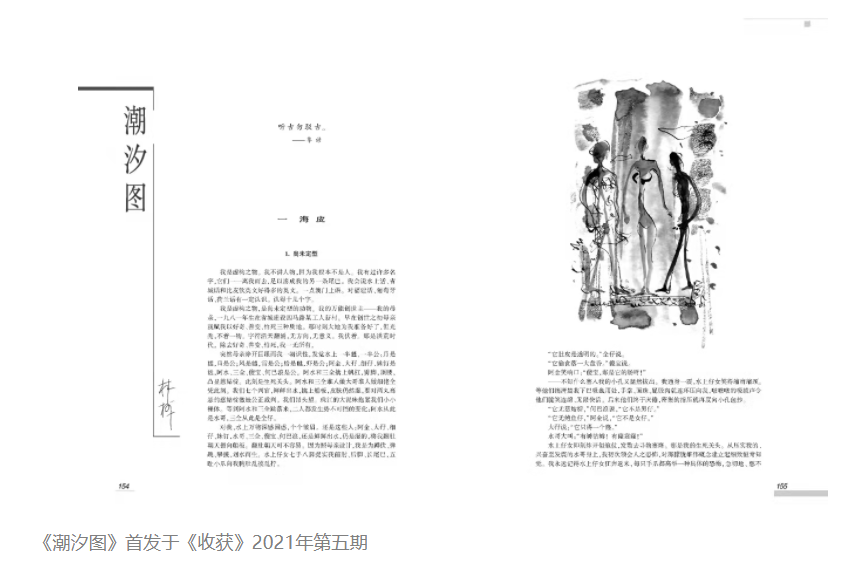
最值得玩味的是,巨蛙在动物园冷静地自剖:观察丹顶鹤与死神的缠斗带来关乎“审美、新知,和别的什么说不上来的”“自我感动的欢愉”。然而,当巨蛙逃出动物园遇到了更为远古的粉头鸭、恒河猴和袋狼时,她觉得它们“怪”,她表现得“很有教养”,她“用人的姿势坐下”,询问它们人的踪迹。巨蛙对它们不感兴趣,在生命的终点她仍然自觉地与雪达犬保持灵魂的界限,因为雪达犬把教授与女助手埃莉诺关于地球的辩论当成催眠曲。
我们更不要忘记,巨蛙的挚友冯喜,是一个“要搏老命去”“远处地方”的画师。实际上,从珠江沿岸漂流到欧陆中心的巨蛙,实现的正是冯喜的一生所求。巨蛙是人类冯喜的兽影。一个岭南人“尽全部努力去想象冰川、白夜和极寒”,想象的不是远处地方的蛮荒,而是遥远的新知;“出海病”不一定是开疆拓土的野心,也可能是上下求索的欲望。好奇,或许正是文明的本能。
《潮汐图》的扉页有粤谚“听古勿驳古”,开篇第一句则为“我是虚构之物”。作者坦坦荡荡地宣布虚构的“特权”、故事的“特权”,正如太虚幻境的门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其实,这是人类的童年,或者说童年的人类曾经最热爱的那种故事——是神话又是历史,是传说又是寓言。(原题《当巨蛙生吞文明》)
作者:姜瑀(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编辑:许旸
图片来源:出版方
责任编辑:宣晶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