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创作是作家安身立命的职业,阅读则是他们离不开的滋养。这些年的中国文坛,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走出书斋和课堂,乐于向大众讲述他们读书的体验与心得——王安忆的《小说家的十三堂课》、毕飞宇的《小说课》、鲁敏的《虚构家族》、张悦然的《顿悟的时刻》……他们讲得绘声绘色,大众听得有滋有味,毕竟,由作家谈论文学,再没有比这更顺理成章的了。



原本文学阅读是件很私人的事儿。有人把它当成闲暇时光的消遣、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将它视为窥探世界的渠道、体味百态人生的途径;有人拿它作为职业,客观理性地解析作品的意义,正襟危坐地点评作家的风格,条分缕析地总结文学的规律。文学评论自然也是个性度极高的活动,毕竟一千个读者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人热衷直觉式的点评,有人享受共情化的代入感,有人则受到各种批评理论的加持,善于说理性的论证。
然而作家这群人,是资深的文学爱好者,却不是学院派的文学批评家。文学阅读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需求,他们的文学评论比不明就里的直觉评判更能洞察作品深层的玄机,比感同身受的情感共鸣更具有旁观者清的冷静,比讲究逻辑的理性论证更注重描绘阅读的主观感受。因为他们深谙文学的真相,熟知写作的脉络,他们有着明确的审美立场,在评价同行的时候尽显个性的锋芒,或饱含溢美之词,或暗露讥讽之语,或直抒批驳之言。
于是,作家笔下的文学评论,不仅带我们深入被评论对象,更为我们打开了窥探作家本人的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挑剔与爱憎分明,他们对文学、对文字的高度敏感和细致入微的解剖,还有他们对文学不可取代的地位的坚定信心。如果说作家的创作显露的是他们的“第二个自我”,作家的评论则以更直观的方式展示了本真的自己。
世界文学史上,不乏经典作家留下的评论作品,《普通读者》《文学讲稿》和《小说的艺术》尤其被广泛阅读和讨论,已然成为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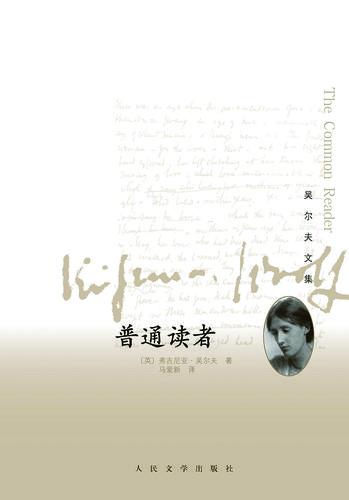
《普通读者》:弗吉尼亚·伍尔夫使我们精准定位并无限走近那些遥不可及的人物
打开《简·爱》时,我们也不禁怀疑会发现她的想象世界像这荒野上的教区一样古旧过时,带着维多利亚王朝中期的气息,只有好奇者才会去访问,只有虔诚者才会去保存。可是只读了两页,一切疑问都打消了。——摘编自《普通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身为20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曾撰写了五百多篇文学评论文章的伍尔夫,自称只是一个“普通读者”。但一个崇尚阅读带来的纯粹快乐,将读书本身的价值作为终极追求的读者,显然并不“普通”。
她用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审美眼光,为我们架起了一台探测文学经典的望远镜,使我们精准定位并无限走近那些耳熟能详却遥不可及的人物。那个“带着恶意的笑容,与一切狐狸、驴子和母鸡联合,嘲笑生活的盛况和礼仪”的乔叟,那个成功地用文字为自己画像,使“整个灵魂的图像、重量、色彩和边界,包括它的混乱、多变和不完美”得以呈现的蒙田,那个善于描写琐事,却能够“在读者的脑海中扩展,给外表琐碎的生活场景赋予最持久的生命形式”的简·奥斯丁,那个“一打开他的书,就会感觉像海伦照镜子时那样,发现她无论怎样做,都永远不会被看做相貌平平的女人”的约瑟夫·康拉德。
她拒绝以偏概全。为了了解莎士比亚之外真实的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她犹如强迫症一般读了不少“次要作家”的作品,走进了英国文学中一个“极其令人生畏的地带”。她用“痛苦”“纠缠”“折磨”“心烦意乱”等词语形容她与这片“丛林和荒野”交锋时的体验,口无遮拦地抱怨它们的枯燥、浮夸与华丽,以及大幕落下时的愤怒、无聊与乏味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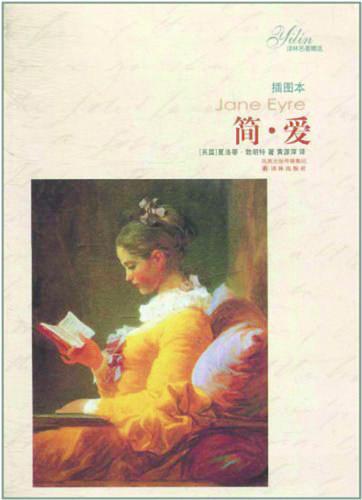
她的眼中容不得沙子。尽管夏洛蒂·勃朗特的激情和愤怒同样令她深深沉浸,但她无不犀利地指出了《简·爱》的局限——“永远是家庭教师,永远在恋爱”。她调侃夏洛蒂的文学世界缺乏“好奇的玄想”,人物不立体不丰满,作品没有想象空间,难以引人深思。在她看来,夏洛蒂的所有力量都体现在“我爱”“我恨”“我痛苦”这几句话中,却从不企图解决人生的问题,甚至未曾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
她用不疾不徐的从容和举重若轻的口吻探讨了许多“搞研究”的学者穷尽一生精力钻研的问题。比如小说家的使命是什么?不是运用精湛的技法,呈现精妙的结构,不是为故事营造无可挑剔的可信性,不是像威尔斯、本涅特、高尔斯华绥那些令人失望的“物质主义者”只关心肉体,而是“表达(生活中)变化多端的、未知的、不受限制的精神(无论它表现出何种反常或复杂性),尽可能少混杂外部的东西”。

《简爱》剧照
她盛赞伟大的俄国作家都对人类精神怀有一种天生的崇敬,无论是细致微妙的契诃夫,还是深邃博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堪称“圣人”的小说家只关注灵魂,他们的人物是“灵魂的容器”,他们的作品是“翻腾的旋涡,盘旋的沙暴,嘶嘶沸腾的喷水口”,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被吸了进去,旋转,盲目,窒息,但同时有一种晕眩的狂喜”。
“我们给予别人怎样去读书的指点,就是不要听从什么指点。”《普通读者》不是文学的权威解读,而是一名意气风发、生机勃勃的“普通读者”为我们描绘的文学阅读应有的“普通”状态:遵循自己的直觉,进入作者的世界,以充分的理解获取印象和感受;运用自己的判断,对形形色色的印象和感受进行梳理和鉴别;得出自己的结论,使那些变幻不定的东西成为明确和坚实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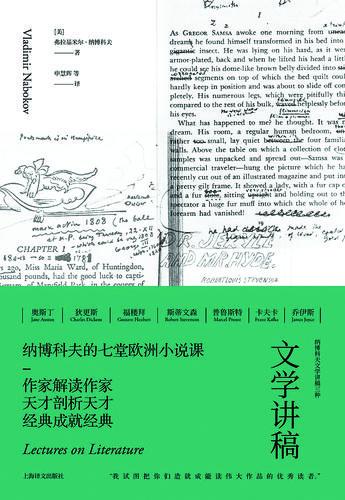
《文学讲稿》: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读文学,就像用显微镜观察蝴蝶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当注意和欣赏细节。如果书里明朗的细节都一一品味理解了之后再做出某种朦胧暗淡的概括倒也无可非议。但是,谁要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思想来看书,那么第一步就走错了,而且只能越走越偏,再也无法看懂这部书了。我们应当时刻记住,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这个新天地,研究得越周密越好。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件同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崭新的东西来对待。我们只有仔细了解了这个新天地之后,才能来研究它跟其他世界以及其他知识领域之间的联系。
——摘编自《文学讲稿》,上海译文出版社

20世纪50年代,康奈尔大学的文学课堂上,纳博科夫一再叮嘱学生:“虽然读书时用的是头脑,可真正领略艺术带来的欣悦的部位却在两块肩胛骨之间。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那背脊的微微震颤是人类发展纯艺术、纯科学的过程中所达到的最高的情感宣泄形式。”
将肩胛骨之间的酥麻滋味视为货真价实的文学之美,纳博科夫显然是一个感官主义大师。在他看来,文学阅读靠的是耳朵听,脑袋想,还有同作者的心灵形成艺术上的和谐平衡,进而感受宣泄心曲的畅快。成为纳博科夫心目中的优秀读者并不容易,需要“有想象力,有记性,有字典,还要有一些艺术感”,需要将赤诚的艺术热情和冷静的科学态度融为一体,需要不断重读一本书。当然,成为纳博科夫心目中的优秀作家更不容易,需要集“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三者于一身,需要把人们熟知的世界打碎后再重新组合,从而独创一个新的天地。

纳博科夫更是一个细节至上主义者。就像他乐此不疲地在显微镜下观察蝴蝶,他同样钟爱用科学家的一丝不苟细读文学,从而拆穿作者的巫术,厘清文本的游戏,发现语言的乐感。在他如炬目光的指引下,我们领略到了无数常被忽视却绝对精彩的细节:比如简·奥斯丁惯常的“特殊笑靥”风格,即在简单陈述事实中悄悄加入微妙的讽刺而达成特殊的效果;狄更斯偏爱的“符咒式的语言”,即如同法庭演说一般,通过对文字公式反复地念诵而使之变得越来越有力量;又如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运用的“多声部配合法”的叙事策略,以及叙述主题在同一章节波浪般流畅地“结构式转换”;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展现的异常丰富的隐喻意象,使其“比喻里还层层套着比喻”;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毫无诗意的正式腔调和噩梦一般的故事内容,两者形成的强烈反差完美地整合了形式与情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实现的时间与人物行动的精准匹配,永远步履匆匆,永远分秒不差。

《包法利夫人》剧照
“所有的小说都是虚构的。所有的艺术都是骗术。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在纳博科夫看来,成就“狼来了”故事魅力的不是在孩子大叫“狼来了”之后真的紧跟了一只狼,而是其背后并没有狼。那个讲故事的人正是凭借在真实世界和夸张想象之间插入了一片五光十色的过滤镜,使孩子故意捏造的恶作剧成了引人入胜的故事,也使孩子终被狼吃了的故事结局产生了警世危言的效果。因此,面对文学作品,纳博科夫一心只想辨明故事如何在变化多端中进展;人物如何在平行和交织中相互作用;作家在精心设计结构时期望产生怎样的效果、制造怎样的印象。
“文学不是思想流派,而是一个个天才的个人”,纳博科夫如是说。但实际上,《文学讲稿》不仅诠释了创作文学所需要的才能,更诠释了解读文学所需要的智慧。纳博科夫让我们更加确信,优秀的作家必然也是一位出色的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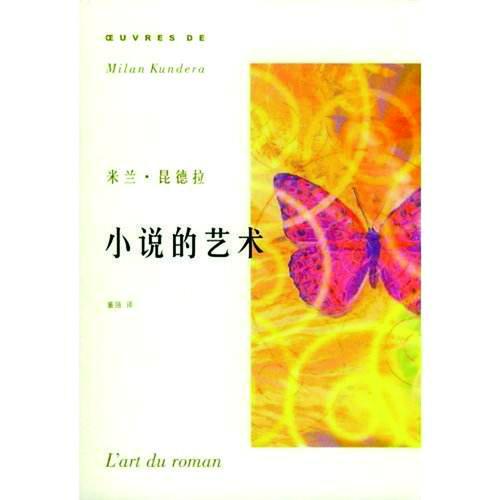
《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用这本书回答了有关小说的艺术本体论问题
讲故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一个说故事人的口吻来叙述;这可以是民俗故事里的匿名声音(“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公主”),也可以是游吟诗人的口吻(如,维吉尔的“我所歌咏的乃是军队与英雄”),或是从亨利·菲尔丁到乔治·艾略特一贯的经典小说中所显露的那种可信、随和、庄重的著者式腔调。
《亚当·比德》一开头,通过一滴既是镜子又是媒介的墨水这个简洁的修辞比拟,乔治·艾略特把写作行为转化为对读者直接、亲密地谈话,邀请我们进入小说的门槛,甚至一头栽入主人公乔纳森·波尔居的工作室。通过含蓄的暗示,她把自己细微独特、注重史实的叙述方法,与充满魔幻和迷信般的令人生疑的展现手法并列对映。关于埃及巫师技法的论述并不具有特殊叙述目的,但是它也并非平淡无趣。毕竟,我们不是只为了故事才读小说,我们读小说还为了扩大知识面、理解这世界,因此著者介入式的叙述方法格外适合包纳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睿智。
——摘编自《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胡塞尔认为人类的危机源于“科学把世界缩小为一个简单的技术与算数勘探的对象,而把具体生活的世界排除在视线之外”时,当海德格尔发出“存在的被遗忘”这一魔咒般的论断时,昆德拉提醒我们:现代的奠基人不仅有笛卡尔,还有塞万提斯;认识世界不是哲学和科学的特权,还有小说。
“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赫尔曼·布洛赫语)昆德拉坚信小说能够触及科技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它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抵抗“存在的被遗忘”,将“生活的世界”置于永恒的光芒之中,并不断告诉我们:“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什么是那些科技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塞万提斯让我们懂得了世界的模糊和真理的相对性,巴尔扎克让我们认识到了人是在历史中扎根的,福楼拜带我们勘察了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土壤,托尔斯泰帮助我们看清了非理性对人的决定和行为的作用,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引领我们探索了时间,那些过去和现在无法捕捉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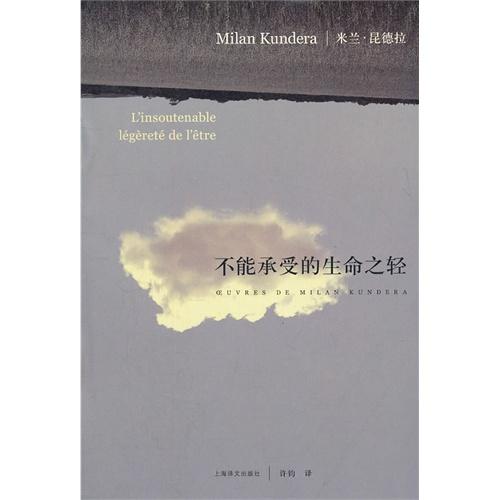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有一句常被人引用的句子:“小说不是作者的忏悔,而是在世界变成的陷阱中对人类生活的勘探。”《小说的艺术》则可以看成昆德拉对这句诗意表达的深入阐释,它回答了一系列有关小说的艺术本体论问题:小说的任务是“捉住自我”,是“研究存在”,小说的深思是疑问式的假设,小说的每一个主题都是对存在提出的一种疑问;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讲述历史,不是预言未来,而是发现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种种可能,小说家是“想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而不是任何人的发言人,包括他自己的思想。
在昆德拉看来,小说的魔力在于它发现了“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了很久很久”的东西,使小说世界与真实生活存在一种神秘的契合。例如,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没有商业运作,没有阶级斗争,没有政治纲领,没有意识形态观念,没有未来学派的预言,只有官僚化的机关体制,使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囚禁了人并抹杀了他的个性。这种描摹在之后的现代社会一再上演,以至于人们将卡夫卡小说仅仅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卡夫卡的伟大归于他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预见。但昆德拉却认为,卡夫卡只是早于“历史”发现了人和世界的一种可能,卡夫卡小说的伟大恰恰源于它所保持的彻底的艺术自主:不介入社会,不介入一个人们早已熟知的现实。用昆德拉的话来说:“一个诗人倘若不是服务于一个有待发现的真理(让人眼花缭乱的),而是另外别的,他就是一个假诗人。”
在1985年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昆德拉感慨,人类命运的真正威胁是对唯一答案的追求和对确定性的渴望,使人们放弃了每一个没有原因和目的的行为,“生活看上去像是原因、结果、失败和成功的光辉历程,人用焦急的目光盯着自己行为的因果联系,加快了朝死亡的奔跑”。此时,解救人类的或许只有小说。因为无论上帝还是科学,都在忙于解释一切事物的“为什么”,而小说,却在因果之桥断裂的地方,展示那些没有理由的存在。
作者:孙璐(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图片:豆瓣
编辑:陆纾文
责任编辑:邵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