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是居住的机器。”这是现代建筑旗手勒·柯布西耶的宣言。这句话意味着,住宅首先要强调功能,而这必须要把“人”当作核心才有可能。现代建筑实现了集合住宅大发展时代为普通人盖房子的任务,但没有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正如墨西哥建筑师路易斯·巴拉干在获得普利兹克奖后的感慨:“现代建筑已然放弃了美丽、灵感、平和、宁静、私密、惊异等主要来自情感的语汇。”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新书《理想的居所:建筑大师与他们的自宅》选取了世界知名建筑大师为自己、家人以及普通人设计的住宅作为案例,通过对这些住宅的建造、改建等的描写和评价,展现大师们的居住美学。本期“阅读”,我们选取了其中部分内容进行摘编整理,以飨读者。
勒·柯布西耶:住宅是居住的机器

勒·柯布西耶(资料图片)
1923年,柯布西耶堪称“近代建筑宣言”的《走向新建筑》一书出版,与此同时,他在瑞士雷曼湖畔给热爱大自然的父亲和喜欢音乐的母亲建造的房屋也动工了。他对这里倾注了特殊的情感:“这个小小的家,是为了经过长年劳作的我的父母亲,为了他们安享晚年的每一天而设计建造的。”


柯布西耶送给母亲的家
不幸的是,住宅建好第二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它实际上成为母亲的家,她一直在这里住了36年。母亲之家是柯布西耶送出的礼物,也被他视作一个小小的居住机器。他将住宅的功能面积最小化,然后将其组合成为一个整体加以灵活运用。为追求整体性,这座房子采用了白色装饰外表面,形成了一个细长的白盒子效果。房子内部并不大,是一个长17米、宽4米的矩形,建筑面积只有60平方米左右。
在面向雷曼湖的那面墙上,柯布西耶开出一个长11米的标志性水平长窗,将雷曼湖和远处阿尔卑斯山脉景色收入视野。东面一侧还有倾斜的天窗,迎接初升的太阳。与其说是将这栋房子向自然开放,还不如说,房屋整体将风景截切了。房子虽小,但是院子够大,像湖畔的一艘船。为了将风景尽收眼底,他在院子南面的围墙上也开出一个观景方窗。因为母亲爱狗,柯布西耶还专门在院墙上为狗留有一个眺望窗。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现代建筑取得席卷性胜利的1933年左右,柯布西耶开始丧失了对机器时代必然胜利的信心,并且开始反对“居住机器”的合理化生产,其后的住宅设计也转向乡土风格。罗伯特·费希曼认为,柯布西耶的社会观念和建筑观念都建立在工业社会具有的一种内在力量、一种能产生真正令人欢乐的秩序的信念之上。然而,在这一信念的背后,他却担心文明会被歪曲,并被失去控制的工业化毁灭。
1945年,柯布西耶更宣称:“现代建筑漫长的革命已经结束了。”一个原因或许是,他亲眼看到自己送到世人面前的现代建筑,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凝聚了巨大的复制力量,以致在现实中反而失去了原本的光辉,堕落为无趣的方盒子,它们也成为现代城市空间僵化、贫乏的一大元凶。
柯布西耶在母亲91岁生日时,给仍住在他多年前设计的湖畔住宅里的母亲画了一幅素描作为礼物,同时配上一首诗:“我的母亲涵盖了这里的太阳、那边的月亮、远处的高山、近旁的湖泊,以及这个房子。”将母亲的形象与房子、自然重叠在一起,这在这位现代建筑旗手构思“为了居住的机器”的初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而这位掀起了现代建筑革命的大师,晚年的自宅只是一幢地中海海边幽僻的传统小木屋。小木屋里陈设简朴,除了隐含的模数控制外,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建筑的造型特征,更像是清教徒的沉思所。1965年的一个夏日,柯布西耶在小木屋附近游泳时意外死亡,如愿以偿地在蔚蓝的大海中自由归去。
阿尔瓦·阿尔托:“居住”的出发点是意识和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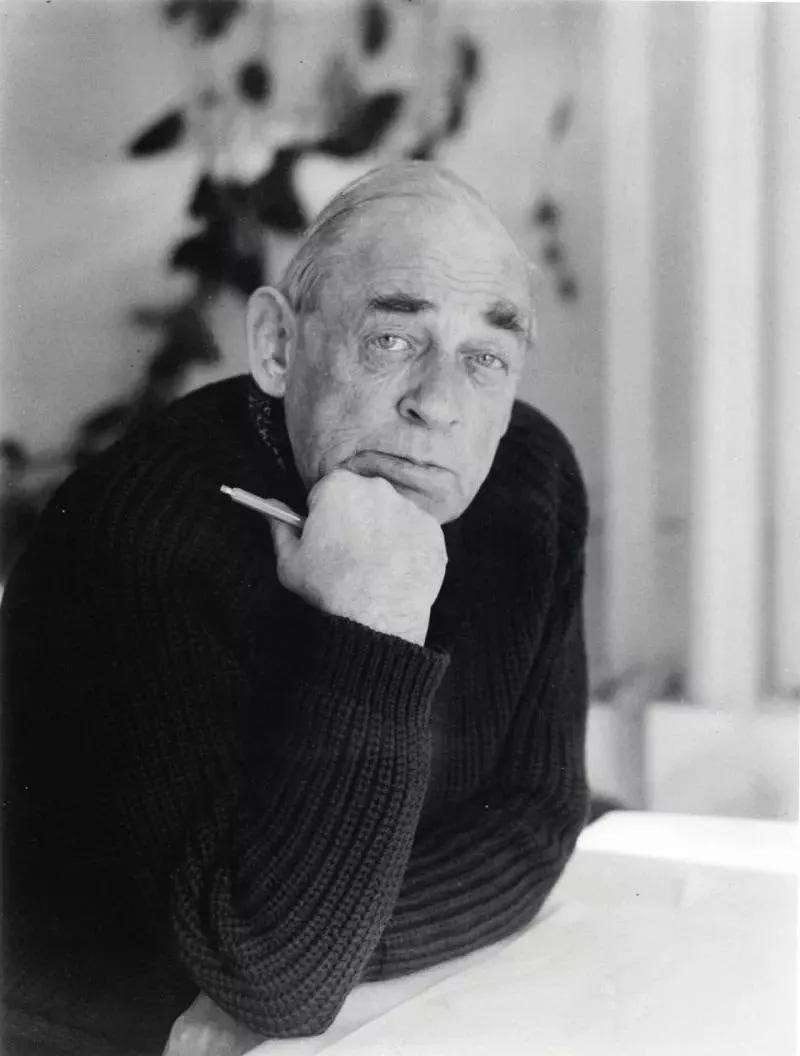
阿尔瓦·阿尔托(资料图片)
在芬兰,阿尔瓦·阿尔托的名字让人如雷贯耳,其影响反映在芬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吉迪恩在《空间·时间·建筑》中说阿尔瓦·阿尔托“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把芬兰带到哪里”。
与柯布西耶、赖特和密斯一样,阿尔瓦·阿尔托是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出现,让北欧成为现代建筑运动中令人瞩目的力量。在他活跃之时,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大行其道。他“居住”的出发点,不是建筑的功能或形式的美观,而是意识和感知。他将建筑的实用与居住者的情感自然地融合起来,似羚羊挂角,不着痕迹。这种建筑中的有机手法,给予了建筑内在的自由。
在阿尔瓦·阿尔托的作品中,梅丽娅别墅是一件毫无争议的杰作,也是一个少见的艺术与建筑结合的作品。房子位于芬兰西岸的努尔马库,始建于1938年,是一座用作夏季居住的别墅。这件重量级的作品,成为阿尔瓦·阿尔托1930年代的完美收尾之作,也是他作品中理性构成主义与民族浪漫主义之间的纽带。阿尔瓦·阿尔托希望,这栋奢华别墅,可以提供一种生活方式的模板与框架,在将来,逐渐走进更多人的生活。他的期望与彼时芬兰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乡村福利的提高,吸引着更多的人走向田园与森林。

梅丽娅别墅充满流动感的一楼空间

梅丽娅别墅设计采用了清水砖墙、抹灰墙与木板壁的混合,而更重要的是,将本土材料处理成能与人体发生知觉关联。在梅丽娅住宅里,不论是壁炉、桑拿房还是植草屋面,都是这片“冰与雪之地”的投射。餐厅北侧外墙镶嵌的壁炉,采用了天然的石材建筑,在石墙没有完工之前,阿尔托曾经派助手到芬兰西北部地区,调查那里的石墙建造工艺。而地面处理的细节更是精妙,从壁炉到起居室的琴房,地面材料从地砖到木地板再变为粗糙的铺路石,不但关注着行走者脚掌与地面接触的微妙变化,还对倾听者提示着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变化。
1926年,阿尔瓦·阿尔托写了他早期的一篇重要文章:《从台阶到起居室》。是年,阿尔托只有28岁,然而,他关于“居住”的理念,在这篇文章里展现出来。他认为,南欧人民延续了许多世纪的居住方式,可以借鉴到北欧的气候和人文环境中来。
阿尔瓦·阿尔托借用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弗拉·安杰利科的名作《天使报喜》,来阐释他的理念。这幅画给予了建筑师极大的启发。画中精细的建筑,完美地映射了20世纪20年代北欧的经典主义——这种风格,正是从意大利北部借鉴而来的。在阿尔托看来,这幅画提供了一个完美例子,演示如何“进入一个房间”。他写道:人、房间和花园在画中展现的“三位一体”,制造了一个不可触及的完美之“家”。圣母脸上的微笑,就像是建筑中最为精致的细节与花园中至为光彩夺目的花朵。在这里,有两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即:房间、外墙和花园的和谐一致与所有元素的结构统一——这使得画中人物更为突出,也表达了她的思维状态。
这段话听起来玄妙,放置到具体建筑之中,便是建筑物、自然环境及居住者的“三位一体”。在阿尔瓦·阿尔托之后的所有建筑中,都可以看到相似理念的秘响旁通——当你穿过梅丽娅别墅宽敞的起居室,一径走向门厅,门外的花园小路映入眼帘,在这一瞬间,你会明白安杰利科之于阿尔托的启示。
路易斯·巴拉干:作为自传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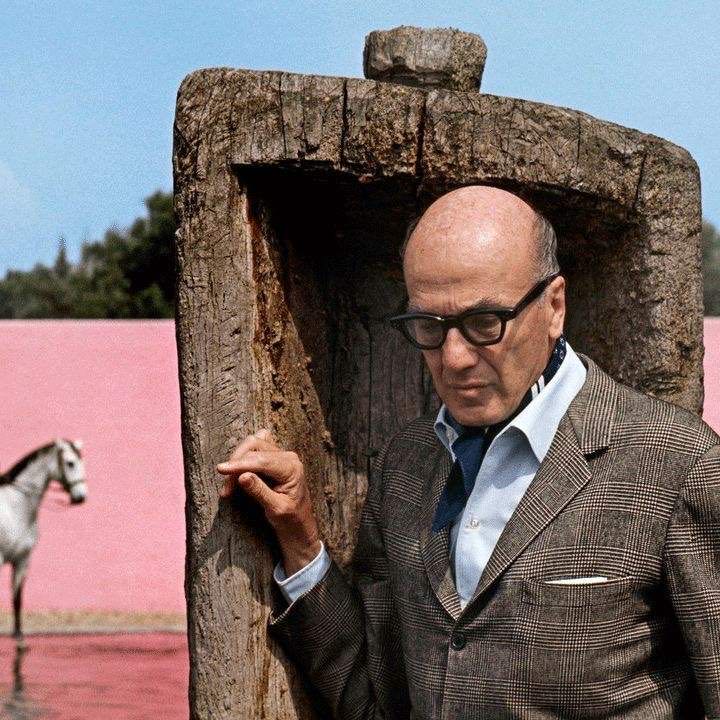
路易斯·巴拉干(资料图片)
“我的建筑就如同我的自传一般。我所有的成就——如果那些能被称为成就的话——都流淌着我在父亲牧场上的回忆。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的时光。我总是试图在我的设计中,使那些久远而怀旧的岁月与现代生活相适应。”——1980年,墨西哥建筑大师路易斯·巴拉干获得普利兹克奖后写道。
巴拉干的童年在麻扎米特拉村附近的一所农场度过。这是一个与山丘相连的村庄,有瓦屋顶和可以让行人躲避当地常有的暴雨的大挑檐。即使是土的颜色也是有意义的,它是红色的。在这个村庄里,分水系统是由粗原木制成的、用树杈支撑在屋顶以上五米高的窄水槽。水槽跨越整个村庄,到达各家的内院,流进那里石砌的池塘中。内院有马厩和鸡窝、牛棚。在外面的街道上有系马的铁环。当然,那条顶上已长满青苔的水渠到处滴漏,给村庄赋予了一种神话的氛围。
青年时代的旅行中,巴拉干还游历了西班牙——深刻影响了墨西哥文化的国家。在伊斯兰园林阿尔罕布拉宫,植物、石头、水等元素穿插组织,形成了宁静而私密的园林风格。巴拉干着迷于建造者摩尔人的园艺智慧,几年之后,他终于到达了摩尔人的故乡摩洛哥。
摩洛哥是一个色彩丰富的国家。包豪斯的色彩大师贝耶晚年时去摩洛哥旅行后感叹:现在我终于可以安静地死去了,因为我已发现了色彩。巴拉干大概跟他有着相似的感受。摩洛哥的当地建筑触发了他的童年回忆,在墨西哥的村庄和偏僻的小镇中,有白色的抹灰墙、宁静的天井和果园、色彩丰富的街道,以及村庄四周分布着的有阴暗入口的广场,显得谦逊而高贵。
摩洛哥由自然条件和本土文化生发的建筑风格启发了巴拉干,但他并未立即实践。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巴拉干发现墨西哥城南一块崎岖的布满粗犷火山岩的地方,极有潜力发展成为一个优美的居住区。“我被这美丽的地貌迷倒了,决定创造一系列花园,使其人性化,同时又不被破坏。我走在壮丽岩壁的阴影下,走在火山岩的罅隙边,突然惊奇地发现了一些小小的神秘的绿色村庄——它们被牧羊人称为‘珠宝’——它们被岩层包围着,这些岩层瑰丽多彩。这是史前岩浆受到强风化作用而形成的。这些不经意的发现带给我一种感动。”




巴拉干惯于使用墨西哥玫瑰红、赭黄、铁锈红等丰富的色彩
在塔库巴亚区的一些旧街巷中,低矮的树木点缀着普通的二层住宅楼,并不张扬,许多住宅混杂着墨西哥本土与殖民地的双重风格,与正在兴起的都市高层建筑和卫星城相比,仿佛是另一个陈旧的时空。
巴拉干自宅就隐匿在老旧的街区里。房子的外观是整齐划一的石灰泥墙,除了嵌在墙上的泛黄的窄金属门,没有任何修饰。住宅外观为三层,实际上各个空间分布在六个不同的高度上,由七段楼梯将这些空间连接起来。
窄门开启,立即进入这个迷宫般复杂的空间。入口即是幽暗的走廊,走廊尽头的门厅中,有一段半开放式的楼梯,与住宅中的所有楼梯一样,没有扶手。起居室与楼梯口相对,通高两层,其中一整面墙嵌上落地玻璃,窗外是植物茂盛的花园。自然花园的设计不仅反映了他受巴克影响而形成的喜好,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
起居室向里走是书房,窗户的设计截然不同。小小的窗高高架起,虽然临街,却既不能外望,也无法内视,使书房成为隔绝的空间。书房一侧墙上凭空出现了一段楼梯,通向夹层的工作室。只是那扇窄门紧闭着,仿佛从来没有开过。穿过书房的阳光房,通过洒下阳光的天窗,形成了室内与室外的过渡。走向楼顶庭院,发现这不是一个可以俯瞰街景的开阔空间,四面筑起围墙,使头顶的天空成为唯一的风景。
所有曲折和复杂的空间结构,都是为了隔绝外界、营造“宁静”而设计的。“它(宁静)是痛苦与恐惧最有效的解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建筑师有责任将宁静永久性地体现在居住中,无论住宅是奢华或是简陋。”巴拉干说,现代生活打破的正是宁静。
防止结构复杂的住宅变得枯燥、单调的办法,是色彩。门厅的一整面墙完全被涂上了墨西哥特有的玫瑰红色,书房是柠檬黄。楼顶庭院颜色最丰富,玫瑰红、铁锈红、赭黄、蓝色,简直是传统色彩的集合。
这座自宅通过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出受到关注。四年之后,巴拉干获得了建筑界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人们开始谈论他,并且试图将他的设计纳入已有的范式中。因为现代的许多经验表明,至少在建筑领域,美不再是一种神秘的东西,而成为可被量化、可被描述、可被归类的。与阿尔托一样,巴拉干将现代建筑要为普通人盖房子的使命,提升到建造让普通人身体能够感知到的房子。
原研哉:家是开启未来的媒介

原研哉(资料图片)
日本设计界“教父”、无印良品艺术总监原研哉的家,是一个有宽敞的起居室和狭小书房的居室。在他的构想中,未来人们理想的家应该会是一个非常简单、清新的状态。
试想一下这个画面:桌子上吃完的各种碗碟杯子、各种遥控器,是一种多么累赘的场景。而如果一张空无一物的简单桌子上什么都没有——正因为空荡荡的,才有无限填充的可能,才是一种富有和自由的状态。


原研哉理想的起居室
这种构想对应的是,原研哉认为,在经济发展和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的大背景下,人与人仿佛越来越分散的趋势难以阻挡。日本有一个调查数据,现在一个人或两个人生活的比例已经高达60%,而且很多情况下共同生活的两个人并不是夫妇,而是像90岁的妈妈和60岁的女儿这样的组合。几十年前,大家印象里的一家三口加上爷爷奶奶,两三代人在一个屋檐下,围坐在一起吃饭、看电视,这种其乐融融的场景,可能接下来很难见到了。这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整个居住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同时,伴随着云技术、交通、通信及安保服务事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新的融合方式应运而生,共享服务或超越物理空间的人际网络构建等生活方式层出不穷,生活中的满足与充实的定义也在发生着变化,这或许也是不可逆转的。
“我们将迎来怎样的未来,在产业背后的科技大门敞开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或者关于幸福的形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直以来,机器人、大数据、信息基础设施等这些都是作为单独课题被看待,但是单从社会或技术发展一方面出发,很难找到协同思考未来问题的路径。”“如果从整体来考虑科技发展的利弊的话,有时候会觉得,‘科技真的增强了创造性,增加了幸福感吗?’”在原研哉看来,家就是共同探讨这些问题最独特的选择。因为家既是各个产业的交叉点,又是文化生活的基础,可以作为将老龄化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国际化问题、文化问题等整合在一起的“媒介”。
2016年,原研哉在东京发起了一个名为“理想家”的展览。面向东京湾的台场区域,12栋房子矗立在伸向大海的一块棒球场大小的空地上,1∶1实体搭建,但呈现出统一的原木外观,内部也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模糊了现在与未来的边界。这里像是一个关于未来的实验室,讨论的并不是居住的空间分配和家具布置,而是一个个日本正在面临的社会问题——人口的减少、老龄化社会、年轻劳动力衰退等,12栋房子就像是12个解题的盒子。
展览上,有一个“木格水岸”,烈日下,这个种植着枫树的庭院看上去特别有清凉感。走近才发现,庭院里铺设着木质棋盘格子花纹,这种格子是日本古坟时代的织物花纹,京都东福寺的方丈庭院里就用了这种式样。而且格子高低错落,高的格子可以坐,低的格子则是个凉水池,正好可以没入脚踝。和同格子的人一边泡脚,一边聊天,很快就能建立一种分享的亲密感,人与自然的界限也在消失。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回应着原研哉的疑问——不一定要用高科技,才能获得幸福感。
“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物品化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也许最小限度的就够了。”
摘编整理自《理想的居所:建筑大师与他们的自宅》,图片除标注外均由出版社提供
编辑:周敏娴
责任编辑: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