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显现出多元与分裂的特征。表现在南京大屠杀上,尤为典型。日本右翼势力回避责任,漠视历史教训,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思视作“自虐史观”。在和平与发展被视为时代主流的今天,那些“逆流”令外界感到忧虑。
但日本学界也存在着一些坚持历史良知、对侵略行为痛加反省的知识分子。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史上,自上世纪70年代起,数位日本进步学者发掘并坚持历史真相的顽强身影,是值得中国人民尊敬和牢记的。恰逢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我们就此采访了学界的有关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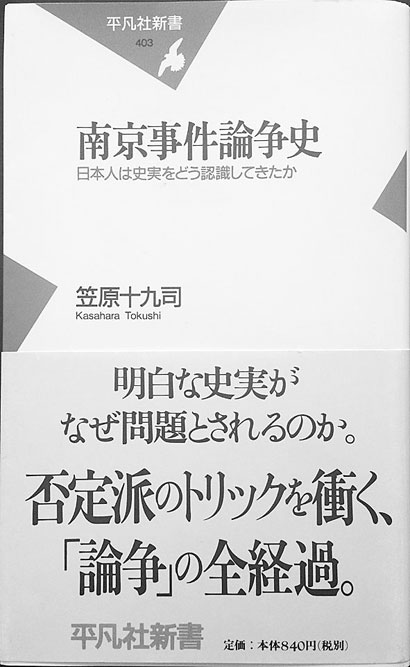
▲《南京事件争论史》是“南京大屠杀存在派”学者笠原十九司的力作。该书以“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历史事实”为主线,概述了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围绕“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的争论历史。从南京大屠杀事件爆发到日本战败不久即开庭的东京审判,直至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证据的查证以及判决有罪,作者揭示了一个不为日本人所广泛认知的情况:南京大屠杀爆发期间,日本政府和军部指挥层对此并非“不知情”,相反,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与国民不同,进而大量隐瞒、销毁对日本不利的信息和证据。
交锋 一场远未结束的论战
“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军全部占领南京,十七日,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首举行了入城式。在这五天内,穿上了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刹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下关的街道被浇上了汽油,烧得精光,呼救声响彻大地,一片垂死挣扎的哭叫声,火舌把天空染红,汽油燃烧冒出阵阵黑烟,机枪在咆哮,死尸散发出恶臭,著名的南京古城墙到处血流成河,扬子江的混浊江水也染得血红。这幅巨大的地狱画卷在现实中出现,成为一种愤怒,笼罩着江南的旷野……”
这段叙述南京史上黑暗一页的文字,出自一个日本人的回忆录。作者是前南满洲铁道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目击了这一幕幕惨剧。对于这段血腥的回忆,已故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怀着复杂的心情,将它“原汁原味”地引用到自己的历史著述《决定版·南京大屠杀》一书中。1982年,该书由德间书店出版,被视为洞富雄毕生成就的代表作。在这本书里,他以严谨的学术论证,与质疑南京大屠杀死亡数字的右翼学者激烈交锋。在书末,在那些证明日军暴行的史料面前,他提出了一个锥心之问:“在当时军人中是否有人看了这些文章而无动于衷,毫无痛心之感?对离不了军国主义的‘大和魂’和思想顽固的人来说,我的提问也许是毫无意义的。”
洞富雄追问的背后,在日本,有一场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风暴。那是关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论战。虽然因为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广为人知,但它只是一个模糊的整体印象,其残酷性和规模究竟如何,则不为大众所详知。这种历史认识上的灰色地带,成为那场论争的基调。作为长年从事南京大屠杀与东京审判研究的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程兆奇对那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有着深入的观察:“有关日本的战争罪行,在日本惟有南京大屠杀久争不息。走进日本的书店可以看到,没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历史事件有南京大屠杀那么多的著述,足见这一争论不再限于狭窄的专业范围,已成了社会关注度相当高的话题。”
在“南京”这个沉重的字眼之下,日本学者大抵有几种选择:做一个旁观者,不去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成为一个“虚构派”或“否定派”,极尽可能减轻战争中的加害程度,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甚至非学术性地歪曲篡改历史事实;或者,以一个真正客观正直的历史学者的姿态,为维护真相而努力。
作为世界上第一位南京大屠杀研究者、“大屠杀存在论”学者的代表,直至2000年以94岁高龄去世,洞富雄的大半人生都在与右翼史观论者的交锋中度过。历数洞富雄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贡献,程兆奇认为,“拓荒”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点。洞富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67年,见于《近代战史之谜》中的一章,这是日本第一篇在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南京大屠杀的文字;他的《南京事件》出版于1972年,是日本第一本研究性的专书,迄今仍被不断征引。此外,洞富雄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探讨,“从代表作《决定版·南京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的证明》看,洞富雄提出的问题和对日本‘虚构派’的辩驳基本构建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框架、确立了回应‘虚构派’挑战的方向”。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成为议论热点,乃至形成论战则与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报道有关。1971年,本多胜一获许可踏上调查侵华日军战争罪行的采访之路,寻访日军暴行的旧迹和幸存的受害人。报道以连载方式在《朝日新闻》刊出,其中当年11月4日到11月16日之间的10篇报道涉及南京大屠杀。此后,报道以《中国之旅》为名集结成书,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在原来“平顶山”、“万人坑”、“南京”、“三光政策”之外,又增加了“人的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防疫惨杀事件”、“上海”、“‘讨伐’和‘轰炸’的实态”等篇章。《中国之旅》在此后10年中重印了26次,但也引发日本右翼势力的疯狂攻击。
正是由于本多胜一的严厉批判,加上《朝日新闻》的影响力,“南京大屠杀”已成为日本大众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程兆奇认为,“它的影响本身使持反对所谓‘东京审判史观’者不能自安,由此形成了一波强于一波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汹涌浪潮。”于是,“大屠杀存在派”和“大屠杀虚构派”的学者针锋相对,攸关历史真相与正义的一场论争于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全面展开。
1984年,洞富雄与藤原彰、本多胜一、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进步人士组成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对于该会的初衷,吉田裕在1985年曾有这样的阐释,“‘幻影派’优先考虑的是政治立场和思想领域,其次才是历史事实,因此他们无视甚至歪曲历史事实。对此,研究会的目的之一是尽可能正确地从各个角度还原南京大屠杀事件原貌。目的之二是将南京大屠杀事件作为历史教训,以此促进真正的日中友好,同时,以此为动力,促使国民自觉培养和平意识。另外,正好那时正在审理家永教科书案。研究会第三个目的就是积极支援审理家永教科书案。”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前半期,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成员为中心,在国内外挖掘收集南京大屠杀事件史料与证言的工作进展迅速,编辑翻译出版了9部资料集,还相继出版了记述南京大屠杀事件原因、经过、结果及其历史影响乃至整个事件全貌的历史书籍。
在“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中坚力量、日本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笠原十九司看来,南京大屠杀不可否认,已是被论证的事实。在日本展开的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否是史实的争论,在学术上,以“否定派”、“虚构派”的失败而告终;关于家永三郎教科书案的判决,以企图从教科书中抹掉南京大屠杀记述的文部省的败诉而告终等一系列案件,也“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事件争论在司法界也已结束”。然而,在现实里,由于种种原因,右翼思潮频频回潮,与学术无关的南京大屠杀论争还在日本继续。这段令中国人倍感切肤之痛的历史,如今在日本仍然“布满迷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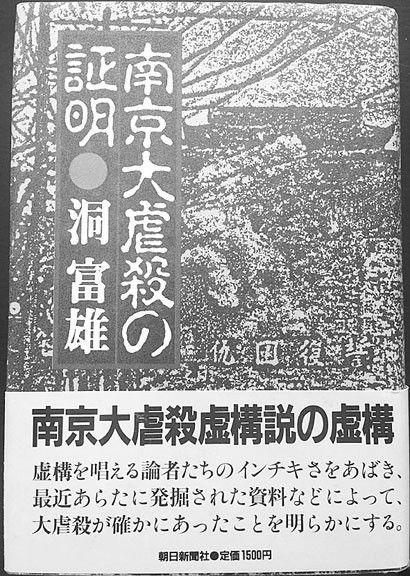
▲《南京大屠杀的证明》是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先驱、著名历史学家洞富雄在其80高龄之时,写下的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最后一本单行本著作,全面批判了田中正明“虚构论”和板仓由明“屠杀少数人论”。这部著作全面收集了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所发掘出的以及后来不断被公布出来的日方各种资料和证词,因此该书对右翼论者的批判被认为更有说服力。洞富雄对“虚构派”田中正明引用的资料和记录原件,逐一进行认真分析和批判,包括指出其阅读资料的方法粗糙、不看资料即随意撰文、未读懂洞氏的批判文章即予以反驳、其反驳实际毫无意义等等。
缺失 屠杀缘何未成日本记忆
外界观察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争,常有这样的困惑: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事实,为什么没有成为一般日本国民的“常识”?非但如此,南京大屠杀“否定论”和“虚构论”为何反而能在日本大行其道,有着强势的影响力?日本人究竟是怎样认知史实的?
笠原十九司在其著作《南京事件争论史》一书中,系统地直面了这一系列被外界反复抛出的质问。他反思:除去战后日本政治的保守化风潮不利于日本民众正确认识历史这个因素之外,如何认识历史,更取决于看到怎样的历史。他认为,从战时到战后,南京大屠杀那一段历史并不曾通过国家的形式,被彻底而郑重地呈现在日本民众面前,这导致“后果非常严重”。
在战时,日本的舆论报道受到严格审查和管制。“南京大屠杀事件一发生,日本政府和军部领导层即获得情报并作出了反应。但相关信息被严格管制,不让日本国民知晓。”笠原根据史料发现,这种自上而下的不透明在战后得以继续,直接影响了日本人对东京审判的看法,进而影响了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认知度。日本战败后,趁联合国占领军未抵达的“空白期”,政府、军部和军队大规模地彻底烧毁、隐藏文件档案资料。结果,“史料缺失使从历史学角度判明南京大屠杀事件全貌工作受到限制。”“很多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因此认为,‘没有可以证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日本官方史料,所以从未有过屠杀。’、‘外国人的记录和文献是反日的政治宣传,是敌国的战略宣传’”。另外,由于日本媒体几乎一边倒地从日本辩护方角度报道东京审判,日本国民也无从得知详细的审判记录。
“如果经过大量审理,并由东京审判判决且为当时日本国民得知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事实,被当时的日本社会接受,成为固定的日本国民对战争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就不会出现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事实还是虚构’的争论了。”笠原在书中禁不住感慨。
此外,笠原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之所以没能成为日本“国民的记忆”,还因为日本国内接纳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虚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心理基础。在他看来,德国国内设有犹太人集中营,有影像资料和文书资料的记录。最关键的是,受害的犹太人也是德国国民。而日本则不同。首先南京在外国,受害者是中国人。其次,除了某些地方,日本国土从未变成惨烈的陆地战场。“日本人对于战争的记忆,听到的讲述都是空袭、原子弹爆炸、物价上涨等受害经历,而南京(大屠杀)事件等加害记忆,则用‘沉默’、‘封印’进行‘抹杀’,使之被忘却”,“因此,日本国民从未亲历过军队杀害平民那种惨绝人寰的情况。对顽固认定自己是战争受害者的日本人来说,只要他们不接受这极其残酷的加害现实,就很难让他们实际感觉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事实。况且,能让国民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事件事实的影像和文书等记录资料从未向日本国民公开过。”
而参加过南京战役的原日军官兵,如果讲述他们残忍杀戮的经历,则被视为背叛,等同于“利敌行为”。笠原指出,这有文化上的因素,在日本社会,内部成员的犯罪违法会互相习惯性地默认、放任,如果泄漏到外部或公之于众的话,会被看作背信弃义而有可能受到严厉的制裁。“这种集团性、社会性法则是一种传统。”
笠原不是唯一的追问者。生于1929年,对战争有切身体验的学者津田道夫也有类似的质疑,“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良的劳动者’、‘平凡家庭的父亲’、‘礼仪端正的人’之类的日本庶民,到了中国战场会变得那么残暴。”曾与之有深入学术交流的程兆奇在2000年翻译出版了津田的《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一书。在他看来,津田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自我批判,也不满足于一般的“历史”分析,而是“由表及里”从日本大众的“精神构造”下手探讨残虐行为的人性根源。正如津田在书中所说:“我觉得仅仅以战场的异常心理,或者为了战死的战友报仇等解释是不够的。我认为这和日本大众特殊的精神构造有关。”他有着日本人罕见的反省意识,用自己的笔“无惧地解剖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批判“庶民利己主义”。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日本在战后从未对侵略战争进行过全民性的反省,“以至在战后的今天,为战争鸣冤叫屈的种种怪异之论,才得以甚嚣尘上”。
“现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项目已有结果报告,即认定了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历史事实”。对于自己的研究问题,笠原给出了解决方案,“因此,下一步就是要求日本领导人,用行动来表示这样一种政治态度,即认定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事实。在政治上结束这场争论,还要反映在政府的历史政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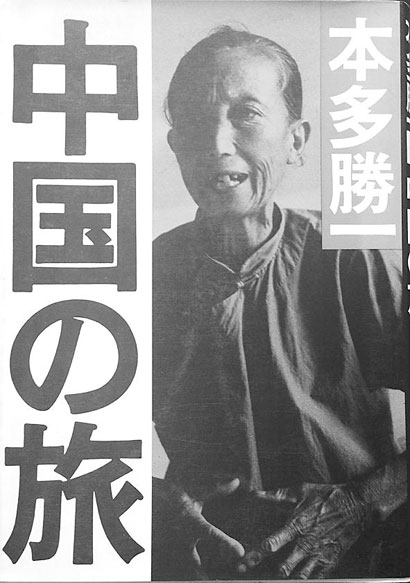
▲《中国之旅》是第一个在日本勇敢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前《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报道作品集。1971年,本多胜一获许可踏上调查侵华日军战争罪行的采访之路,寻访日军暴行的旧迹和幸存的受害人。报道以连载方式在《朝日新闻》刊出,其中当年11月4日到11月16日之间的10篇报道涉及南京大屠杀。此后,报道以《中国之旅》为名集结成书,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在原来“平顶山”、“万人坑”、“南京”、“三光政策”之外,又增加了“人的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防疫惨杀事件”、“上海”、“‘讨伐’和‘轰炸’的实态”等篇章。
研究 以学术方式捍卫真相
“日本竟然出现试图将最能证实日本战争犯罪的南京大屠杀‘幻影’化,其论著得以发表,还受到一些人群吹捧的思潮”,“目睹当今法西斯潮流再次专横汹涌”,“我作为历史学家,有责任拨开‘幻影’迷雾,澄清历史事实”。1975年,洞富雄在《南京大屠杀——批判“幻影化”操作》一书中如是说。
历史学家的责任,这或许可被视作那些与右翼幽灵作战的日本人的集体心声。然而,捍卫真相的道路布满荆棘。比如,在论战多年后,本多胜一在公开场合时出现几乎都戴着墨镜。再比如,笠原十九司在自己的书中也坦承,曾被右翼分子戴上“自虐狂”、“反日派”和“卖国派”的帽子。“在日本的互联网上,只要搜索‘笠原’、‘南京’字样,网页上即会出现数量庞大的诽谤、中伤”。但是,在包括笠原在内、仍然奋战在论战前线的正直的日本学者看来,他们以学术的方式所捍卫的历史真实,正是为了“恢复日本人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围绕南京大屠杀的论战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日本的进步学者在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中,已发表了近百本著作和论文。那些包含正义感的论述有力批驳了错误史观,形成了宝贵经验。
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的那批正义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上做出了三方面的贡献。首先,他们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珍贵史料。其中包括日军战斗详报、联队战史和日军官兵的日记与书信等,由于战争后日本政府烧毁了许多作战部队的核心资料,这部分资料显得十分珍贵。其次,他们的研究成果扎实、针对性强,学术研究视野也比较超前。最近几年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成员重点开始从历史教育、社会记忆、跨文化研究、国际对话等多视角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
日本进步学者在学术上的抗争史,对于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有何启发?
程兆奇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日本的南京大屠杀“虚构派”长于“观念”的批判,而疏于材料的辩驳,而“对日本右翼挑战的最有力也最有效的回应就是用可靠的证据说话”。他指出,日本的“虚构派”确实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但“虚构派”不是只有口号。“虚构派”几乎每一部重要著作在材料上都有新发现,虽然曲解史文、强词夺理在“虚构派”著作中司空见惯,但“如果我们发空论,不辨根据,也起不到‘驳倒’的作用”。
中学教师渡辺久志对东中野修道等人编辑的《检证南京事件“证据照片”》一书的“检证”即是生动一例。程兆奇介绍说,渡辺久志在《照相机目击的日中战争》一文中采用了朴素的办法——追寻母本的史源,参以相关文字影像资料,以求还其本来面目。比如,《检证》称某照片为中国“伪造”,理由是照片中的日军军装没有肩章。渡辺搜寻事发时照片,发现大阪每日新闻社1937年10月21日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中“举杯祝贺占领无线电台的田中部队长”为题的一张同样没有肩章。有此一照,《检证》所说已可不攻自破。“但渡辺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又在文献中查到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曾在同年8月29日下达通知,通知明言:各部队为了‘防谍’可以摘除肩章。有了梅津此件,该案定谳再没有疑义。”程兆奇说,“渡辺文既没有高亢的声势,也没有滔滔的辩辞,但一气读完后感到的,就是踏实的力量。”
此外,程兆奇认为,正确对待历史情感记忆非常重要。为什么在日本,惟独南京大屠杀会有那么多的争论?“在日本人看来,南京大屠杀在日军所有暴行中规模最大;被认为是两国间‘历史纠葛’的‘象征’;日本一直有人号称南京大屠杀是针对‘反人道罪’的‘编造’……”在他看来,这些原因都与学术无关。“如果没有立场的因素,南京大屠杀不可能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当然,南京大屠杀之所以成为持续的‘热点’,也和事发时记录的不充分以及第一手文献的‘遗失’有关。”
“日本有所谓‘同时代史’的说法,以区别于与今天无关的‘历史’。南京大屠杀距今虽已77年,但至今仍没有走出和我们情感相连的‘同时代史’。暴行给受害一方留下深刻印记,另一方面,在‘公理’‘公法’主导的今天,将‘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和‘广大日本人民’分开是一个大度而不失原则的立场,人们纪念南京大屠杀时总是说是为了珍惜和平而非记取仇恨。问题是南京大屠杀——其它暴行也一样,虽然可以引出珍惜和平等理性意识,但惨痛回想更直接或者说更容易勾起的还是‘痛愤怨疾’,这从网络相关话题中可见一斑。”程兆奇指出,如果说南京大屠杀研究确实有学术以外的影响,这种影响着朝野承受力、比狭义的“是非”更难超越的“情感”(常常和“民族大义”混为一谈),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层面,他认为,对日本右翼学者提出的“证据”不能只以“大义”来回应。在时隔77年后的今天,史学工作者应该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更注重“历史事件”的真实细节和确切的数据。“‘虚构派’一直以‘论从史出’自我标榜,因此我觉得对付‘虚构派’的最有效的办法还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有俗话所说的‘事实胜于雄辩’的自信。”
作者:吴宇祯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朱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