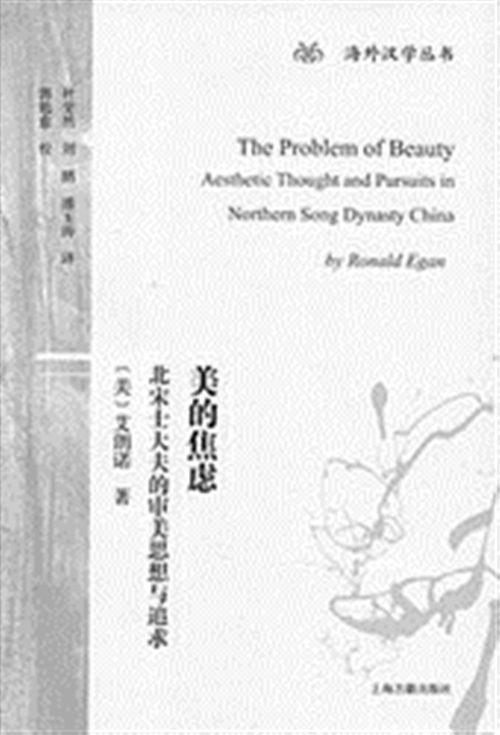
《美的焦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艾朗诺著 资料图片
此书原名TheProblem of Beauty: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DynastyChina,200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中文译本令人意外地将标题中的problem(问题)译成(或者说改成)了“焦虑”,还在副标题中加入了“士大夫”一词。据我所知,这是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其夫人陈毓贤女士(她也是译者之一)与译者杜斐然(哈佛大学博士生)、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及审稿人反复商讨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中文书名反映了作者、译者、编者对此书终于达成的共识,向我们提示了理解此书主旨的途径。与原版书名显得不甚一致的“焦虑”和“士大夫”二词,应该被看作“关键词”。下文就从“焦虑”说起。
为什么是“焦虑”
译者杜斐然最近给我写信,阐述了她对原著书名的理解:
在英语中,可以被翻译成“问题”的有两个词,一是problem,二是question。question非常中性,而problem就是“存在问题、有问题了”的意思。比如,在英文讨论中如果说“Ihaveaquestion”,就是“我想提个问题”,这后面接的是个问句;如果说“Ihaveaproblem(withwhatyoujustsaid)”,那就变成了“我认为你刚才说的有问题(我接受起来有问题)”,这之后跟的是自己的意见和质问。因此,problem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如果译为“问题”,那其实是暗含两个解释方向,一是这个时代中存在的几个主题、讨论的问题、当时代人的concern;另外一个方向才是我们想要它传达的意思,就是“存在问题”的意思。
按她的理解,因为与传统观念有所冲突,北宋士大夫意识到他们对美的鉴赏和追求是“有问题”的,从而引起心理矛盾,以及试图克服矛盾的曲折表述,这才是英文书名所要传达的意思。从这个角度说,“焦虑”是原书名的一个传神的译法。
我想这应该符合艾朗诺本人的写作意图,实际上,在陈毓贤翻译的此书《引论》部分,我们就能读到“焦虑”一词:“11世纪左右,中国士大夫对美的追求空前地热烈,开拓了大片的新天地,但也因而造成新的焦虑。”(第1页)他所说的新天地,主要包括四个领域,书中分列为六章:第一、四章讲的是艺术品的鉴赏与收藏,第二章讲的是诗话,第三章讲花谱,第五、六章讲词。艾朗诺关于四个领域的讨论,虽然各自都可以被看作专题性的研究,但从文学艺术史的角度看,它们涉及了创作(词)、鉴赏(艺术品收藏)、批评(诗话)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花卉),有足够的理由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更重要的是,这些讨论中确实贯穿了统一的思路,如其自云:“总的说来,北宋末士大夫的精神内容和表达方式都扩宽了,以前被认为离经叛道的娱乐和各种对美的追求得以见容,而且可诉诸文字。……本书把焦点集中于北宋士大夫在追求美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指出传统儒家对这些活动有许多成见,他们必须开辟新的视野,敢于挣脱教条的束缚,勉力给出一个说法以自辩。”(第3页)实际上,全书的主要篇幅,就在精细地考察一系列关于审美爱好的“自辩”说法,而正是这些“自辩”透露了士大夫们的“焦虑”。
在今人看来最正常不过的各种审美活动,为什么会引起“焦虑”而需要“自辩”?儒家思想对审美活动的“许多成见”,是我们经常提及的阻扰因素,但事实上这并未导致中国美学史或文学艺术史乏善可陈。从积极的方面看,艾朗诺所讨论的四个领域都是宋代所开辟的“新天地”,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词是一种新兴的体裁,虽不是起源于宋代,但士大夫们接受它,并使它发展为与诗文并驾齐驱的创作样式,是在北宋期间;艺术品收藏是北宋新兴的风尚;诗话是新兴的批评载体;而据艾朗诺的考察,以欧阳修作于11世纪30年代的《洛阳牡丹记》为始的有关花卉植物的专论,也是北宋期间中国文化史上的若干“第一”之一,“有史以来,宋代首先见证了大量关于花卉栽培和鉴赏文集的产生,这比西方要早几个世纪”(第81页)。很明显,他有意去捕捉一个时代所产生的新现象,并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新兴的领域。并非所有儒家思想家都会极端排斥审美活动,但新兴领域所包含的一些方式、倾向,却具有对传统观念的挑战性乃至颠覆性。比如:写词是否意味作者是浪荡子弟?士大夫抒写他对歌姬的爱恋是否有失体面?对艺术品的占有是不是一种“物欲”?以闲谈随笔的形式论诗是不是不够严肃?像牡丹花那样的诱人、艳丽之美也可以沉迷其中吗?由植物嫁接技术所带来的反自然的花卉之美也可以接受吗?借用上引杜斐然的话说,这些问题真的不是question,而是problem。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而且每个士大夫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可能只对他本人有效(甚至这一点也难以保证),但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这些问题,并试图去解决。换句话说,他们在此种“焦虑”情形下产生的一系列文本,是艾朗诺致力于解读、分析的对象。
于是我们看到,本书中被全文引录或大段摘录而加以精细解读的文本,约有二十余篇,多数是北宋的“记”文或序跋。对这些文本的准确英译,是原著的一大成果,中文译本则只能传达作者的“精读”之功。他从这些文本一一读出了与全书主旨(“焦虑”)相关的信息,还把不同时期的文本相互比较,藉以考察各个领域的进展变化。
这里没有必要全面复述他精彩的解读过程,但有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就是全书讨论的四个领域,都以欧阳修为开启者或重要的早期作者。这在《引论》中就已明言:“欧阳修是个关键人物。他非但首创把石碑铭文的书法当艺术品收藏,撰写诗话和花谱,他对词的发展贡献也非常大。”(第2页)因此,欧阳修是此书考察的核心人物,要说“焦虑”,他也是最为“焦虑”的个案。确实,欧阳修的业绩涉及许多方面,按照现代的学科门类,我们可以赋予欧阳修很多“身份”:儒学思想家、政治家、诗人、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文献学者、花卉鉴赏家、文物收藏家,或者照顾到传统的学术领域,称之为经学家、古文家、词人、金石学创始人,等等。这些“身份”对于他来说全部当之无愧,因为他在任何方面的成就都居于同时代的一流水平。换言之,只要是北宋这一时段成为考察对象,几乎所有人文领域的研究者都将面对欧阳修,他无所不在,“全面发展”,确实令人倾羡。然而,具备这么多“身份”的欧阳修毕竟是同一个人,他能使这些“身份”完全保持平行,而不致互相冲突吗?在他留下的很多文字中,艾朗诺读出了他的“焦虑”,这便是冲突存在的证明。推而广之,他的超强的创造力经常是与内心的“焦虑”相伴随的。从某种角度说,“身份”越多的人,“焦虑”就越甚。欧阳修是个典型的个案,类似的情形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不少士大夫身上。或者说,这是北宋士大夫相当显著的特征。由此,我们的话题将转向此书中文版标题中的另一个关键词“士大夫”。
“士大夫”、“文人”或者“才子”
英文原版的副标题,可以直译为“北宋的美学思想与追求”,其中并不包含表示主体的词语。中文版的责任编辑向我介绍,加入这样的词语最初出于陈毓贤女士的建议,她认为应该加上“文人”二字,后来经过讨论,将“文人”改成了“士大夫”。
实际上,并没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来说明“士大夫”一词比“文人”更为合适,尽管书中讨论的人物绝大部分拥有“士大夫”即文官身份,但不要说李清照是明显的例外,像晏幾道、米芾等人,也大抵放弃了“士大夫”的主业,即他们应该扮演的政治角色。让我们按照年代顺序来制作一个书中主要人物的名单:
柳永(984—1053)
晏殊(991—1055)
欧阳修(1007—1072)
苏轼(1037—1101)
黄庭坚(1045—1105)
晏幾道(1048?—1113)
秦观(1049—1100)
米芾(1051—1107)
张耒(1054—1114)
周邦彦(1056—1121)
李清照(1084—1155?)
此名单仅限于生卒年可考的,但从中已可看出,这些人在政治史上的重要性,及其成就广涉多种领域的“全面”性,大致呈现坡形,先逐渐上升,至苏轼后又随时代的下移降低。也许“文人”的称呼更能概括出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可能考虑到与正标题中“焦虑”的呼应关系,后来决定采用“士大夫”一词,因为引起“焦虑”的原因多半与他们的“士大夫”身份相关。然而,出现在此书所论审美领域的主体,从真正“全面发展”的士大夫文人,到北宋后期逐渐转移到接近专业化的“文人”,这个趋势却不是艾朗诺随意选择论述对象所造成的,它揭示出一种客观存在的变化。
对于“士大夫”或“文人”的关注,是目前中国、美国、日本等地的宋代研究者比较一致的学术趋向。艾朗诺探讨了前文所述四个领域的具体情形后,也在《结论》中把问题引向了这个方面。他引用了伊佩霞(PatriciaBuckleyEbrey)的观点,阐述宋代“从崇拜‘大丈夫’到崇拜文人”的转向(第277页)。在我看来,这种转向也可以从上面的名单得到印证,但更应重视的是伊佩霞对“文人”的描述接近于所谓“文弱书生”:他们优雅、博学、多思,具有艺术气质,但不必强壮有力;他们使用轿子出行,收藏古董和艺术品,从不从事狩猎;等等。艾朗诺把这种“文人”形象与他所论述的宋人审美追求相联系,称之为“崇尚男性精致文雅的新潮流”,指出该潮流在其兴起之时“并非毫无问题。这一转向其实存在很大的阻力”(第278页)。显然,他所说的“阻力”就是“焦虑”的原因,但重要的是“转向”的实现。他分析道:
从许多角度都能发现“文”与各种男性典范间的对应。有君子之“文”,相应也有美学家之“文”、享乐者之“文”、词人之“文”、花卉鉴赏者之“文”。前者反对伤感的精致,后者却并不如此。宋代的儒家和新儒家(包括哲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中从来不乏推举君子之文者,但从我们考察过的那些人及其言论中,却时常能看到对后一种文的好尚倾向(当然,也有人,如欧阳修同时具备这两种文的特点,分别体现在不同的心境和表达方式中)。但似乎没有一个现成的词能准确地归纳这种与“君子之文”相对的“后一种文”(其实包含了几种不同的“文”),这一点很麻烦。最接近的应该是“文人之文”,但“文人”一词又过于宽泛,仍不理想。或许“才子”更能代表这后一种文的好尚群体。当然,“才子”在元明清文化中有更固定的所指,但它与前代这一群体存在着很多共同点,也同样能接受男性的敏感和多情,宋代的这“后一种”文人其实可以看作是元明清“才子”的先驱。(第278—279页)这段话概括地提示了全书“考察过的那些人及其言论”对于“士大夫”或“文人”研究的意义,而从欧阳修那样兼具“两种文”的士大夫,到偏尚“后一种文”的文人,再到元明清时代所谓的“才子”,艾朗诺描述的发展脉络是十分清晰的。
当然,除了描述外,还须揭示“转向”的原因。笼统地说,全书考察的宋人之“焦虑”及其“自辩”都旨在于是,但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艾朗诺论述这个问题时比较独特的性别视角。所谓“男性的敏感和多情”——“才子”的这种招牌性特征,在艾朗诺看来,主要是随着词在北宋士大夫社会中被接受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在第五、六章中,他从性别视角出发,对一批北宋词作的写作特点作了细微的体认。我们知道,唐五代词有替女性“代言”的习惯,男性作者因此必须去体会和形容女性的“敏感和多情”。到了北宋,词中的抒情主体一步步发生变化,晏殊词“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其叙述者性别的模糊,读者在字里行间找不出任何可以将叙述者确定为女性的细节或暗示”(第197页),与此同时的柳永词也是“言情多取男性叙述视角”(第199页),下一代晏幾道的词,“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词人脑海中女孩的形象,还有她们在他心上刻下的印记”,“晏幾道是第一个将这一主题确立为创作中心的词人”(第246页),最后还有周邦彦词,“特别关注男性在恋爱中的体会”(第251页)。随着“代言”习惯的消失(这表示写词的行为被士大夫社会所接受),与词体相适应的“敏感而多情”的主人公形象由女性变成了男性。一方面,“一种偏爱自然之美与纤细风格的文学审美情趣正在词的发展中确立”(第255页),另一方面,被接受的词体也塑造着它的作者,使之向“才子”型的新男性转化。
艾朗诺对词的论述让人耳目一新。这无论如何是个有趣的话题,除了苏轼等少数作者,只要是写词,男性作者就须改变传统“大丈夫”的自我意识,而表现出“男性的敏感和多情”。可见,尽管艾朗诺把此书的大部分篇幅让给了细致的文本解读,但从全书《结论》部分中有关“文人”的议论,我们不难了解,他其实具有非常宏观的眼光,去注视整个中华帝国后期的审美文化及其承担者。在宋代研究者通常能看到的道学、党争、民族矛盾以及一般所谓“文学成就”之外,他独具慧眼地看到了一种基于个人趣味的,精致、文雅而偏向柔情的审美意识,正在这个时代突破既有的社会观念,经了士大夫们的种种“焦虑”和“自辩”而发展起来。他谨慎而又大胆地勾画了这种审美意识的来龙去脉,证实了近世中国的这一传统,或者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不过,伊佩霞和艾朗诺对“文人”或“才子”的描述,极易让人联想到《西厢记》中被“倾国倾城貌”惊艳的那位“多愁多病身”,还有鲁迅的一段相当刻薄的形容:“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在现代人眼里,这样“病态”的“才子”决不讨人喜欢,但具有艺术气质、“敏感而多情”的文弱男性,生命中的盛期和衰暮无非如此。那么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由经受了“焦虑”的宋代士大夫所建立,而被后世的“才子”们所继续的审美传统,何以走上了那样的穷途末路?当然,对这种审美传统的反思,并非此书所负的任务,但艾朗诺对其形成过程的揭示,将有益于我们的反思。
文/朱刚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