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瑟夫·布罗茨基
上海译文出版社计划引进出出版被誉为“继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的布罗茨基的诗作——《布罗茨基诗歌全集》,这套书将收录其用俄语写作以及由他本人或在他本人的帮助下由英语译为俄语的全部诗篇,囊括了诗人一生中最重要、最著名的诗歌作品。近日,这套书第一卷的上册已经面世,主要内容为《佩尔修斯之盾——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文学传记》及诗集《在旷野扎营》中的大部分诗歌。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是著名的俄裔美籍诗人,他对生活具有敏锐的观察和感受力,思想开阔而坦荡,感情真挚而温和。他的诗充满了俄罗斯风味,特别是在流亡国外之后,怀乡更成为他的重要诗歌主题之一。在艺术上,他始终“贴近两位前辈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奥登”,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和音韵的和谐。1987年,在他47岁时,以其“出神入化”“韵律优美”,“如交响乐一般丰富”的诗篇,以及其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并“为艺术英勇献身的精神”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这项世界性文学大奖继加缪之后又一位年轻的获奖者。布罗茨基已经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此次出版的《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上)》分为两部分,主体收录了他的诗集《在旷野扎营》中的大部分诗歌。《在旷野扎营》是布罗茨基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内容均为他的早期作品,本卷中收录了七十首短诗和叙事诗《伊撒和亚伯拉罕》。对于布罗茨基来说,这些作品在其诗歌的道路上则标志着其风格的形成和确立:结构手法、词语的形象体系(象征性词汇)、独创性的诗律。除此之外还收录了布罗茨基的研究专家洛谢夫撰写的《佩尔修斯之盾——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文学传记》,这本文学传记长达七万字,是洛谢夫结合自己与布罗茨基的交往和对他的研究所做,对布罗茨基的人物生平、文学创作、思想变化都介绍得非常详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此次《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的出版,将是华语世界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地全面翻译出版布罗茨基的诗作全集,这是世界范围内除了英语和俄语外的第三个语种的译本。
日前,思南读书会邀请到了该书的译者娄自良,诗人胡桑以及责任编辑刘晨和读者一起走进布罗茨基的诗歌世界。
“诗歌是整个思维思考以及对世界感受的加速器。”这是布罗茨基在随笔集《悲伤与理智》中的一句话,它震撼了很多人,包括嘉宾胡桑和该书编辑刘晨。
据刘晨介绍:这本诗集收录的只是布罗茨基比较早期的作品,最后一篇是1967年。这中间有一个节点是1940年,在此之前布罗茨基的诗歌还带有比较明显的俄罗斯传统风格,后来出现了很大的转折。布罗茨基在接触大量英语诗歌之后,既没有抛弃俄罗斯诗歌的抒情传统,又保持了奥登这种英美诗歌冷静的思考,他使用折中主义的方法保持两个传统。这一点在他到了美国之后出版的诗集里面有更多明显的特点出现。刘晨说,这本诗集里面还有一些诗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性,翻译娄自良老师将这种联系翻译成跨越,两首诗可能间隔几年或者十几年,但是某些意象是相通的,这点给诗的翻译造成很大的难度。88岁的娄老师精益求精,不断修改,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
对此,娄老师表示;“这本书,本来我点头就可以出版了,但后来全部否定了。第一版我推翻了,第二版我自己也推翻了,最后就是现在你们看的这个。我真心实意地为读者服务,我爱尊重我的读者。”
诗人胡桑认为,布罗茨基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有一种重要的贡献,就是一种威严感,这不是某些英美诗歌或者法国诗歌可以呈现的,因为法国当代诗歌过于形式化,威严感是被削弱的。以布罗茨基为代表的俄罗斯诗人的作品,这种威严感非常强烈,教你严肃的生活,严肃的思考,严肃的认知这个世界。胡桑说:“为什么我们还读诗?这个时代是小说时代甚至说小说时代都有点心虚,应该是电影时代或者微信时代,那为什么还要读诗、写诗?写诗就是加速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或者加深对世界的感受,因为我们对世界的感受还不能仅仅通过小说或者散文甚至电影来表达,诗歌更精炼精密。”胡桑还回忆了他去威尼斯拜谒布罗茨基墓的情景:“墓碑就是一块很简单的汉白玉,墓碑上有一句他遗孀为他选择的话,也是这本诗歌传记最后一句话,‘死去了不是一切都完了。’死不是终结。”布罗茨基的一生波澜壮阔,可是他的诗歌比他的人生还要波澜壮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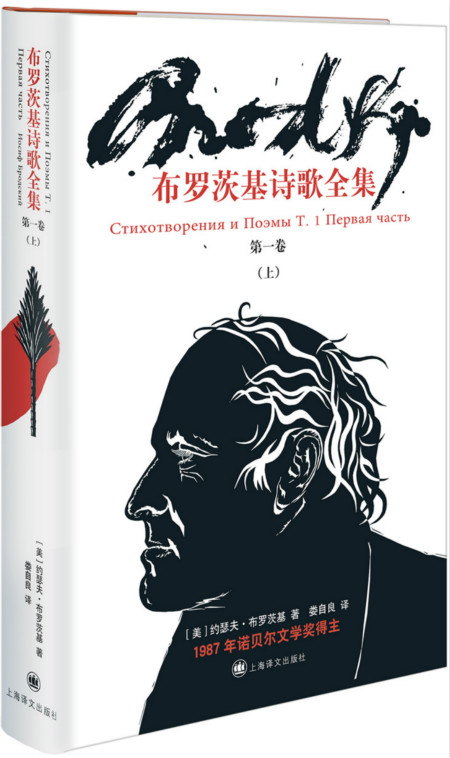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
【美】布罗茨基著
娄自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定价:98元
相关阅读
六年后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一月二日又恰逢星期二,
何必惊讶地抬起眉毛,
要像汽车前窗上的——雨刷,
从脸上赶走莫名的哀伤,
让远方不再模糊。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要是下雪,就不禁觉得——会下个不停,
也好,为了不让她眯起眼睛
我用手掌遮住它们,眼皮
不信会有人来解救它们,
就躁动不安,仿佛掌心里的蝴蝶。
一切新鲜事物与我们是如此格格不入,
以致睡梦中的紧紧相拥
会败坏任何精神分析学的声誉;
以致紧贴在肩膀上的双唇
和我吹灭蜡烛的双唇不顾
一切地融为一体。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在破旧的印花壁纸上,蔷薇科
换成了满满的小白桦林,
两个人也都有了钱,
整整三十天,大海上舌状
的晚霞以大火吓唬土耳其。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没有书,
没有家具,没有器皿,陈旧
的小沙发在出现之前就是这样,
一个三角铁竖着放在小沙发上,
当初一位熟人把它竖在
相连的两点之上修复了它。
我和她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我们用自己的身影
做各自的门——工作也好,睡觉也好,
却始终敞开门扇,
显然,我们就是穿过这些门扇,
走出暗道,奔向未来。
1968年
黄昏
雪从棚顶下的缝隙
落在干草上。
我摊开干草
看到了一只螟蛾。
螟蛾啊螟蛾,
你钻进干草棚
躲过了死亡,
总算能活下来过冬。
螟蛾爬出来一看,
只见“蝙蝠”在冒烟,
原木的墙壁
被照得通亮。
我把螟蛾移到面前,
看到它身上的薄粉层
比火焰,比自己
的手掌更清晰。
在黄昏的雾霭里
只有我们两个。
我的手指很暖和,
宛如七月的天气。
1965年
作者:蒋楚婷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徐坚忠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