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
对不速之客,一般都不会欢迎。鲁迅同样如此,甚至更为反感,这在鲁迅的日记中有特别强烈的表示。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的性格和处世待人的风格。
1913年1月25日:“晨忽有人突入室中,自称姓吕,余姚人,意在乞资,严词拒之。”这时鲁迅住在北京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一般外人很少进来。这天是星期六,一大早突然闯进个陌生人,素不相识,自称是余姚人,意思是与鲁迅同乡,开口要钱,其实余姚与绍兴相隔数十公里。时值冬日早上,外面正在下雪,鲁迅晚睡,早上起得晚,让他这样直接冲进房间扰嚷,当然很不悦。
1914年2月7日:“有一不知谁何者突来寓中,坚乞保结,告以印在教育部,不甚信,久久方去。”巧得很,这天也是星期六,也是下大雪,不过是晚上。这位不速之客更加冒失,撞进来非让鲁迅替他作保。当时很多人到北京考文官,需要有北京人士作保,鲁迅是教育部官员,所以经常为人作保。就在这天前后,鲁迅多次为人作保。但作保是要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如果被保人出了任何涉及法条的事,保人是要受牵连的。当然,为人作保尤其是为熟人作保的事是很常见的。有时鲁迅作保的人自己并不熟悉,但有可靠人士带来,自然不成问题。这位不速之客,与鲁迅并不熟悉,强行要求鲁迅为他作保,当然为鲁迅所峻拒。鲁迅不能明说拒绝,就借口说印章在教育部,没法盖章。可那人还是不相信,纠缠了很久才走。
有时是熟人带来陌生人,对此,鲁迅的脾气是开始一般不对陌生人示好,不会表现得很客气、很热络。可一旦谈得投机,以后就会非常健谈。1913年1月27日:“晚阮和孙来访,并偕一客姓曾,是寿洙邻亲戚云。”阮和孙是鲁迅大姨母的儿子,也即鲁迅的表兄,比鲁迅大一岁。他当时在山西做幕友,来北京时顺道拜访鲁迅。但他偕来一人鲁迅不认识,阮只介绍说是鲁迅塾师寿洙邻的亲戚。鲁迅没有问其名字,显然与他没有多交谈。这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待人接物风格。
即便是熟人,如果是在早上,也有吃闭门羹的可能。有的人不知道鲁迅的生活习惯,就会感到被冷落了。1923年9月23日,“晨和森来,尚卧未晤。”还是那个表兄阮和孙,早上突然造访,但鲁迅还睡着,便吃了闭门羹。从鲁迅的《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可以知道,早上九点半鲁迅还没有起床。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说明问题。1924年2月17日,星期天,下午:“蔡察字省三者来,不晤。”这个人鲁迅应该是知道的,虽然并不熟悉。但他来得也不是时候。这天是星期天,鲁迅不上班,这时恰好有客人在。这天下午接连有弟子宋琳、许钦文来,还有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来访。这些人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人物,也不会有多么重要的事情在谈,再增加一位来客也不是不可能,但这位不速之客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事先没有约定。
另一位没有约定的熟人来访,鲁迅也不予接待,1924年2月18日:“晚空三来,不晤。夜成小说一篇。”陈空三是北京世界语学校的创办者之一,曾经聘鲁迅在该校任教。这天晚上,鲁迅正在写小说《幸福的家庭》,需要一气呵成,大约因此不接待来客。
最使鲁迅反感的一个不速之客,就是所谓“杨树达君袭来”事件。1924年11月13日日记:“上午有一少年约二十余岁,操山东音,托名闯入索钱,似狂似犷,意似在侮辱恫吓,使我不敢作文,良久察出其狂乃伪作,遂去,时约十时半。”这里鲁迅没有提到来者的名字,只说“托名”,事实上来人自称杨树达,似乎精神不太正常,来意是向鲁迅要钱。鲁迅也知道他不是杨树达——鲁迅原就认识杨树达。但鲁迅怀疑来人是装疯,因而更加厌恶。当晚鲁迅写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作为声明。后来鲁迅了解到,这位学生真名杨鄂生,确实精神不正常,正在发病时。鲁迅听后非常抱憾,因而又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两则予以澄清。三天后,鲁迅还得到过真正的杨树达即杨遇夫的来信,信的内容不得而知,或许与这事有关。但无论如何,这件事对鲁迅的影响是加重了“多疑”的倾向。凡是突兀的、临时的、匆忙的人和事,都会加重鲁迅的多疑。
还有些时候,虽然既不是休息时间,也不是素不相识,甚至是经常见面的老朋友,在突然来访的情况下,虽然鲁迅也会接待,但是心里却未必舒服。例如1928年7月2日:“午赵景深、徐霞村突来索稿。”鲁迅没有拒绝接待,甚至也没有婉拒的意思,但在日记中记下了一笔,虽然没有指责、批评,可仔细玩味其措辞,一个“突”字还是很明显表露了不满之意的。
这种情况,一直到老也没有改变。1936年8月29日有“上午得自称雷宁者信。”虽然没有更多的褒贬,但是“自称雷宁者”的提法就传达了这样几个信息:第一,鲁迅不认识他;第二,鲁迅也不相信他真叫雷宁,因为这姓名只是“自称”的。第三,鲁迅对这封信满腹怀疑。所以,虽然只是短短的九个字,却反映了鲁迅的交友观。越到后来,这种情况越多。鲁迅晚年碰到不速之客时,由于政治环境险恶,更多是拒绝见面,时常声称不在家。1930年1月9日:“午有杨姓者来,不见。”这人显然也是突兀来访,鲁迅连对方的姓名都没有记下来。
最令鲁迅气愤的是诗人林庚白的来访。林庚白是南社社员,曾经担任中国大学和俄文专修馆法学教授,众议院及非常国会秘书长,1929年时,他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12月24日鲁迅日记:“林庚白来,不见。”到26日,就有“晚林庚白来信谩骂。”这封谩骂信历经近八十年的沧桑,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鲁迅的收藏品里。我们不妨来见识见识:
鲁迅先生:
前天去看你,一半是因为我向来喜欢找生人闲谈,一半是我对于你有不少的怀疑,所以要谈谈。并非什么“慕名”,更说不上别的啊!可是你明明在家,却先要投个名片,结果是以不认识我的原因,推说上街了。真使我联想到吴稚晖自己对人家喊说“吴稚晖不在家”一样的高明!敬佩之余,得了一首旧体诗,写给你笑笑!末了我又感着四个疑问,一,鲁迅居然也会“挡驾”吗?二,鲁迅毕竟是段政府底下的教育部佥事不是?三,鲁迅或者是新式名士?因为名士不愿意随便见人,好象成了原则似的。四,象吴稚晖一流的鲁迅是否革命前途的障碍物;要得要不得?这几个疑问,请你来复吧!
讽鲁迅 有引
余初不识鲁迅,顾以夙喜无介诣人,又每疑鲁迅近于吴稚晖一流,造访果尔,诗以讽之,鲁迅其知返乎?
鲁迅文章久自雄,痴聋如许殆成翁?
婢知通谒先求刺,客待应声俨候虫。
毕竟犹存官长气,寻常只道幕僚风。
景云里畔飘檐滴,一笑先生技未穷!
鲁迅先生以为如何?婢字也许太唐突,说不定是妻,女,妾,随便用那一个字吧!
庚白
十二,二十六,上海
如果说,前面的内容还只是无聊,最后一句却是十足的“谩骂”了,难怪鲁迅不屑一顾。林庚白写了一封信,还不肯罢休,过了两天,又来一信,又写了一首诗:
刀笔儒酸浪得名,略谙日语果何成?
挟持译本欺年少,垄断书坊是学氓!
垂老终为吴蔡续,失官遂与段章争。
曾闻艺苑呈供状,醉眼镰锤梦亦惊。
这样的诗,未免太失格。林诗人虽然名闻诗坛,其为人格调却如此低下,难怪鲁迅的态度冷淡,令人想起鲁迅的名言,“最大的轻蔑是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但当初林来访,鲁迅没有见他,恐怕还是因为是“不速之客”的缘故。看来鲁迅真要庆幸自己没有接见这个不速之客。不过鲁迅还是把这两首歪诗保存下来了,恐怕也是“立此存照”的意思吧。1933年,林庚白还给鲁迅来过一封信,鲁迅也没有回,而且连来信也没有保留。我们有理由相信,鲁迅对他的胡搅蛮缠,已经轻蔑到觉得连“立此存照”的价值都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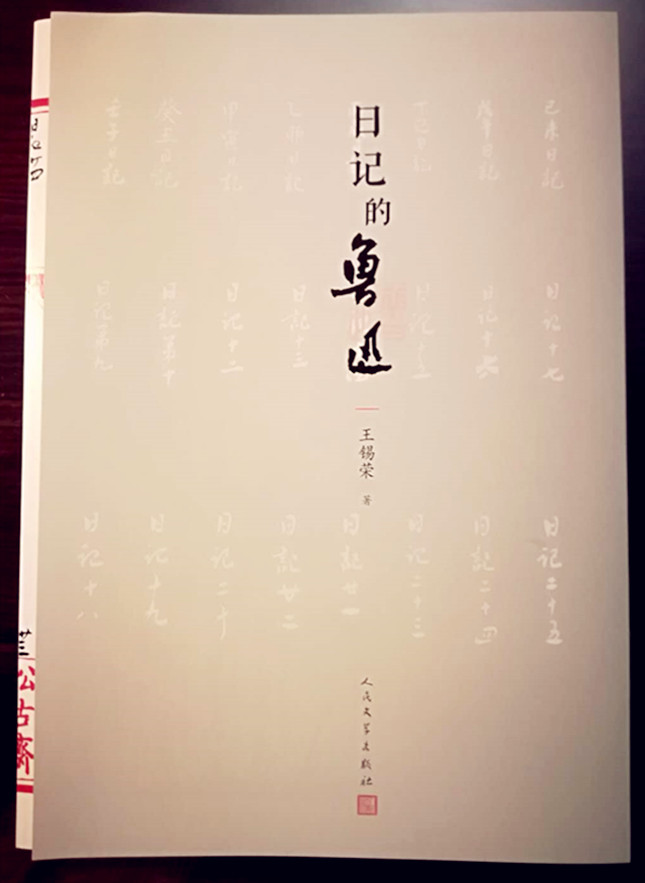
▲本文摘自《日记的鲁迅》,王锡荣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作者:王锡荣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