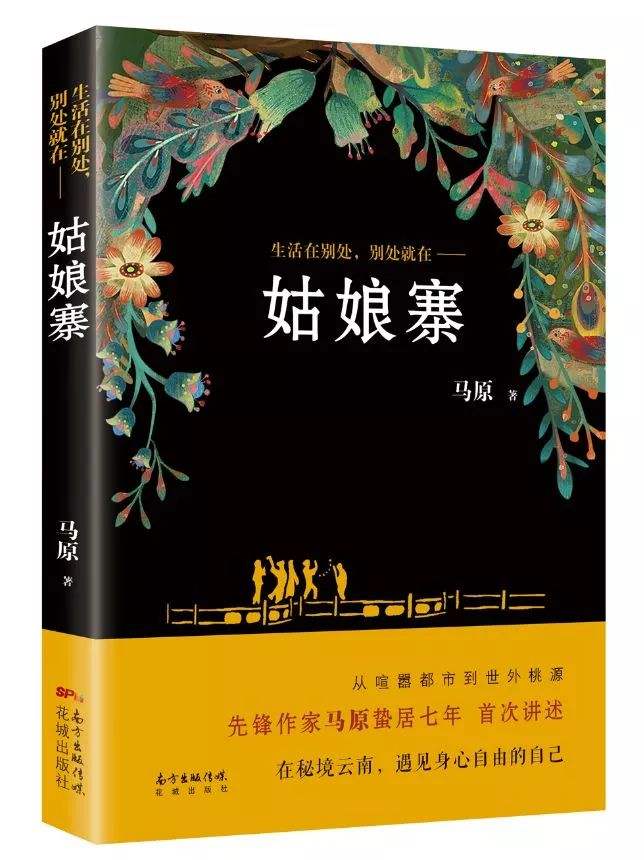
▲《姑娘寨》 马原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提及马原一定是与“先锋”二字挂钩的,他是先锋派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之后因为种种原因马原一度停止了创作,近年来他再度出山,新作不断。今年出版的《姑娘寨》是马原的一部精神自传体小说,具有先锋小说的传承和延续,是典型的先锋归来之作。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在姑娘寨隐居时遇到的一些奇异故事,比如在原始森林中与帕亚马的相遇,为猴子举行送葬大典的祭司与巫师以及其后代的故事,救了哈尼族人的英雄刚拉的故事等。现实与幻想彼此分割却又在姑娘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相互交织。关于西藏的书写曾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参照在马原的作品中呈现,而近期他的创作将地域转向云南,这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无论是气候还是风土人情,都有一种特别的韵味。
从技法层面来说,《姑娘寨》中马原的“叙述圈套”还在延续。比如他曾在《虚构》中采用时间方面的误差来瓦解叙述,在《冈底斯的诱惑》中用“我”“你”“他”这样的交叉讲述视角瓦解叙事,这样的手段在《姑娘寨》中同样出现,他用儿子关于帕亚马的叙述消解“我”从头至尾关于帕亚马的叙述。就连帕亚马的身份作者也进行了瓦解,究竟是哈尼族,还是僾尼族,究竟是帕亚马还是帕雅马,不得而知。叙述空缺也在延续,比如开篇作者便说茶品在他之后的生活中会充当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后文再无与之相关的叙述,而关于帕亚马的故事也戛然而止,再无下文。
同时,《姑娘寨》是一部元小说,融入了大量的真实事件,比如作者的儿子走上文学的道路,作者的疾病、籍贯、在上海当老师的经历等。作者希望让小说变得更为真实,不过这仍是一种掩饰,无论如何,小说是虚构的。元小说实际上仍是叙述主体的问题,在视角选择上,小说有不同的叙述者。比如关于和帕亚马的相遇,有“我”的叙述,“我”儿子的叙述,针对同一件事,二人的叙述完全不同,一个在建构,一个则在解构。不同的视角是为了让叙事变得更可靠。很明显,这些所谓的“我”都不是作者本人,背后仍然有一个隐含叙述者。
叙述身份在小说中至关重要,叙述主体是叙述研究的重要方面。马原的小说中,叙述主体有多个,不断跳角,作家的真实身份、叙述者的身份、幻化出来的身份。非自然叙事的流行正是这种敬畏感消失之后的替代补偿。关于民族的东西书写也较多,提到不少少数民族,可谓民族神话的重述,用隔空对话的方式与民族英雄帕亚马对话,虽然最终帕亚马不复存在,是儿子眼中的幻觉,但是没遇见不意味着不存在。关于灵异和神秘事物的书写比比皆是,与帕亚马的相遇,松鼠会与人对话,贝玛拥有三项超能力,马莉雅怀胎三月便产下男婴等等。
《姑娘寨》有作者不少的思索在里面。小说写到,祭司和巫师都失去了职业,竟要为一个猴子举办一场盛大的祭祀典礼,甚至由此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瘟疫。很明显,作者有着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敬畏感。同时,还以此为契机对历史书写提出质疑。作为50后的作家,尽管马原的技法时髦而新奇,骨子里却是对经典作家的致敬与回归,是对现实生活虔诚而热切的拥抱。小说中绝无真正无意义的闲笔,一切的冗余其实都是经过作者精挑细选才得以出现在文本之中的。
有评论者指出,从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苏童、马原这一批作家开始,才是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起点,是现代性得以真正确立的标志。现代性是一个长久的问题,小说一般而言有四种召唤,游戏的、梦的、思想的、时间的召唤。《姑娘寨》对神秘边境的书写很明显带有一种现代性反思,是对存在的敬畏,对未知的敬畏,也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陷入一种“对存在的遗忘”的状态之中,小说正是对“存在”的唤起。
《姑娘寨》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一部寓言,或者也可以称作喻世明言,它有最神秘的书写,最终指向的却是现实、社会以及每一位个体。马原近年来的创作题材不断扩充,努力实现技术与思想的双重突破。其他作品也可以拿来互文阅读,比如他的《黄棠一家》是一部深入现实的作品,涉及官场、商界、疾病、婚姻等多种现实主题,是马原由先锋转向现实的作品。小说书写了时代震荡带给人们的伤痛,反思了命运的荒诞性。但无论用什么样的笔法,都体现了马原对现实社会和人的存在的深度思索。
作者:刘小波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周怡倩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