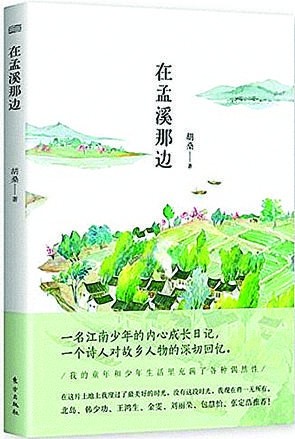
▲《在孟溪那边》胡桑著东方出版社出版
2007-2008年,身在泰国普吉岛、未到而立之年的胡桑完成了这部乡愁之书。
乡愁是历史意识中最难捉摸的。人到晚年,对乡愁或返乡的书写,浸透了时间的智慧。古诗云“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意味着,通过“相见”,确认了自己的伦理位置与灵魂居所。这是用一生来寻找的所在,就如特朗斯特罗姆诗云:“记忆看见我。”那么,有着哲学博士学位的胡桑如何书写乡愁?
他笔下的乡愁,批判都市和商业,希望亲近乡土,以此获得存在之家:
上海的超市覆盖了新市镇,超市里什么都是现成的,况且已经没有几个年轻媳妇会做麦芽饼、包粽子了,渐渐地大家会忘却这些手艺。孩子们不知道风筝的做法,油菜地只剩下零星的小块,当时的大人快成老人了,现在的大人忙碌地来回在去乡镇企业的路上,骑着速度极快的摩托车,交通事故逐渐增多。
乍看,这是缅怀乡土、厌倦都市;细思,并非如此。这段出自《雪:一个世界的逝去》的乡愁,与其说是“城市/乡土”的二元对立,不如说是对自己具有绝对归属感的记忆的追溯和建构:
我书写的不是对农业文明的乡愁,我只是极其偶然地出生在了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三角洲腹地的一个封闭村落。假如我出生在都市,我会以同样的语言方式去书写街道上、弄堂里、商场内部的那些繁复事物。
胡桑的乡愁极具语言意识,将言说视为存在之家。这在他的写作中可分为两个过程:其一,他找到了江南古典诗歌与其自身生活经验之间词与物的对照,这突出呈现在《隐逸的江南》里。这意味着,他为物找到了词,找到了事物进入言说的入口,从而可置身于这一传统或方式中确定自己与故乡的关系。其二,他努力使用自己的词来命名这些物,命名故乡,就如江南先辈诗人那样,让故乡在自己的言说中显现、敞开、得以庇护。在此过程中,言说者将故乡命名为某种不可抵达或必将消逝之物,自己则相应地成了永远的异乡人。这便是全书的重点所在。
在胡桑的言说里,异乡人存在着原初创伤式的、来自儿时的对故乡的恐惧。他的言说极具寓言风味,比如对水的恐惧、与成人交谈的恐惧……这些构成了事件性的意义,构成了异乡人言说中源头性的存在。这是对自己与故乡之间裂隙与纠葛的隐喻:
水是一种古怪的生灵,它有着自己的躯体和生命。在我的周围悄悄生息。水不可能是一种无色无味无臭透明的液体。它是面目乖戾的魔鬼。它又是我特殊的亲人。我的敬畏而亲和的神祇。
与这种恐惧相伴的,则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欲望。这在书中多有呈现。一部分是对偶然闯入物的书写,比如顺着水流漂进故乡的什物,比如疯子、乞丐、商贩等闯入者,这些最终都指向对外部世界之欲望的追忆和言说,并由此实现对自己异乡人身份的建构。
如果说对闯入者的书写来自真实经验,那么对天文学、地理学这些儿时趣味的追忆则是以知识和想象力为纽带,构成了胡桑对外部世界欲望的另一面:
天文学之于我,与地理学之于我的意义是一样的,它们使对外部充满好奇的我在物质上不能超越故乡这块狭小的地域时,得以在意识里去拓展一片壮丽的疆土。所不同的是,地理学是在大地表面,天文学则向上深入无限的宇宙内部。
借由这些知识所达成的对想象力的发现,在胡桑的生命史中意义重大,这衔接了他后来对以写作为志业的确认,尤其是诗歌这一极具想象力的人类精神劳作:
我把迷恋天文学时对世界的全部想象和奢望移植到了诗里。天文学让我第一次触摸到了时间的羽翼。现在,我始终认为,写诗是坐在时间的翅膀上穿越世界的一种方式。
借由闯入者和想象力,胡桑得以突破故乡的限制,完成身体对故乡的突围。然而这尚未意味着他完成了对自己异乡人身份的书写。一个重要的步骤是离乡后对故乡的追忆和对过往时光的守护。在对故乡的雪的书写中,胡桑制造了这种消逝感:
雪已很少下了。我说“了”的时候,又一次感觉到了这些事物的逝去。
它永远地降落在故乡。不会死去。即使一个旧的世界死去了,那片阴凉依然匍匐在我心头。让我冷却下来,并且幸福。
胡桑书写乡愁的重要特色,是借助自然风物。它们成为他追忆时光的载体,从而召唤出“事物在时间中的印迹以及曾经存在于世的气息”,“正是这种气息塑造了我对世界的感受力以及想象力,它们最终在我的体内凝聚为对待世界的方式”。对自然之物的召唤,使他得以在消逝中追回过往的时光,将乡愁变成一种恒常性的气息,随身携带,永远守护,并指向未来。这颇具东方的智慧和美学。
身在故乡,无法远行时,我们思念未来,思念外面的世界;当羽翼渐丰飞离故乡渐行渐远时,我们需要返回内部,为乡愁赋形。这既意味着心智的成熟,也意味着生命时空的开阔和贯通。故乡在胡桑的言说里不再是儿时那个常常幻想着突围的藩篱,而是自己在世的重负,漂泊的伴侣,生命的守护。“离别,是为了返乡”,没有乡愁的离乡者,只是漂泊者,而不是异乡人——异乡人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乡愁,让它活在自己体内。
由此,胡桑书写乡愁,不同于晚年之人“记忆看见我”式的泰然和平缓。他在最好的年龄里,不是为自己建构一个安居之所,而是建构一种守护。随身携带乡愁的人,是异乡人的另一个名字。胡桑书写的乡愁,不局限于狭义的故乡,而是构成异乡人身份的一切必然消逝的事物。
携带着故乡前行,故乡也会随着自己生长、变化。胡桑不是用记忆为自己建造一个终点,而是从记忆中找到一个终生伴侣,一起成长、扶持、前行。
文:李海鹏
编辑制作:朱自奋
责任编辑:薛伟平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