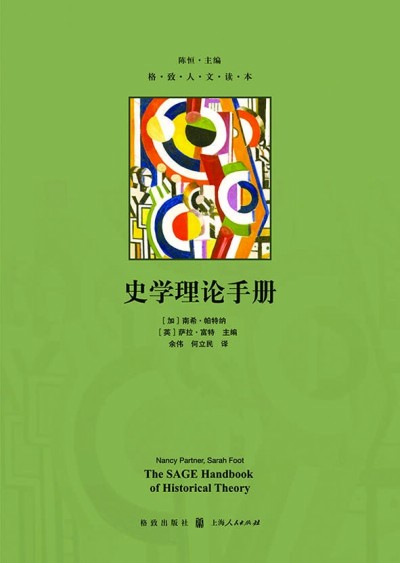
《史学理论手册》
[加]南希·帕特纳 [英]萨拉·富特主编
余伟 何立民 译
格致出版社出版
李娟
距今一万五千年以前,在位于今天法国拉斯科的洞窟中,一些原始人类正在岩洞壁上勾画着野马、野牛和鹿。1940年,当这些史前画作重现天日时,举世震惊。关于原始人勾画这些动物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但无论是倾向于宗教仪式、日常行为还是艺术想象,总逃不脱“记录”这个概念。将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甚至想象中的事物,用尽一切方式保留下来,这也许是人类的本能。当人类的历史足够久远时,这些记录中有一类便脱颖而出,它是对往昔的回忆、总结和反思,对现实问题进行解答,甚至定义着一个族群的来龙去脉,只是那时它还没有“历史”这个名字。
荷马吟唱、希罗多德朗诵、太史公奋笔……时至今日,历史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认同途径,建构、解构和重构着我们对于自身、社会和世界的认知。然而,即便在古老年代,对历史叙事的质疑就已经产生了。古代哲学家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就在《皮浪主义要旨》中指出,人不可能知晓过去。意大利哲学家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更是在《历史十谈》中重点讨论了“历史的真相”,主要聚焦于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之间存在矛盾的问题。菲利普·锡德尼爵士在《诗辩》中更是赤裸裸地嘲笑史学家是“住在故纸堆里的人”,“很大程度上明显是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赋予自己的研究以权威性”。更不要说中国古代发达的史学批评和文献考证,不断对历史叙事进行的质疑和批判。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件的描述和解释存在巨大差异,这是让人对历史叙事产生质疑的根本原因之一。
十九世纪,随着历史学科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进程,这片同历史叙事形影不离的阴影,变得愈发浓重。为了消弭这片阴影,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斗争良久。然而,就是在这漫长的斗争中,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片阴影源于历史学本身。史学家就如同一只翱翔天际的飞鸟,俯瞰着人类历史的曲折变化,却永远飞不出自己的影子。这影子,便是我们的认知方式、价值立场、叙事风格等等,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的主观性。今天,我们把这一领域的研究称之为“史学理论”,也是《史学理论手册》的主要内容。长期以来,这一战场中的主要问题是,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同历史知识的主观性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鸿沟大到一度让人丧气,无论是描述、解释还是证据,历史叙事的各个方向都笼罩在主观性的阴影之下。历史与文学区别何在?失去客观性的历史还是历史吗?这些问题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历史死了”这句后现代名言。
然而奇妙的是,随着所谓后现代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非但“历史没有死去”,对于那片笼罩历史学的阴影,也有了更深入的认知。正如《史学理论手册》中所言,“史学理论是一套严密规整但又有所弹性的框架组织,支撑着历史知识分析,并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能获得怎样关于过去的知识,确切地说,即历史知识是如何被建构、编排和表达的”。也就是说,史学理论关注的不再是往昔,而是我们自身,是我们思考和表达往昔的方式,是人类的历史思维本身。也正是借由后现代史学理论的东风,现代历史学科才得以或主动或被动地拆解所谓“科学历史学”设下的诸多藩篱,挖掘出历史思维中的丰富元素,重新实现同宗教、文学、艺术和政治的种种联系,发现传统史学的盲区,在深度和广度两个层次上完成历史学的飞跃。
飞鸟的影子不是阴影,而是镜子,是人类思维的关怀。世间万物,唯有打上思维的印记,才能进入人类文化的范畴,花草树木如是,历史亦如是。我们透过这阴影之镜看到的,终究是自己。我们通过历史传达的,除了人物和事件,更重要的是思维和价值。也许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会有曲终人散的一天,犹如人类历史上那些曾经出现过、闪耀过的学科门类,但是作为一种思维形式的历史,相信会与人类同在。数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夜晚围坐在火堆旁,靠讲故事打发漫漫长夜;现代人捧着纸书、电脑或kindle,检阅历史。在经历了若干周折之后,历史学仍要回到自己的过去,从学科诞生之前、蓬勃多样的历史思维中汲取养分,正如该书最后一篇文章所阐述的——《应用基础:亚里士多德的叙事理论和后现代史学的古典源头》。
最后,想就翻译说几句。非史学理论研究专业的读者,必定会被书中各种理论术语、复杂的句子结构和不符合中文的表达形式所吓到。这也是我们所有学术翻译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语言是存在的家,学术翻译的家有两个,是背叛母语还是背叛外语,实在令人头疼。我赞成该书译者的处理方式,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直译加语序调整的方式,尽可能保留学术语言的原始风格。正如当年佛经东传,高僧大德们在译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将源自梵文的词句和语法结构纳入了汉语。史学理论在中国仍旧是非常小众的学问,即便在史学界也是如此。这本手册集合了众多西方史学理论专家的作品,引入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和问题,值得对往昔和历史感兴趣的人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