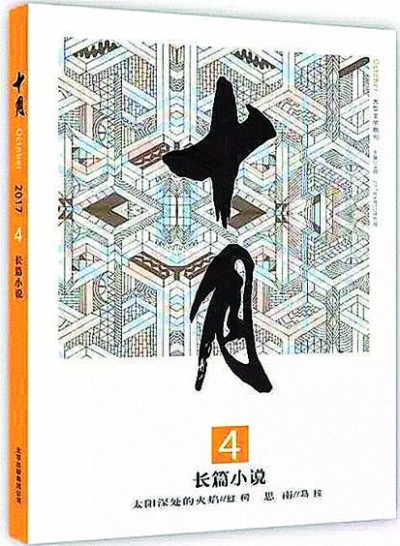
红柯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首发于《十月·长篇小说》2017年第四期。
刘小波
红柯最新作品《太阳深处的火焰》,仍采用复调式叙事结构。小说的一条故事线索是吴丽梅与徐济云的爱情故事,另一条是徐济云的学术成长史及其带领研究生研究皮影艺术的故事。不同于以往作品,红柯此次创作在延续以往神性写作的同时,加入了对现实的深度描摹,从而以冷夸张的叙述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他以自己的工作环境为切入,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揭露客观真相,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学术界在体制化、功利化驱动下的种种丑态。
红柯的作品聚焦西域大漠。正是在那儿恶劣的生态环境中,生长着生命力极旺盛的杨树、柳树,羊群、牛群、骆驼群,以及生生不息的普通人。从《西去的骑手》《大河》《乌尔禾》《生命树》《阿斗》《好人难做》《百鸟朝凤》到《喀拉布风暴》《少女萨吾尔登》以及最近出版的《太阳深处的火焰》,都具有这样的重复性叙述。
小说的阐释,一定程度上通过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对作家的解读,也可从重复这一角度展开。综观红柯的创作,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复,分别是非自然叙事、对自然的崇拜、音乐的合理使用。
非自然叙述
艺术符号具有规约性,创作中又须不断打破规约,完成自我更新。小说创作中,这种反规约主要通过非自然叙述等手法来实现。主流叙事理论建立在模仿叙事的基础上,即叙事受到外部世界可能或确实存在的事物的限制。而当代叙事学发展的新动向则是反模仿的极端叙事,即非自然叙事。于红柯而言,特殊的地域环境造就了其独特的想象,他的作品恣意汪洋,亦真亦幻,具有神性写作的一面。西域是多种宗教交融之地,民间想象力极为丰富,这也直接影响了红柯的创作。
红柯想象力丰富,其作品具有神性,很多诡谲的叙述打破了自然规律。《乌尔禾》中的海力布被塑造成具有神性的英雄,他懂鸟语,与蛇精和谐相处等等,都是非自然叙述。《喀拉布风暴》中关于地精以及武明生家族,作者也大胆地描写了大量民间的性故事、性传说和性知识。这些非自然叙述甚至引起读者关注与质疑。
这样的写作,某种意义上与读者好猎奇的阅读心态有关。小说须有故事,情节越离奇,读者越易走进故事甚至产生代入感。虽然许多作者强调并未猎奇,事实却并非如此。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延续。很多传统文学具有非自然叙事的特质,如志怪小说、神话等,包括《搜神记》《聊斋志异》《西游记》,就连《红楼梦》也有太多的情节超出了日常生活。再则,作家受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的滋养,西方大量作品采用非自然叙述,如《变形记》将人异化为甲壳虫,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和伍尔夫的《奥兰多》等都属于非自然叙述。非自然叙述是艺术对现实的提炼、夸张和变形,能使作品更具张力,更具文学性和艺术性。
自然崇拜
在红柯的作品中,动植物与人一样成为作品的主体。大漠里的胡杨树、红柳等植物,白羊、骆驼、狼等动物以及沙漠、盆地和河流等无生命的自然物,都是作者不遗余力描写的对象,如《西去的骑手》中的马,《大河》中的熊,《乌尔禾》中的羊以及《生命树》中的树。在《太阳深处的火焰》中,比胡杨更有生命力的红柳成为“太阳深处的火焰”,这也是红柯这部新作的命名来源。西域大漠的人和事,包括飞禽走兽、草木砂石,都与主人公共存共荣。在山川、河流、大地以及动物之间,人类找到了生命的根基。
《喀拉布风暴》中的风暴,这一自然现象可谓小说的另一主人公。风暴不仅具有摧毁性和破坏性,而且具有生命力,是自然界检验生命韧性的工具。在大西北沙漠瀚海中,肆虐的黑色沙尘暴被称为喀拉布风暴,它冬带冰雪,夏带沙石,所到之处,大地成为雅丹,鸟儿折翅而亡,幸存者衔泥垒窝,胡杨和雅丹成为奔走的骆驼。而在《太阳深处的火焰》中,作者对塔里木盆地的描写已完全融进小说。红柯不止一次说过,景物也是他作品的主体。
对于离太阳最近的羊的描写,则在红柯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包括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对放生的描写,这一切,都表现了对生命的敬畏。
对自然的崇拜,也是对生命的赞歌。《大河》是生命不死的颂歌,《西去的骑手》是有关英雄和血性的史诗式长篇,《喀拉布风暴》表现生命面对苦难时的坚韧与顽强。《太阳深处的火焰》中,红柳就是火焰,照亮万物的生命,包括民间艺术皮影,作者将各色人等编进故事置于西域风沙的洗礼中。神性的背后,是现实的书写,对历史的书写,对一代边疆开垦人的书写。
音乐元素
小说不乏音乐叙事,当代小说尤为明显。音乐可充当叙事元素,推动情节发展,与小说文本形成张力,深化主题。音乐还能彰显风格,强化情感。
红柯的小说中有大量的音乐元素。《生命树》用歌曲推进叙事,具有蒙古史诗《江格尔》的风味。小说穿插两种歌曲,一是蒙古古歌,这是关于灵魂的音乐。蒙古奶歌在文中多次出现,牛禄喜和马来新的友谊中有奶歌,马燕红在挤奶的过程中悟出了佛性,其间多次响起奶歌。另一是时代流行曲,现代文明在大草原的印迹,也是王蓝蓝、陈辉等人生活的侧影。
《故乡》的情节同样以歌曲推动,故事极简单,情感则极浓郁。故事主要讲述回乡探母,情感主要通过歌曲来抒发。歌曲《我的母亲》在文中反复出现,浓缩了太多的情感。作者把母亲的爱和泉水相提并论,既洗涤了作者的衣裳与双手,更洗涤了作者的灵魂。文中歌声第二次响起,是大学生周健在周原老家时,《大月氏歌》与《我的母亲》接连奏响。当他默默记下这首古歌时,勾起了对家乡的无限思念。歌声第三次响起时,天空中的白云消失,仅留孤零零的鹰。此时的情感又具有另一层色彩,《大月氏歌》是草原的历史,是人们心中最隐秘的伤痛。
红柯对民间音乐情有独钟,搜集了大量民间歌手专辑。这种音乐情怀延伸到创作中,音乐被广泛运用于小说中。除了体现作者的立场,音乐还有助于抒发满腔的情感,凸显浪漫情愫。红柯因其作品流露出浓郁情感,而被冠以浪漫主义者。
红柯游走于西域与关中,勾连起来的是对生生不息的人间万物的颂赞。红柯的根深植于大漠,大量事物、人物、传说、故事、情节、情感等已然书写、反复呈现,小说结构、叙述手法等技法层面也有诸多延续,后期创作除了笔力的进步,融进了更多的人文思考。总体而言,红柯的小说是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命力的讴歌,对苦难的隐忍,对人性的歌颂,对西域大漠的独特情怀。神性中有人性的呈现,是神性与人性交织的生命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