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档案】孟宪承(1894.9.21—1967.7.19),江苏省武进县人。我国现代教育家与教育理论家。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中院和圣约翰大学,1918年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1年又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深造。回国后,先后在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1951年出任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2006年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首批宣传名单,是其中唯一的教育学家。
回望20世纪的中国教育史,一代代教育学家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经历了从移植西方经验到不断本土化、民族化的艰难求索,他们的筚路蓝缕、薪火相传,共同谱写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而孟宪承,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从私塾出发、历经西式学堂,又负笈英美,这样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为他的教育思想奠定了底色——他总是以一种国际性的眼光审视中外教育现实,既善寻他山之石,又立足于本民族传统,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
从20年代起的30年岁月里,孟宪承的名字一直频繁出现在中国教育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里:1933年1月中国教育学会成立,选举陶行知等15人为理事,他列名其中;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部聘教授共29人,他是教育学科唯一入选者;1951年,担任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他始终走在中国教育改革的前列,与其他教育家一起,共同引领着中国教育发展的潮流。
“土佬儿”其实是个“洋秀才”
孟宪承1894年出身于江苏省武进县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早年去世后,母亲杨氏将他带回娘家抚养,杨家为常州望族。家学渊源让孟宪承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年幼时母亲便教他诵读和习字,6岁送他去私塾。据杨家人回忆,孟宪承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陪伴母亲和刻苦读书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用功的孩子,真是孟夫子家的后代。”
如果不是因为时代的巨变,孟宪承也许会同他的父亲一样走上科举之路。然而,20世纪初,内忧外患的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科举制被废、新学制设立、新式学堂发展、鼓励留学等一系列举措,让中国的现代教育就此蹒跚起步,而孟宪承的人生轨迹也因之发生了重大转折。
1908年,孟宪承考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中院(中学部)。1912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外文系,与他同窗的林语堂曾回忆,“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圣约翰每年毕业率很低,孟宪承入学时班里有二十几人,但毕业时获得文学学位的仅有八人。凭借着读书期间“试必冠其曹,恒以退还学费为奖”的优异成绩,他在八人中拔得头筹。1916年,毕业后的孟宪承以中等科英语教员的身份来到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与林语堂、马国骥等共事。曾为其学生的梁实秋多年后回忆,“林先生活泼风趣,孟先生凝重细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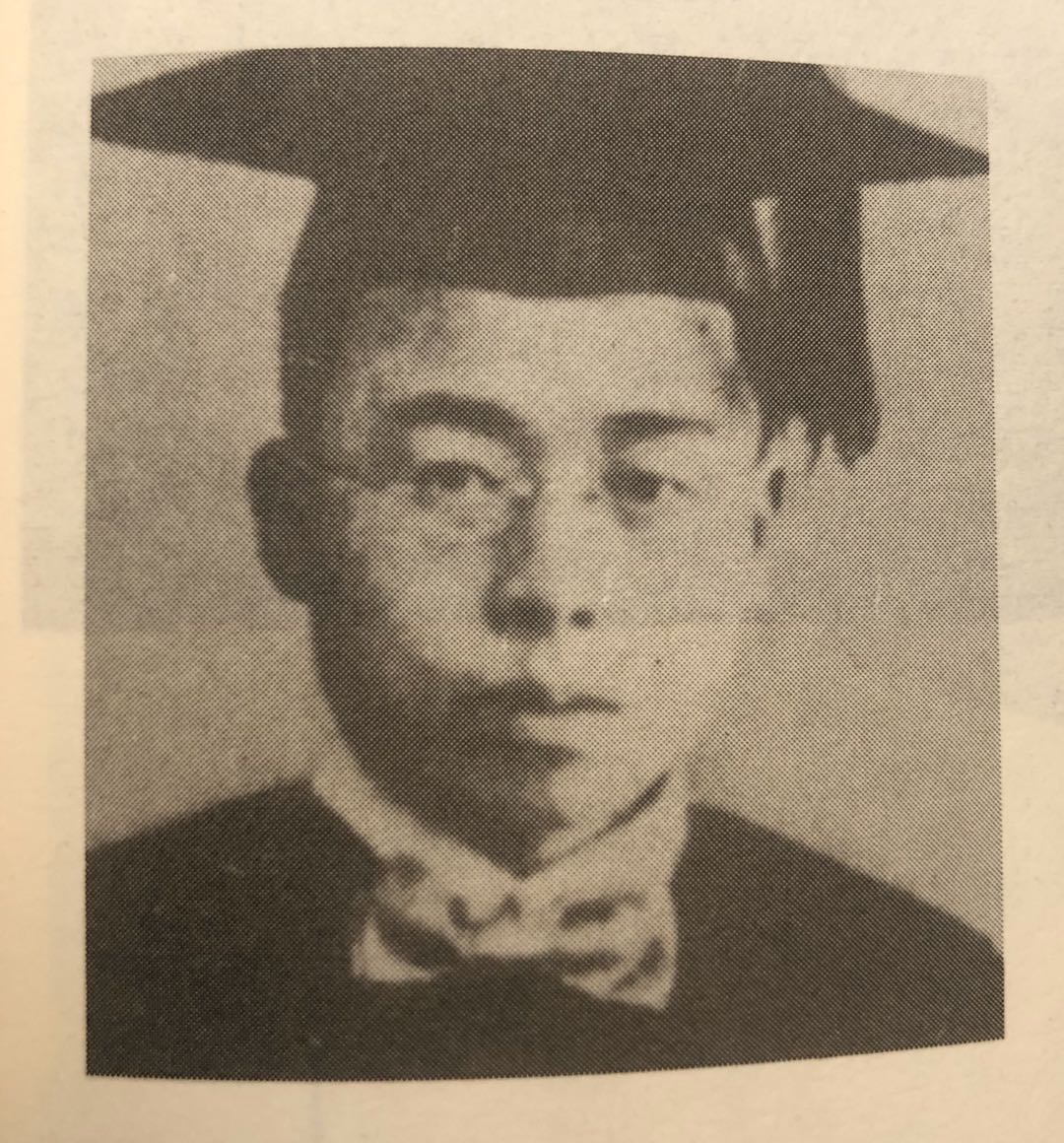
1916年孟宪承先生从圣约翰大学毕业时的照片
清华是当时庚款公费留美预备学校,而渴望走出国门,“藉资历练,稍获新知”也是孟宪承一直以来的梦想。1918年,考取公费的他赴美入华盛顿大学师从杜威,主修教育学、副修哲学。1920年,获教育硕士学位后,转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深造。但因需供养家庭而中断学业,于1921年11月回国。对那代留学生来说,祖国的崛起和民族的兴盛是终身相伴的梦。留学经历让孟宪承切身感受到工业革命后西方诸国的强大,认识到教育改革在其中的推动力,也更坚定了他以教育为良方,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现实的信念。
多年来西方文化的熏陶,似乎并没有在孟宪承的生活习惯上留下太多印记。在清华上英语课,他坚持身穿青衫长袍。即便是出洋,外面套着西服,里面穿的也还是夫人为他手缝的粗布衣服。其孙孟蔚彦也曾记录下这样一则趣事:“在旧上海,一次去看牙医,因为一身布衣,身旁的洋人不时假以白眼,待祖父取出洋书来读,洋人便来搭讪,祖父开口便是纯正的英语,洋人肃然起敬,没有想到身旁的‘土佬儿’,实在是个‘洋秀才’。”
“国民教学之不可寄托于外人也”
当孟宪承在外留学时,大洋彼岸的这头,五四时期的中国掀起了一场“民主与科学的教育思潮”,随着杜威等实用主义教育家的访华而更是达到高潮。知识界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杜威学说,在学校中也大力试验。对当时中国教育界来说,实用主义思潮的传播不仅挑战了对自清末以后传入中国的、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西方传统教育思想和观念,也松动了存在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观念。
学成归国的孟宪承,很快成为其中的“主力军”。通过翻译包括美国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杜威的《思维与教学》等在内的多部教育名著,他向国人呈现了一幅国外教育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势的绚丽画卷。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同在教育上的努力,而各国所应付的问题却不同”,“各国的问题不同,所采取的方法也不一”。因而,思考如何将西方教育理论本土化、民族化,成为这一时期他学术探究的重心。
出版于1933年的《教育概论》是这一探索的重要成果。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杜成宪认为,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顺应了当时中国教育学理论的转向,更是在中国倡导了以儿童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立场。原先的教育学著作,从概念出发、注重演绎,其理论体系的展开,通常是循着‘教育的定义’“教育的目的”……这样的逻辑。而在孟宪承的《教育概论》中,第一、第二两章分别为“儿童的发展”和“社会的适应”,立足于教育的出发点——儿童,展开对整个教育问题的讨论。1934年9月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教育概论课程的“教材大纲”与他的《教育概论》十分相近,多少能窥见这部著作在当时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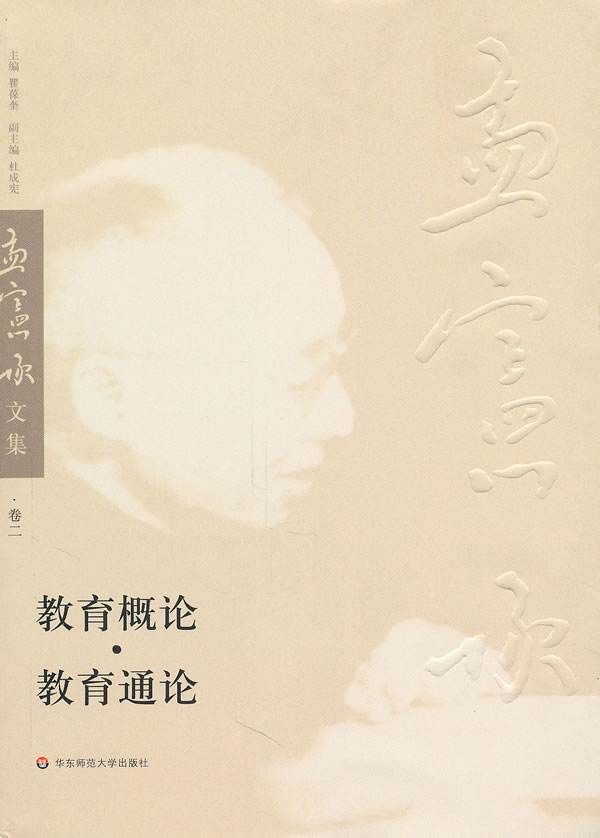
将外来教育资源民族化的努力,在孟宪承那里远不止于“坐而论道”——针对当时教会学校“重英文轻中文”的通病,以及自倡导白话文以来国文教学中出现的问题,1923年,孟宪承回到母校圣约翰担任国文部主任,开始投身于国文教学改革。他大刀阔斧地提出一系列规定:实行统一的中西文学级,中学毕业生达到新定的国文程度方可升学;组织国文教学研讨会,探讨教学原理、制定课程标准等;编纂出版面对学生的国文出版物。他的国文教育主张,“推进了中国国文教育在由文言向白话转型过程中的重建”。
在他任职前,黄炎培曾率专家考察圣约翰时认为“中文改进之计,事不容缓!”而在他改革后,“学生之国文与英文水平相当”,许多学生从以前只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ABC”,转而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产生了兴趣。由于成效斐然,《申报》等当地重要报纸也经常报道这场国文改革的最新情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然而,这场国文教学改革最终因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中断——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上海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圣约翰师生也组织抗议,但遭到校方阻挠。为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6月1日,孟宪承召集学校的中国教授开会,在会上慷慨陈词:“假如做一个学生,只知自己是圣约翰的学生,而不知是中华国民,看到同胞为外人屠杀漠不关心,这对我们平日所讲的国民自觉教育,将无法自圆其说。”“教师应该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否则,今后我们也无颜再以学问文章与学生相见于讲台”。在师生的据理力争下,校长卜舫济被迫同意学生罢课、降半旗向死难者致哀,不料却在6月3日出尔反尔。师生终于“义愤填膺,忍无可忍”。以孟宪承为首的19名教师带领553名学生,宣布“永远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发誓“以后不再进任何外国教会学校”。
圣约翰师生的这场壮举,在当时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上海学生会联合会致信称赞道:“于此全国愁惨之空气中,忽现一线曙光,使顽夫兼懦夫有立志,此不幸中之幸也。……此次约大学生独能以爱国心,与人格为天下倡,其难能可贵,更非寻常之学校可比。”而经此事件,孟宪承们也彻底认识到,“国民教学之不可寄托于外人也,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同年八月,他们自行创立“光华大学”,孟宪承为十二人筹委之一。
走出象牙塔“为生民立命”
20世纪20年代末,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新式教育在中国越来越“水土不服”。教育家陶行知直接抨击其为“培养小姐、少爷、‘高级废物’的教育”;而孟宪承也展开了反思,他认为其“最大的缺点,在于教育的设施,没有能和国计民生,发生重大的影响。到现在一般学生,还只把求学当作是‘读书’,毕业当作是‘资格’,教的学的,没有的确能增进实际生活的丰富和效能。所以民生是民生,教育是教育,依然没有策应。”
国难当头,当不合时宜的新式教育热潮褪去,如何重构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蓝图,是当时所有教育学人在思考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必须依靠民众力量。为此,不少学者纷纷走出象牙塔,去到城市和乡村,就此开展了一场持续20年之久的教育运动。其中自然也有孟宪承的身影:1929年秋,放弃了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职务的他,到中国第一所培养民众教育师资的学校——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暨劳农学院任研究部主任兼教务部主任。之后,他又在杭州创办民众教育学校、主持江苏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陆续进行民众教育的探索前后跨时8年。
面对新生的民众教育,“孟宪承关注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学院的前途和发展,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民众教育事业的发展。受过良好的外文和教育学专业训练的他,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教育经验,将民众教育的发展置于全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范围进行综合考虑。”(张爱勤语)为此,他阅读了世界先进国家关于成人教育的大量论著,还专门研究了当时在世界成人教育运动中有重要影响的丹麦乡村民众学校运动,留下了以《民众教育》为代表的丰硕理论成果。但纸上得来终觉浅,民众教育是实干的事业,必须回到农村的现实生活中找问题。而孟宪承也深谙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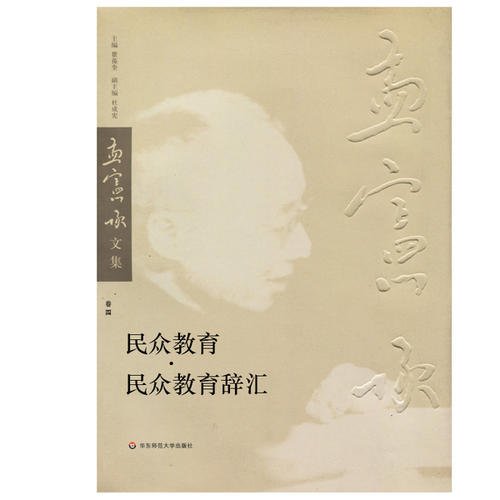
那么,中国农村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当时有人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在于文化的沦丧,要振兴儒家文化来改变,如梁漱溟用文化建设的方法进行的“邹平改造”。但孟宪承的答案则更为“接地气”,他觉得问题在于农民不会过自己的生活。他分析说,民众是绝大多数的直接生产劳动者,他们每天的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劳动,小部分时间是休闲。他们劳动,为的是维持生计;他们休闲,要的是一点娱乐。他们最需要的教育,是“增高生计的知能”和“满足娱乐的兴趣”这两项。
于是,同样是教民众识字读书,他觉得“呆板的照教科书教,不如先教成年民众看洋钞票上的字,看路上布告招牌的字,教他们记账、写信、开发票。”教民众维持生计,他的办法是走职业教育的路,举办“民众职业补习学校”,“乡村注重农业补习,县市注重商业补习”。而怎么让他们的闲暇时光更有意义,他主张“用艺术的手腕”,在北夏实验区设立民众茶园和俱乐部,组织戏剧、曲艺、国技和民众音乐会,以及图书阅览室、巡回电影放映……
在杜成宪看来,孟宪承关于民众教育的思考同样体现了民族化的追求,“他将民众教育的首要目标定位于生计训练而非一般地读书、识字、学文化。他希望通过生计的改善而达到民众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改善,乃至国民经济的改善和民族的复兴。这样的主张与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思想是相通的……他的民众教育探索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体贴’。”
在丽娃河畔践行“大学的理想”
孟宪承曾经说,“现代国家,没有一个不把教育看做是国家的命脉,没有一个不尽力从事师范的培养;为改进中等教育计划,没有一个不在高等教育里,提供师范的训练。”从1921年任教东南大学算起,孟宪承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几乎都与大学相关。通过高等教育培养精英人才与通过民众教育启迪民智,是他所认为的“教育救国”的两条途径,这两者也紧密交织在他一生的学术思考里。
如果说《民众教育》中的孟宪承是“接地气的”、“体贴”的,但同样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教育》里,孟宪承却站在了整个人类教育史的高度,高瞻远瞩地对中国现代大学的理想进行了展望——毫无疑问,“大学是最高的学府”,但大学之“高”不仅仅在于教育体系的层级,而是因为“在人类运用他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发展上,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了。”因而,“大学的理想,实在就含孕着人们关于文化和社会的最高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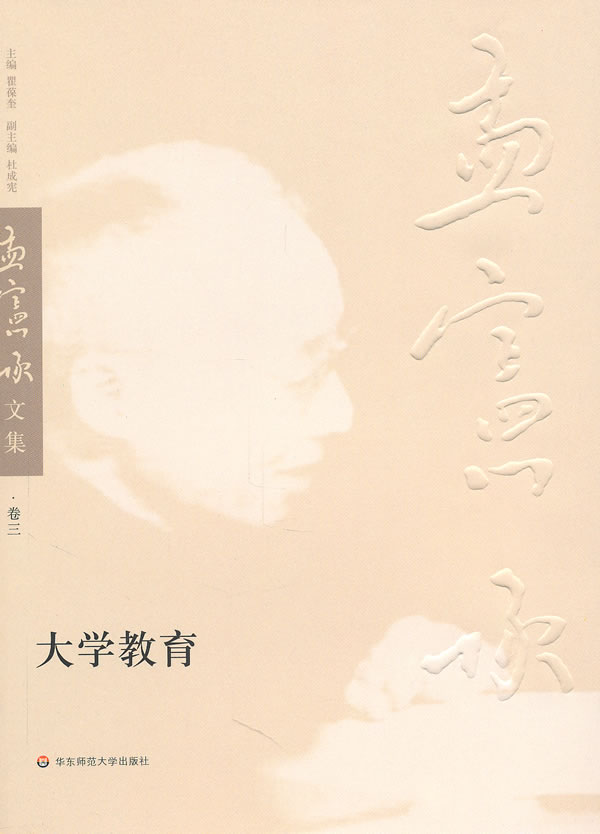
在他看来,现代大学的理想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智慧的创获”。大学精神首先在于发挥研究的精神,致力于创造发明。“到现在,没有哪一国的大学,教师不竞于所谓‘创作的学问’,学生不勉于所谓‘独创的研究’”;二是“品性的陶熔”。他曾引用哲学家怀特海的话,“大学的存在,就是为结合老成和少壮,而谋成熟的知识与生命的热情的融合”。这种陶熔的锻炼,应该以教师对学生人格上的潜移同化等方式来实现;三是“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大学还须“到民间去”,将其创获的知识推广于学校围墙之外,由此实现对民族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在孟先生对大学精神的把握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现代大学三项任务——研究、教学、推广——的含义,也能看到他对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大学》‘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精神的继承。今天,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其中的生命力。”杜成宪这样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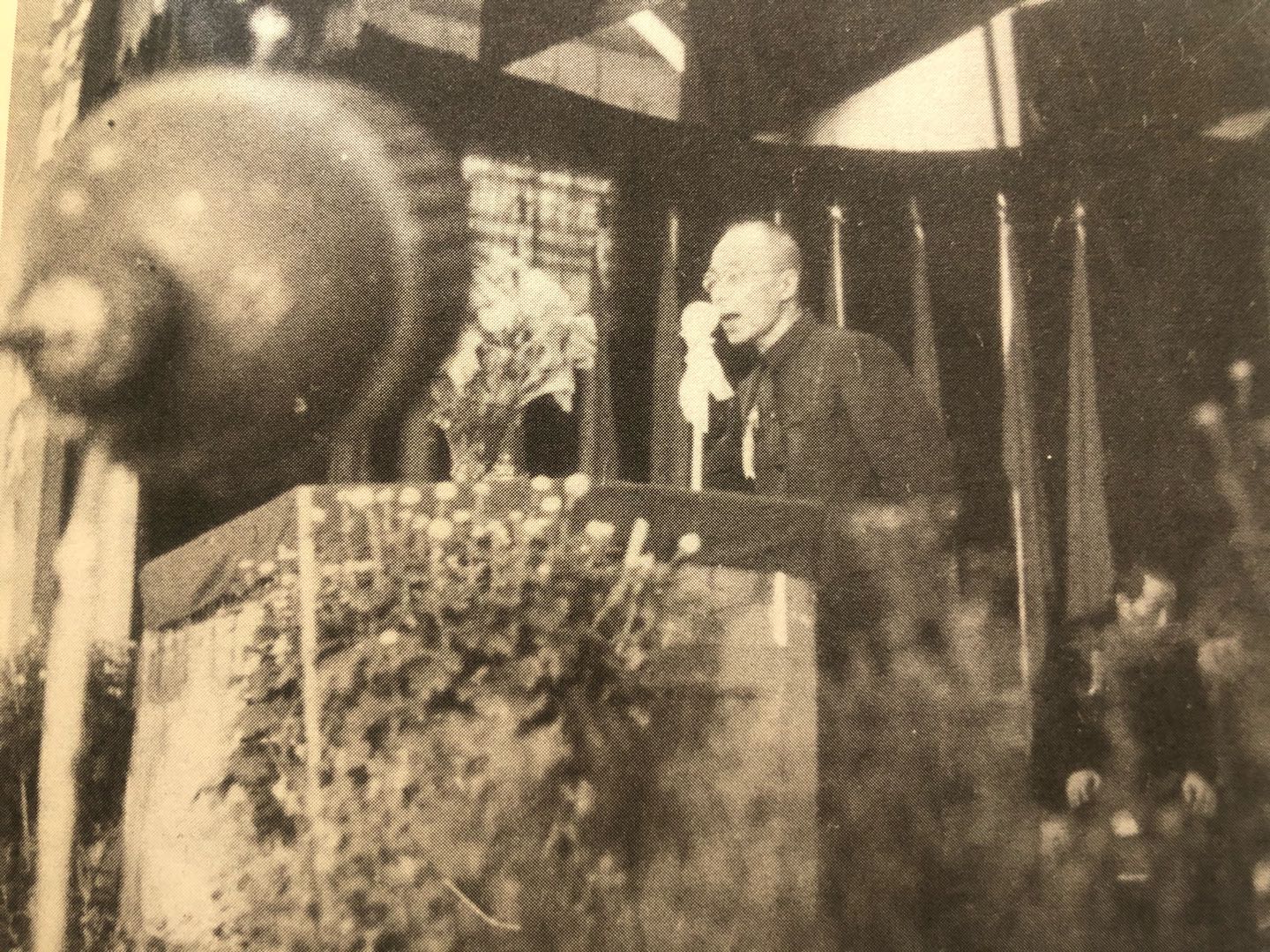
1951年,孟宪承校长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大会上讲话
当年孟宪承提出的“大学三理想”,后来成为了他作为首任校长执掌华东师范大学的办学理念,这也是他留给这座学校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从1951年学校成立到1967年他逝世,华东师大是孟宪承人生中停靠最久的“驿站”,而他也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这座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师范大学里。
“对华东师大来说,曾由孟宪承先生来执掌校务,是幸运的。”这是所有师大人的共同心声——办校初期,面对当时高师办学中存在的“师范性”和“学术性”之争,孟宪承明确表态高师应当从提高教学质量与提高科学水平的角度,“向综合大学看齐”。秉持这种理念,华东师大一直坚持师范性与学术性并重,以科研带动教学,开创了中国师范教育的新局面。在他的带领下,初创时期的华东师大一派生机,1959年便成为全国16所重点高校之一。
身为校长,即便事务再繁忙,孟宪承也从未中断他的理论研究,并始终站在教学的第一线。1956年9月,孟宪承担任由教育部指定开设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的导师,开始系统讲授中国古代教育史。曾有学生这样回忆,“第一次研究生课,黑板上板书工整六个字:‘古代历史材料’,没有一句客套话,讲课有条理……再没有一个老师讲一堂课,可以如此自始至终吸引着学生,他的旧学底子厚,儒学和清代的考据学左右逢源;他中英文俱佳,作报告二三十分钟没有一句废话。”这个班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中国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班,在他的带领下,华东师大后来成为我国教育史学科的重镇。生命的最后几年,孟宪承在发掘整理中国传统优秀教育遗产上倾注了极大心血,编著出版了包括《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等在内的一系列古代教育论著。

1956年,孟宪承校长与助手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回归中国精神,将中国教育史作为最终的学术归宿,对孟宪承来说也绝非偶然——对于传统,他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没有一个人能对于他自己社会里的历史文化宣告独立。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递,本来是教育应有的职能。”也正如学者张爱勤所说,他的一生“虽致力于西学的传播与研究,但始终注重中华民族自身文化传统,努力在探求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和中外教育历史比较中找寻中国复兴之路……最终实现了从西学传播向中学优秀文化传统研究的心路转型。”
“从古不知有多少‘悲天悯人’的教育家,耗尽了他们的心力,甚至贡献了他们的生命,才把我们的教育史,装点成这样的灿烂庄严。他们生平的故事,更可以净化我们浮躁的精神,鼓舞我们奋争的勇气。教育者精神的食粮,也将从这里得到了。”孟宪承早年在《教育史》中写下的这段话,恰恰是他教育人生的写照。
今天,“孟宪承”这个名字,早已成为华东师大的人格化象征;而重温他的故事,每一位师大人的教师梦,将变得更为坚实与丰厚——去年12月,师大学子用一出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大师剧《孟宪承》向他们的老校长致敬,孟宪承的饰演者、本科生黄天策就这样动情地说道,“‘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这不仅是孟先生认为的大学的理想,更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我们青年学子也将在他的精神指引下奋进,将自己的理想融入国家与民族事业中。”

作者:本报记者 陈瑜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